4月9日下午,作为“西域文明”系列讲座之一,我在国图作有关“印度教的神话与造像”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有听众提问:“为什么三相神中的毁灭之神会被译成‘湿婆’呢?听讲座之前,我一直以为湿婆是位女性。”对于长期学习印度文化的我来说,这个问题既陌生而又熟悉。说它陌生,是因为以我们的专业训练,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湿婆”是传统的译法,采用的是古代翻译佛经时形成的梵汉对音的惯例,“湿”对应音节si,而“婆”对应音节va。说它熟悉,则是因为很久之前一位医生朋友也有同样的困惑:为何佛经中的医生被译成“耆婆”?感觉像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角色。虽然这是一个细节问题,但从中亦可反映出汉语与梵语相遇时所面临的冲击。汉语基本上可说是表意文字,通过形旁可以望文生义,推测汉字的意思。这也是为何一般人看到“婆”字往往以为是女性。梵语则是记音体系,记录的是语言的发音,与意义倒无直接的关系。故而有学者戏称二者的接触是“眼睛”与“耳朵”的相遇。湿婆性别的尴尬问题,亦由此而产生。不过,作为印度思想中很关键的对立统一原则的体现,湿婆也有雌雄同体大自在天相,即身体的一半为男性、一半为女性。汉语译名“湿婆”,或许不自觉地反映了大自在天“安能辨我是雌雄”的神性?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偶合。
一直对印度教神话很痴迷,觉得太不可思议、太出人意料。很难想象身躯庞大、肥胖蠢萌的象头神会以体型瘦小、敏捷灵巧的老鼠为坐骑,对比太强烈,甚至让人心疼起小老鼠是否能堪重负;以甘蔗为弓、以鲜花为箭、以鹦鹉为坐骑的印度丘比特——爱神迦摩,旗帜上所绘的居然是鳄鱼,令人惊骇不已;去印度旅游,到处都是林迦(男性生殖器)-约尼(女性生殖器)像,让来自礼仪之邦的我们不禁脸红耳热。走进神庙、博物馆,眼前的景象总是既陌生,又似曾相识。太阳神的马车,我们已在希腊神话中见过;太阳神手持的莲花,则是佛教常见的装饰元素。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希腊神话、经由佛教,我们已经对印度神话有所了解。前者可谓是印度神话在印欧文化圈里的亲戚,而后者则是同样生长于印度文化沃土中的同根之木。然而,印度教又有其鲜明的独特之处。一是化身思想。为了拯救万物,维持之神毗湿奴一次次下凡,他的主要化身有十个:鱼化身、乌龟化身、野猪化身、半人半狮化身、侏儒化身、持斧罗摩化身、罗摩化身、黑天化身、佛陀化身、伽尔基化身,似乎暗合了从海洋动物到两栖动物、哺乳动物、半动物半人类、有缺陷之人,再到健全之人的进化历程。二是分身思想。每当毁灭之神湿婆发怒,从他的怒气中便会产生可怕的生物,残暴而富有攻击性,惩处恶人,彰显正义。
长期以来,虽也零零星星对印度教神话与造像有所关注、了解,但系统地学习把握,则是从施勒伯格这本《印度诸神的世界》开始。认识此书,得益于段晴教授的推荐:这部著作不仅在德国国内好评如潮、重版多次,在德语世界之外还被译成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出版。一气读来,酣畅淋漓,手不释卷。其中,神话与造像两个维度互为补充,互相阐释,将散落各处的神话碎玉连贯成一串圆满生辉的珠链,于是相应的造像也就被赋予了生命,变得鲜活起来。通过施勒伯格的叙述,印度教万神庙里的诸神,不再是干巴巴的名号。通过故事、诉诸图画,他们变得栩栩如生。在作者的笔下,诸神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欲望与恐惧,扮演着夫妻、父母、子女的角色。善恶之间并无绝对的区分。阿修罗通过苦行可以获得超越于诸神之上的法力;为了对抗他们,诸神也会玩弄阴谋诡计。作者的叙述条理分明,脉络清晰,从以“吠陀”典籍为依据的婆罗门教,如何逐渐发展到以“往世书”典籍为依据的印度教,印度本土的土著文化在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书中一一都有交代。最终萌发将这本书译为汉语的想法,并真正付诸实施,却要归功于段老师的鼓励支持与鞭策指点。在本科生的专业课上,段老师曾将此书作为教材,讲解了前面部分的内容,我也深受裨益。
本书共分八章。第一章从理论的高度介绍了印度教中神性观念的图像学转化。第二章主要叙述印度教万神庙中的三相神——创造神梵天、维持神毗湿奴、毁灭神湿婆的事迹与相关造像,接着描写了女神群体、象头神迦纳什、战神室建陀、吠陀诸神、曜神、仙人、阿修罗、圣徒等。第三章分析了创世神话搅乳海的故事,并交代印度教神话中动物、植物、山川的象征内涵。第四、五、六、七、八章分别介绍造像中诸神的体态(站相与坐姿)、手印、法器、装饰,以及标记图案等等。在这本书中,神话与造像相得益彰,宏观的把握与细节的描摹并重,叙述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翻译的同时也是一种享受。
然而,在翻译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最主要的便是上文提到的译名处理。在《广林奥义书》里,当被问到有多少天神时,Yājnavalkya回答说有3亿3千万。虽然这段话不能拘泥于字面解释,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印度的天神之多。名目浩繁的神,各有化身与分身,关于他们的传说又往往不止一个版本,名号的拼写也时有变异。如何翻译诸神的各种名号?这是比较棘手的问题。第一个原则是遵循传统、尽量从众。有些天神在古代的佛经里已有过介绍,如梵天、大自在天,这类便尽量沿袭古译。但其中有些译名,如乌摩天后(Umā),则改为在现代出版物中更常见的“乌玛”。有些天神在古代很少介绍,在现代汉语中译名又不一致,则采取相对常见、简便的译法,如战神Skanda译为室建陀,而非塞犍陀。第二个原则是尽量义译。对于习惯了汉语的表意性的中文读者来说,有意义的名字更容易记忆。另外,汉语中的同音字太多,音译容易造成混乱。不过,为了兼顾已经介绍到汉语中的音译名,可能时将义译、音译一并列出,并将音译放在前面,方便读者查找。如杜尔迦与难近母、须羯哩婆与妙项。在文中第一次出现的诸神名号,都会附梵语原文,书后也有详细的神名索引表,方便读者查找。不过,原书的索引词条为梵语,考虑到国内读者的需求,译稿的索引词条变为汉语,并且有所增删。希望将来条件成熟时能编一册《印度神名表》,统一对诸神名号的翻译,便于后来的研究者。
其次,由于这本书面向的读者群很广,既有专业性,也具普及性,故而在叙事上有些不够严谨的地方。例如,书中提到了行星神与恒星神,提到了地球的自转,是以现代的概念去规范古代的思想。这类问题,有的在文中以译者注的形式明确指出,有些笔误之处随文更正。总体来看,瑕不掩瑜,无损于这本书的参考价值。
著名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茨默在其《印度艺术与文明中的神话与象征》一书结尾讲了一个犹太故事。家住克拉考的拉比埃斯克三次做梦,梦中被敦促前往波西米亚的布拉格寻宝,宝藏就埋在通往王宫的大桥桥底。他来到梦中的目的地,但由于桥上有守卫,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每天都去桥边,徘徊至日落。终于,守卫长被这位老人的毅力打动,前来询问情况。当他得知拉比的梦境后,大笑起来:我也做过同样的梦,敦促我去克拉考寻宝,宝藏被埋在犹太拉比埃斯克家的炉窖后边的角落里,但我却不会因为虚幻的梦境而徒然跋涉!拉比听完守卫长的这番话,深深向他鞠躬,回家后立刻挖掘炉窖后的那块地,寻得宝藏,结束了自己贫穷凄惨的生活。茨默认为,这则故事的寓意在于:真正的宝藏不在远方,而在我们内心最深处;但只有走过虔诚漫长的旅程、得到异域陌生人的点拨,才能了悟内心声音的真实涵义。对我们而言,印度文化或许就象征着异域的陌生人,经由其映照点拨,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自身。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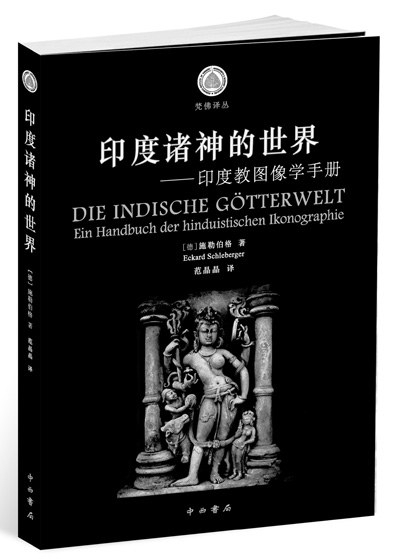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