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11月,在“侨易观念的意义与问题”学术研讨会上,借专著《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的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叶隽研究员向学界提出他穷8年之功思考的“侨易学”体系,系统阐述了作为哲学方法论的“侨易学”的学科概念、核心内容、研究对象和基本原则等。叶隽提出,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因“侨”而致“易”,既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也包括不同的文化子系统如何相互作用与精神变形。近年来,作为一种新观念、新概念体系,侨易学颇受各学科关注,不但报刊媒体时有讨论,而且在研究层面也逐步落到实处。在理论创新非常不足的中国学界,这一新理论的提出应予肯定,至于其前景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下面的文章则对这一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和建议。
过去两三年间,通过《侨易》一、二辑(第一辑仅仅做了一些理论方面的梳理,几乎不涉及实证分析)和《江苏师范大学学报》“侨易”专栏一年多以来持续不断的努力,侨易学已经从三万英尺的云端下探,逐渐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利器”。如何让侨易学这一理论得以发展与完善,是接下来应当努力的目标。笔者认为,侨易学这一“利器”欲要取得更大的突破,需在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关注:一是理论的挑战与回应,二是实证的拓展与细化。
一
在理论方面,笔者认为,经过最初的理论建构和梳理之后,侨易学目前应当努力的方向是:一,了解自己在理论层次中的位置;二,回应其他理论的挑战;三,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完善理论,使之更具有说服力,减少可能存在的含糊与自相矛盾之处。
在理论层次方面,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理论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级,他提出“中层理论”(theoriesofmiddlerange)观点,指的是“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而又必须的操作假设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类理论。“中层理论”主要用于指导经验研究,更接近于构成可验证的命题的观察资料,比单纯的经验概括更高一层。叶隽先生曾提出,“如果仅仅将侨易学作为一种理论,或是哲学来看待,往往有可能陷入浮生空谈。所以有必要特别强调其可操作性问题,甚至是具体的专门研究领域的问题”,所以,侨易学的提出,其“主战场”应该是在对经验的指导方面。因此在这种理论谱系之中,侨易学理应划入“中层理论”范畴。
笔者认为,虽然叶隽先生的研究背景是外国文学,但他提出“侨易学”概念,似乎并不仅仅想解释各种文学问题,至少哲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同样是侨易学企图施展的领域。也就是说,作为“中层理论”的侨易学,应当具有“超学科”的解释力,因此必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受到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挑战。
回到关于侨易学的讨论。如果将理论之外附着的哲学思想剥离,则可以看到,侨易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在移动中的若干生物,从此一地到彼一地,或从几个处所到另一个处所;研究它们的一切关系上与活动上所表示的一切现象”,其中“包括物质位移、精神漫游所造成的个体思想观念形成与创生”。例如,乔国强先生采用侨易学理论,对犹太移民到达美国后所经历的“第一次冲击”,他们在与美国“互动”中所发生的“易变”,以及美国犹太作家的移民经历及其作品展开研究,是运用这一理论的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但是,迁移活动对于个人行为和心理所产生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议题。例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中,区别了“旅居者”“归附者”和“双重国籍者”三类移民身份:“旅居者”抱有临时逗留心态,随时期待返回家乡,拒绝被移入地同化;“归附者”是那些背弃原籍文化,期待被移入地同化的一群人;“双重国籍者”则是“脚踏两条船”,对移出地和移入地都倾注情感忠诚。
亨廷顿关于迁移者认同类型的讨论,给予我们重要的启发,即由于社会环境结构、自我经历及受教育情况等因素的作用,使得迁移者在进行时空位移的过程中,其思想认识必然存在各种差异,绝不能用一种模式加以涵盖,也不能简单地以“变”或“不变”进行概括。归根结底,迁移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状况,应当在进行类型化分析的情况下,讨论导致不同类型出现的各种因素,并进行归纳与总结,寻求概念的升华,这应当是未来侨易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由于政治学、社会学在相关问题上,都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尤其是与移民问题有关的讨论,关注其迁移过程中的心态变化、以及对迁出/迁入地的认知差异,相关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必然蕴含着不少灵感火花,能够让侨易学在进行理论对话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收益。
二
在实践方面,笔者曾提出,“侨易学的价值与意义,正需要在各种领域反复尝试,甚至进行试错式探索,方能了解到侨易学的作用与局限究竟在哪里。随着实践的深入,反过来会推进与完善侨易学理论,双方的紧密互动,能够将其提升到叶先生目前难以想象的思想高度”。笔者目前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既然侨易学的目标是成为既有理论归纳、又有经验指导作用的水准较高的“中层理论”,那么决定侨易学生命力的根本,就是使用者本身的“用户体验”。如果侨易学能够达到以下两点:一,对这一理论的使用,能够解释以往研究过程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某些事物或现象;二,侨易学虽然并不一定效力十足,但使用起来方便顺手,区区三两招便能直击要害,那么侨易学的“市场前景”必然看好。
具体来说,先前在《侨易》集刊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及叶隽本人的讨论过程中,以侨易学为理论先导所进行的实证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的“侨易”,主要讨论个人进行时空迁移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与行为的迁变状况,如徐显静对伦道夫·斯托、黄少雯对哈尼福夫·库雷西、熊辉对徐志摩、顾钧对费正清所做出的解读等,这一类的研究是目前侨易学实证分析的“重镇”;二是“思”的“侨易”,主要讨论思想理念在进行“旅行”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如周云龙对“话语”术语的探讨,唐卉对“史诗”词源的考察等;三是“物”的“侨易”,主要讨论物体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历史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产生的“本土性”转变,例如王涛对拱廊、百货商店的研究等,这一类的研究目前成果还较为稀少。
对于利用侨易学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时存在的问题,我较为同意乔国强先生在2015年2月11日《中华读书报》上所发表的观点。他认为,目前的侨易学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的而非群体的‘侨易’”,或至少在叶隽看来,“群体性的侨易学分析,不太容易做到”(《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第35页)。乔国强认为,假如一个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个体,那么这个理论的有用性是有限的,或至少其广延性是狭小的。
当然,叶隽先生从来都没有提过,侨易学理论仅适用于个体,而不能解释群体现象;他也没有说明,侨易学仅能对精英行动进行分析,而不能介入普罗大众的讨论过程。笔者担心的是,目前利用侨易学理论所进行的实证分析,似乎都是走“高”“个”路线,即局限在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个”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历史上遗存下来可供讨论的文本,主要是由“高”人留下的,即使想从自下而上的角度进行分析,资料不足的障碍是必然会遇到的。另一方面,或许也可以称得上是“路径依赖”,即侨易学的首倡者叶隽先生,在其系统提出相关理论的著作《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中,主要进行的案例分析即是从“个体”层次出发(如对魏时珍、王光祈、郭沫若、宗白华等文化名家的讨论),无形中给予使用者强烈的暗示。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前者虽然障碍重重,却在史学研究路径转向的整体背景下,有望得到明显改善。近年来在中国逐渐盛行的“新文化史”“微观史”研究,开始突破长期以来史学研究奉行的“宏大叙事”“精英决定论”等视角方法,将关注焦点集中在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历史,在文化领域内进一步实践了“自下而上的历史”的主张,使学者更多地去研究过去文化史很少关心到的领域,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不少由平民撰述的文本(如日记、书信、笔记等材料)逐步得到发掘整理,相关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此外,口述史研究近年来方兴未艾,通过回溯性访谈的方式,从普罗大众那里获得平民视角的材料,以小见大地反映历史命运和时代变迁,这些工作已经在国内外多个研究机构展开。对平民文本和口述材料加以使用,能够让饱含精英文化色彩的侨易学研究更“接地气”,更具有包罗万象的解释力。
笔者记得,当年美国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Walder)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国营企业的劳动关系模式提出“新传统主义”概念之时,各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研究者对于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解释力度、理论局限等问题纷争不休。此时,另一位历史社会学研究“大拿”裴宜理(ElizabethPerry)发起倡议,“捋起袖子,大干一场……把比较政治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真正走进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现场去看一看”。而这种“捋起袖子,大干一场”的精神,正是侨易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能否产生突破的根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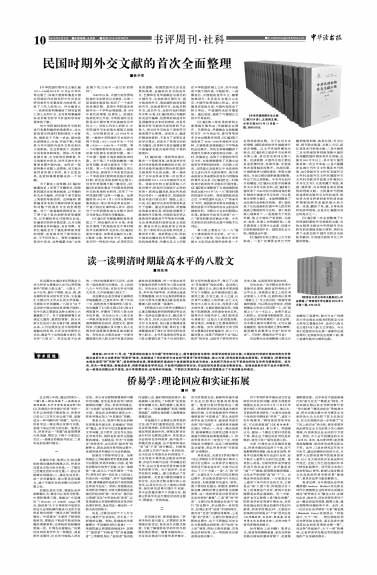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