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化和工业排放的关系问题上,“主流”科学家经常信誓旦旦地说:人类排放CO2正在造成气候灾难性的变暖,虽然有一些反对意见,但我们还是听主流的吧?这种想法在我因面对科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而心生厌倦时,时不时就会冒出来——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这样的简单世界多美好!
这种思维的惰性,在我的老师江晓原教授看来,是极不可取乃至是有害的——对科学的“警惕”在他已是一种常识,因为在所有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科学争议中,几乎都离不开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的维度。这就使得宣称“这是一个科学问题”经常变得非常可疑。有一次我们谈论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时,我说起下面这个故事,江老师非常感兴趣,对这样“非主流”的叙事,媒体很少关注,读者也就了解不多。
这件事简单来说就是:发明了“全球变暖”(globalwarming)这个词的科学家,在35年后的一本书中,对他早年的这个发明表示愧疚,并明确提出对主流观点“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CO2持续积累将超过临界值而不可逆转”并不认同。这位科学家沃利·布洛克(WallaceBroecker,更常用的名字为Wally)在很多领域都是先驱(《纽约时报》语),自然也称得上是一位“主流”科学家。而这本《大洋传送带:发现气候突变触发器》,讲述了从1980年代起作者关于“大洋传送带”的假想是如何形成,又如何经历了世界各地观察数据的验证及挑战的。
“未来水世界”如何容纳“后天”?
对这个书名感到“似曾相识”的读者,一说到《后天》就能想起来了——这就是那条贯穿海洋,据说对北半球气候产生巨大影响的温盐环流(THC)。在电影里,正是由于它在极区部分径向翻转环流(AMOC,北大西洋表层水下沉向南转为深层水)的中断,才导致地球在一周内就进入了一个新冰期。而发生所有这些灾变的罪魁祸首正是CO2——它使全球变暖,融化了极冰,稀释了流经此处的表层海水使其无法下沉,造成AMOC中断,开启了北半球的速冻模式。
但这只是电影。对于古气候学研究来说,短短几十年间,人们对于“突变”的想象越来越大胆。沃利的结论与《后天》相差甚远:即使“大洋传送带”中断,也是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内逐步衰减。至于现实中它是否正在发生变化,要在几十年的尺度上才能判断。他建议将对“大洋传送带”的关注“适度后挪”(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10年来AMOC无变化)。
沃利并未在此书中提到“主流”对其理论的接受程度。以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为例,五次报告都未使用“大洋传送带”一词,而是以THC或MOC代替,对“大洋传送带”影响全球尺度气候的想法仍有保留。就是说,全球变暖理论对沃利假说的接受度是有限的,就前者而言,灾难性的场面从50年代起就是《未来水世界》(温度及海平面上升)而非《后天》(间冰期/冰期转换)。但IPCC仍然将其列入预测,在最近两次评估报告中都认为未来温盐环流会减弱(将抵消一部分CO2导致的变暖)。如此一来,不管未来气候怎样(变冷、变暖或不变),都将无法证伪CO2的作用。
现实版的冰与火之歌
这样“强大”到无法阻挡的理论当然不是一天造就的,从沃利的经历看气候变化研究史是一个有意思的角度。
知道沃利的人都知道他发明了“全球变暖”一词,并把这件事说得好像是他的光荣成就。现在看起来这个词好像很普通,可是在70年代,实际上大部分观测都局限在北半球中高纬度地区:一开始是欧洲北部,后来是北美北部。而在60年代,像“气候变迁”“气候振动”这样的词尚且都是相当新鲜的概念(在中国,竺可桢60年代用史料证明气候不是固定不变的,70年代才将这些内容整理发表),且仅超长时段的变化才涉及全球。当这个词被发明出来,它所带来的语言上的震慑力是强烈的,以致于大众媒体都用“全球变暖”替代了“气候变化”。最近几年这个现象得到纠正,只是“气候变化”在内涵上与“全球变暖”等同的谬误,却不是那么容易矫正的。
可是,如果你见到沃利,千万不要拿这件事恭维他,因为他正为此后悔不迭呢。他跟学生说,如果谁能证明他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他愿意提供两百块钱的奖金。为什么他要感到后悔呢?这要从他何以发明了这个词说起。
研究气候科学史的美国科学史家沃特(S.Weart)有句话说得好:科学家和大众的想法是协同并进的。在环保主义兴起之前,人们对气候灾难的设想一般是冰期的严寒,而温度的上升通常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繁荣。因而在80年代之前,当科学家提起20世纪相对于小冰期的气候时,常使用benign(温和、良好)等褒义词。
对冰期的恐惧曾在70年代初的世界粮食危机中达到高潮。当时沃利正在哥伦比亚大学Lamont-Doherty地球观测所,为一位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逃脱”的地质学家库克拉(G.Kukla)积极游说,试图将其留在美国。库克拉自己也很争气,在仅一年的访学期内,就代表Lamont-Doherty地球观测所致信尼克松总统,警告说下一个冰期很可能在一个世纪内到来,而苏联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冷战时期,什么事一旦涉及到苏联,美国就不淡定。这之后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开始列入美国的政治议程。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沃利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论文——“气候变化:我们正处于明显的全球变暖边缘吗?”(Science,1975)
除了发明了“全球变暖”以外,这篇文章还清楚地回答了“CO2数据与气温趋势不匹配”的难题。CO2会导致气温上升作为一种理论在19世纪就出现了,直到1958年才开始有观测数据。虽然这个值是上升的,与化石能源消耗的曲线一致,可却与气温趋势不一致(气温1940~1970年下降)。这曾让科学界对CO2的关注停滞了一阵子。可是除了这个基于简单的物理机制得出的看似“必然”的结论之外,没有其他理论更适合作为预测基础。
气候的天文周期理论涉及的是万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对气候预测几乎没用;曾短暂流行的人类排放气溶胶导致降温的理论(理论值与欧洲北部观测数据一致)基本是个坑,因为气溶胶的作用极为复杂。其实沃利提出的“破解办法”在当时就是矮子里拔将军:用气候模型算出CO2升温效应,与冰芯代用资料得出的“周期外推”结果,二者叠加得出:“降温必将结束,CO2必将变成主要作用。”虽然到2000年这个预测都“应验”了,但之后又不灵了。如果没有这场“冰与火”之战,沃利或许不会像他的好朋友库克拉那样,急于发表尚不确定的言论;可是不管哪种危言耸听,带来的都是对气候学研究的资源投入。
这之后,沃利对碳循环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很多公开评价,都将这些(而不是“大洋传送带”)作为他对气候学最重要的贡献。但是悔其少作的他,如今对CO2气候作用的模型预测也不像当初那样推崇,这可能是他后悔年轻时说了大话的一个原因。
两种不完善的推测方法,信哪一个?
“在模型能够令人满意地再现过去之前,对化石燃料CO2排放影响的预测仍将存疑”,这是沃利在序言中告诉读者的,因为有人批评他的书很少提到计算机模型。
目前气候研究中的两个主要方法,一是代用资料(树轮、冰芯等)代替缺少的“观测值”,一是数学模式模拟代表物理机制产生作用的过程。一般来说,用代用资料重建的气候变化,如果能用模型模拟出来,就被认为是可靠的;相应的,若某种模式正好能够后测(“预测”过去)代用资料建立的结果,则认为这种模式是可靠的,其预测能力就显得比较高。之所以需要相互参照,是因为这两种主要方法都有比较显著的不确定性。问题是,当两者不符的时候,信哪个?
沃利此书中,两种情况都有。最值得一讲的是,关于“大洋传送带”的想法,本身正是受代用资料得出的一个错误结论启发而来。
如果CO2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那么历史上的气候变化必然伴随着CO2浓度的变化。1984年,瑞典的奥什格尔(H.Oe⁃schger)报告了格陵兰南部冰芯中CO2随温度变化而剧烈变化的发现。这不仅令科学家开始重视千年尺度气候变化的意义,也让他们更加相信CO2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沃利以及其他人对这个错误常常轻描淡写。事实上,几年后奥什格尔在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中担任第一章的主笔(四人之一),将这个结果写进了报告(11页)。事后证明,奥什格尔的发现只是格陵兰冰贮存过程中发生的化学变化。要知道,确认这是个错误总共用了9年(1984~1993)!没有这个错误,还会有沃利的“大洋传送带”吗?会减少科学家对CO2的关注吗?这很难回答。
有意思的是,这个错误为何能被发现?是因为,CO2的大幅度变化,仅出现于格陵兰冰芯和北大西洋沿岸,已知的任何机制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换句话说,这个发现难以被模型化(J.D.Robert,1993)。
在这个例子里沃利承认观测是错的,是因为这与他的碳循环理论相抵触。但更多的时候,选择的标准并不那么清晰。沃利曾一度相信,即使没有大量北极融冰稀释北大西洋的海水,仅靠全球变暖带来的降水增加就能导致传送带的减弱甚至关闭。这是当时气候模型给出的结果。但在此书中,他又选择相信另一种模型,即随着全球变暖,全球水供应会减少。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历史冰期找到了观测证据(当然是间接的)。
代用资料和模型的“架”打了不是一两次了。跳出沃利的书,最有趣的一件事是所谓“全新世温度变化之谜”(2014):同样是对全新世气温变化的重建,利用3种气候模式分别模拟出的结果与利用73种代用资料重建的结果,前者升高0.5℃,后者降低0.5℃。这两者出现偏差的原因,尚未达到“观察和理论之关系”的哲学高度,最大的问题还仅在于人们对于复杂现象的把握能力有限,即这两种方法都有明显缺陷。
去年Science发表了一篇对“大洋传送带”理论不利的论文,但争论远未结束。不管怎样,沃利写出这本书是令人赞赏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自己的成就和过失一并坦然处之。而它能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是:科学家的说法会变。至于使他改变的那些科学之外的因素,这本书就不会明白告诉你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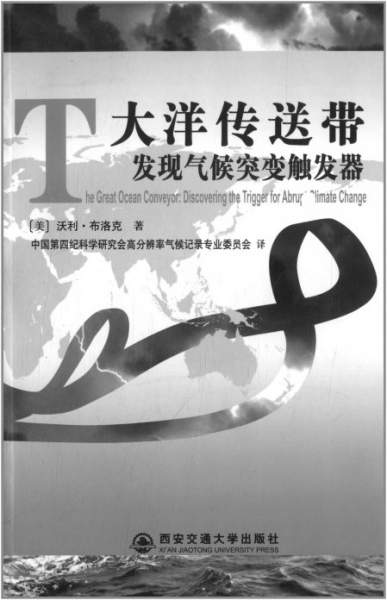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