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兵
江:
这次我们要谈的《爱因斯坦社会哲学思想研究》一书,虽是许多学者通常不屑一顾的“项目书”,但平心而论,“项目书”中也有好书,以前我也推荐和评论过。况且此书还相当有趣味,这在“项目书”中就比较少见了。这里我先举一例以见一斑:
爱因斯坦曾表示“我愿意当管子工”一事,是常见的关于爱因斯坦的“花絮”之一。对于这个花絮的意义,以前我们见到的读物中有各种解读。看起来比较“唯物主义”,是从经济收入来说事,说管子工虽然干的是脏活累活,但收入很高,有人甚至把管子工的收入和当时美国一个州长的收入相提并论。当然,在这个解读中,爱因斯坦即使只是随口开玩笑,也显得相当庸俗,仿佛唯利是图见钱眼开的样子。
现在《爱因斯坦社会哲学思想研究》叙述了关于此事的具有更多学术含量的版本:1954年11月18日出版的《记者》杂志上,发表了爱因斯坦的一封来信。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终止奥本海默的“安全特许”,为美国制造原子弹立下汗马功劳的奥本海默已经面临对他“忠诚”的审查。这封来信就是因此事而写的,爱因斯坦在信中说:
只想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去谋生,那么,我绝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plumber),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这是关于爱因斯坦“管子工”事件最初的文本。从这个文本看,显而易见,“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只是爱因斯坦表达政治抗议时的修辞手段而已。爱因斯坦的这种政治立场,和当时美国的政治风潮——盛行数年的麦卡锡主义恰好在此时退潮(两周之后美国参议院就通过了法案,谴责麦卡锡的政治迫害行为)——联系起来看,是很容易理解的。
其实这封信在被《记者》杂志刊登之前,已经于11月10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了,次日《纽约时报》又报道说,爱因斯坦将获得管子业工会的会员卡。几天后,爱因斯坦收到了芝加哥管子业工会给他寄来的管子工工作证,他回信说很高兴收到工作证。而纽约管子业工会则为爱因斯坦送去了一套镀金的管子工工具。于是一次严肃而不失委婉的政治抗议,迅速转化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花边新闻。
刘:
我们现在谈论的这本关于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思想的书,涉及有关爱因斯坦非常重要但在日常的科学传播中却经常被忽视一个方面。你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可以说是让普通人更容易接受而且颇具戏剧性的。其实就爱因斯坦来说,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有些非常严肃,而且极有启发性和象征性意义。
在我们日常的科学传播中,大多只是关注爱因斯坦作为一个顶极科学家的身份和贡献,而在国际上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和纪念中,将爱因斯坦称为“科学家-哲学家”,却早已是经典的说法。人们经常会说,当一位科学家达到很高层次时,便会自然地超越那种纯粹技术性的层面而去关注哲学问题。但爱因斯坦却又并不仅仅是一位关心科学和哲学并且关于这两者都有深刻思想的伟大人物,他有关社会事务的许多观点,也都曾有过很大的社会影响。当年,我的导师,国内爱因斯坦的权威研究者许良英先生,选编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一卷主要是科学论文,一卷主要是哲学文章,另一卷则主要是社会政治言论。
有关科学,那本是爱因斯坦的研究专长。关于哲学,比如涉及科学技术伦理等哲学问题,比如他与玻尔长达几十年的争论所涉及的关于物质世界科学规律的本质等更根本性的哲学问题,这也还可以算是与其科学研究有很大相关性,但又是在深层次上的拓展。而在涉及社会政治问题时,他的言论和观点引起人们关注,也许一是因为其超等的智力和思考方式,使其观点本身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启发性;二是因其正直、善良、勇敢的天性和立场,使其观点公正且不虚伪;三是因他在科学上的声望而联带产生的明星效应。
江:
我查阅了一番,发现我们在本专栏13年的历史中,已经三次讨论过爱因斯坦:第一次是谈《爱因斯坦全集》前五卷,第二次是关于《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第三次谈的书就是已故令师编的《走近爱因斯坦》。每次的侧重点当然各不相同。
爱因斯坦是让人们百谈不厌的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的科学成就,还因为他的种种传奇故事,和他在各方面所发表的言论和他的思想。我注意到你在为《爱因斯坦社会哲学思想研究》写的序中,将爱因斯坦称为“公知”,而且是“理想的、典型的、标准的”,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这让我想起,我曾在谈论青年爱因斯坦时,将他称为“超级民科”。提到这两个例子,正是想借此说明,爱因斯坦具有多重面相,他的思想和言行具有广泛意义。
本书第六章“自由观:麦卡锡时期的自由斗士”,讨论了三个事件,都是爱因斯坦站出来仗义执言并引起激烈争议的事件,其中就包括“管子工事件”。对此,补充一些有关的背景,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更多便利。
爱因斯坦在美国生活了23年,终老于此,并在来美第8年加入了美国籍。但是很少为人所知的是,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一直怀疑爱因斯坦是共产党的间谍,对他的秘密调查整整持续了23年!FBI对爱因斯坦及与他往来人物的监控行动,包括窃听电话、偷拆信件、搜检垃圾桶、进入办公室和住宅秘密搜查等等,完全和好莱坞匪警片中的老套情节如出一辙。难怪爱因斯坦在1947年12月作过如下声明:“我来到美国是因为我听说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大、很大的自由,我犯了一个错误,把美国选作自由国家,这是我一生中无法挽回的错误。”(见FBI解密档案)
刘:
你说的这些背景,以及听上去颇有戏剧性的爱因斯坦站出来仗义执言并引起激烈争议的事件,确实因为爱因斯坦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正直而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这个原因,我在给这本书写序时,想到了“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因为据一些学者考证,欧洲有关知识分子的概念有两个,一个是来自俄国,专指19世纪30到40年代把德国哲学引进俄国的一小圈人物,是一群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独特的阶层。另一个是来自法国,专指一群在科学或学术圈中的杰出作家、教授及艺术家,他们批判现实政治,成为当时社会意识的中心。我们恰恰可以认为,爱因斯理正是这种典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至于“公知”,则是一个更中国化的概念,而且近年来,在我们这里,在网上其形象先是被热炒,后是被污名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公知”与前述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是等价的。但“公知”概念和“公知”形象在中国的遭遇,有“公知”自身的原因——在这方面爱因斯坦正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理想的榜样。
但说爱因斯坦是“理想的、典型的、标准的”“公知”,又不仅仅是因其敢想敢说,他在社会哲学其他领域中的思想(按《爱因斯坦社会哲学思想研究》一书,至少还涉及宗教观、民族观、科技观、教育观、世界政府等许多方面),也同样整体性地构成了他作为直正意义上而非炒作意义上的理想“公知”的重要基础。
也许我们可以试着做个理想实验,去想像一下,如果这位因其“民科”时期的工作而伟大而获奖而出名,因其独立思考而仗义直言的“公知”的言论,要是出现在我们现在这里的网络上,他是不是也会面临着被“污名化”的风险呢?
江: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想实验,让我们先将条件澄清一下:如果你说的“我们现在这里的网络”,就是指当下国内互联网的“舆论场”的话,那么我的推测如下:作为“民科”的爱因斯坦可能先被方舟子之类的人嘲笑,后来得了诺贝尔奖,自然就跻身科学殿堂的神圣之位。而他作为“公知”的言论,则大有成为“网红”的潜质,很快就跻身“大V”之列,多半不会有被“污名化”之虞。当然啦,他也不能犯政治错误——考虑到爱因斯坦是如此的“左倾”,如此的“同情共产主义”,犯这种错误的概率应该不太大吧?
这就直接将我们引导到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与影响”。爱因斯坦自己说过,“我享有一个无可责备的社会主义者的盛名”,他还在信件中向玻恩表示,“我必须向你承认,布尔什维克在我看来,并不那么坏,不管他们的理论是多么可笑”。二战结束,冷战继起,爱因斯坦甚至在1949年发表了《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样的文章。也许这些恰恰成了胡佛的FBI死死盯住他20多年不肯放手的重要原因。
在接触爱因斯坦这方面的思想时,我们应该看到,在那个时代(二战前后),西方世界上层人士中“左倾”和“同情共产主义”者不乏其人,也可以算是一种时髦的事情,我们在“南腔北调”专栏中谈到过的一些人物,比如贝尔纳、李约瑟等等,皆在此列。考虑到这个背景,就可能对爱因斯坦的一些政治言论和行为有更好的理解。
刘:
你对我说的那个理想实验的回答,我基本上都认可,除了最后一点。我觉得爱因斯坦仍然难逃被污名化的命运,并不因为他的“左倾”和“同情共产主义”,就能幸免于难。更何况“左”与“右”这种政治立场的划分,在我们这里和西方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差异。他之所以被FBI死死盯住,恰恰是因其“左倾”的激进和与官方主流的不一致。
先师许良英先生曾将爱因斯坦总结为:“一个虔诚的世界主义者,一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一个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一个诚挚的社会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怀疑一切权威的人,是一个始终独立思考的人。他一生的追求,就是:真、善、美。”但我却更倾向于将爱因斯坦定位于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因其无可争议的科学地位,而使其在科学之外的领域中贯彻这种理想主义时——那怕有当时像来自胡佛和FBI的“美式的污名化”——能够有充分的“资本”来支撑。
用今天的网络语言来说,许良英先生可算作是爱因斯坦的“铁杆粉丝”。他几乎容不得别人对爱因斯坦有半点的不敬之语。今天作为研究者,我们当然不必有如此的前提公设,也不必假定爱因斯坦讲的句句都是真理,而是更为学术地研究其思想的价值。这些资源,恰恰是当下我们的社会和科学家乃至我们的“公知”所缺少的。
最后还可以提及的是:从师承上来说,许良英先生是本书作者的师爷,到学术第三代,仍然同样关心爱因斯坦的社会哲学思想,这也可算是学脉继承的一段佳话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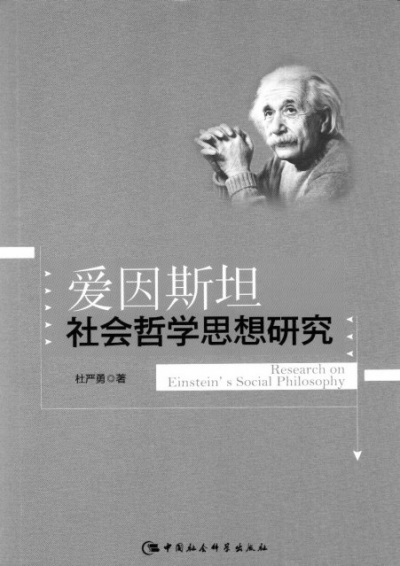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