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飞禽记》之前,我甚至从不知道约翰·巴勒斯的名字。这位生活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一生著述甚丰,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他关于鸟类、植物以及乡村景观的观察与描写。
按照书上所说,巴勒斯出生在美国加斯克尔山下的一个农庄。农庄里的日子对一些人来说是乏味枯燥的,以致急于摆脱,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辈子都无法割舍的。巴勒斯显然属于后者。1873年,36岁的巴勒斯建了自己的农庄,造了溪畔别墅;1895年,又在溪畔别墅附近造了一座原木风格的木屋,那是他晚年最爱的居住地。我在《飞禽记》中看到这座小木屋以及屋中书房的照片,简单的家具摆设、木质的温暖以及窗外满眼的绿色不只暗示了小屋主人的口味,也让我忍不住地想象着小屋主人的写作时光:在每一个宁静的午后或夜晚,聆听着鸟儿的歌唱和风过树梢的喧闹,而他文字中的那种性灵和温暖大概也正来源于此。
《飞禽记》中辑录的就是这些关于鸟儿们的性灵的温暖的文字,它们呈现的是一个距离今天的都市生活如此遥远的世界,或者它本来并不遥远,只是我们在每天忙碌的生活中将它遗忘了。但是对于巴勒斯来说,鸟儿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他习惯了有棕林鸫歌唱的日子,他“每天期盼着这如期而至的歌声,就好像期待美味的早点一般”。但是在某一天的清晨,他“觉得少了点什么,缺什么呢?哦,棕林鸫今天没有唱歌”。他猜想是红松鼠侵扰了这些棕林鸫的生活,结果的确不出他所料。他的情感因此也随着这些小邻居们的消失不见起伏不定,“想必棕林鸫的快乐心情也早已跌落谷底。这一周,再也没有听到过鸟的歌声,树冠里没有,哪里都没有。快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听到在小坡下面,雄鸟的歌声再次传了出来,原来这对棕林鸫在那里又安了新家,现在小心翼翼地又露了头。显而易见,之前的痛苦遭遇还压在心头,尚未退去”。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开始费力地回忆上一次听到鸟儿的歌唱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便隐约记起那可能是某天的清晨,又或者是另一天的黄昏。这样的追忆让我忽然意识到,那个自然的世界已经在我的生活中缺失得太久,而且,这样长久的缺失竟然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此刻,当我想到这一点时着实感到了不安)。就此而言,阅读巴勒斯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叫醒沉睡的耳朵,让心重新变得柔软。
在巴勒斯的笔下,鸟儿们当然并不仅仅带给他美妙的音乐,它们的生活更是充满妙趣与温情。比如东蓝鸲夫妇会双双飞去寻觅筑巢的材料,然后由东蓝鸲太太完成筑巢工作。当然,东蓝鸲先生也没闲着,他会在一旁保护着太太,并且在太太完成工作后适时而毫无保留地送上赞美。同样是筑巢,歌带鹀就让人看得实在揪心,它们总是将巢建在地面上,当然,如果巢建得足够隐秘,那么它们的确不太容易遭到天敌的攻击(但蛇和鼬除外),但是假如粗心大意,把巢筑得不够谨慎,那么可能就连猫都能成为它们的噩梦;它们习惯了在地面上建巢,而一旦想要尝试点新高度,比如把巢建在树上时,则往往因为地形不熟而要冒点风险。乌鸦讲究礼仪,风度翩翩,它们“会迅速发现捕捉它们的任何陷阱或圈套,但要他揭穿最简单的计谋却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巴勒斯将肉和骨头放在它们常常守候的地方,这些小机灵鬼们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怀疑,变换了各种角度与方式去观察其中可能隐藏的风险,结果在它们最终做出抉择之前,狗叨走了骨头。苍鹰是天空的骄子,“冷静而高贵”,当遭到乌鸦等其他鸟儿的围攻时,“他从来不去注意这些吵吵闹闹、暴跳如雷的敌人,而是故意向高处盘旋,上升再上升,直到追捕者头晕目眩,返回地面为止。这一招是独门绝技,摆脱没有价值的对手——上升到那些吹牛皮的家伙感到头晕目眩和难以企及的高度,让他们直接失去筹码!我不确定,但这一招值得模仿。”
在这些文字中,巴勒斯是鸟儿们的邻居,也是那个世界的欣赏者。他看着所有的故事在自然世界中发生,然后再用温暖的文字将它们呈现给他的读者。安静地驻足,温情地注视,换成一句话就叫作“懂得欣赏”,这是今天很多人已经失却了的能力。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有一次在某动物园的所见:在鸟类区,一架架“长枪短炮”一字儿排开。我已经不记得那天后来的情景如何,但当我想起那一幕时,我几乎已经听到揿动快门时的一片“咯嚓”声。今天再想,那一幕的荒谬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地点的选择和对宁静的侵扰,更在于将欣赏的能力与眼光拱手相让的举动:假如将“长枪短炮”从眼前拿开,你是否还能“看”到这个世界?当我写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也颇迟疑了片刻,但我最终还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再一次地,这个结局让我感到庆幸。蕾切尔·卡逊曾说:“在自然中得到的持久快乐,并不只属于科学家,也属于任何去感受天地大海的人,任何去感受万物生灵的人。”在我看来,这“感受”二字中就隐含了上述问题的答案:先要“感受”,继而“欣赏”,然后才能获得与自然相处的持久快乐,而无论是“感受”还是“欣赏”,其实都与那些架在眼前的机器无关,也是它们代替不了的。
此书开头的一篇简短小传中说,巴勒斯的博物学作品“文学性比科学性更强,对动植物的描述并不像最严格的博物学家那样准确,而是更富于个人化的视角和情感性”,小传作者说这是他的作品比其他博物学家更受公众喜爱的原因,而我想说的是,这其实也正是我喜欢他和他的作品的理由。
关于这本书,最后特别想说的是书中的一张照片。那是拍摄于1914年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三个人中,除了博物学家巴勒斯之外,另两个人是发明家爱迪生和汽车大王福特。那一年的巴勒斯已经是一位77岁的老人,雪白的头发,长长的雪白的胡子,很有几分仙风道骨;那一年的爱迪生67岁,他引领了一个发明迭出的年代,他的发明同那个年代里对宇宙的发现一起分享着人们的赞誉;那一年的福特51岁,相比于其他两位合影者,他可以算得上是个小伙子了,而那个属于他的汽车世界也正像他一样年轻,富有活力。三个人并排站立,目光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在拍摄这张照片之后的三十余年间,这三位都曾深远地影响过这个世界的人物相继在84岁时去世。不知道这老哥儿仨是否会在另一个世界再度相遇,但无论如何,这张照片很像是一个隐喻,关于那个已然开启的时代,关于那个他们身处其中的世界。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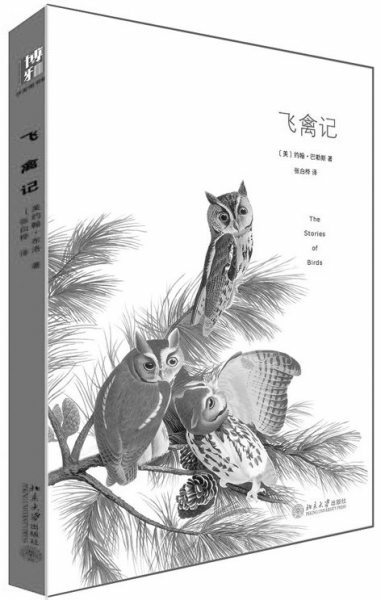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