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九讲》没有延续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将沈从文简化成书写乌托邦式的中国乡土、具有田园抒情诗人气质的文学家,而是带领读者去了解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的沈从文的一生,并将他的挫折、坚持与退守置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加以理解。
理解沈从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沈从文去世后,妻子张兆和着手整理他的生前文字。这本该是借由文字和丈夫的一次重逢,意外地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遗作被发掘,张兆和却渐渐意识到自己过去从未真正理解丈夫。她在《从文家书》的后记中坦言:“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
在沈从文去世前一年,沈虎雏将誊写好的《抽象的抒情》交给父亲审阅。沈从文读完后,却感叹“这才写得好呐”——显然,老人已经忘记了这篇文字。《抽象的抒情》是沈从文1961年在青岛养病前后写成的。那一年,他已经开始准备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部无论对于他个人还是对于整个考古学界都意义重大的著作;而青岛,则是湘西之外,沈从文最为留念的地方,因为他在那里度过“一生读书消化力最强、工作最勤奋、想象力最丰富、创作力最旺盛”的三年,写作了《从文自传》《八骏图》等作品,并开始酝酿代表作《边城》。由此,不难推知这篇文章的分量。然而,二十多年后,八十五岁的沈从文已经将生命中这一重要的片断遗忘了。
沈从文晚年有太多令人唏嘘的片段,许多片段伴随着老者的眼泪。整理家信时的眼泪,答记者问时的眼泪,听闻老友离世时的眼泪。然而,比眼泪更让人唏嘘的是遗忘。也正是这次遗忘提示了我们一条为许多人忽视的理解沈从文的道路——“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抽象的抒情》题记)。
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显然留意到了这次遗忘。在新近出版的《沈从文九讲》一书中,他将这条路径概括成从沈从文理解沈从文。全书以此为基本方法,通过九个相对独立的章节,讲述了沈从文一生创作与实践及其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回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诸多篇幅也是张教授为本科生开设的“沈从文精读”的课程讲稿的底稿。作者以另辟蹊径的方法、娓娓道来的讲述、亲近的文字,为普通读者铺就了一条“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的道路。
《沈从文九讲》没有延续通常的文学史叙述,将沈从文简化成书写乌托邦式的中国乡土、具有田园抒情诗人气质的文学家,而是带领读者去了解作为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的沈从文的一生,并将他的挫折、坚持与退守置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加以理解。作者把沈从文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从一开始创作到1936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是文学阶段;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结束,是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1949年之后,一直到他去世,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阶段。三个阶段分别对应文学家、思想者、实践者三个形象,而“贯穿起这三个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又如,作者在分析沈从文在1949年后的文学创作时,没有止于这些作品,而是通过与同时期的书信、检讨、自白等“并非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的对照,得出后者“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字创作更多的文学性”的结论。张新颖教授认为,“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比公开发表的作品和书信,“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可见,对沈从文而言,书信是一个特殊的私人写作空间,不能简单地说他的作家生涯到1949年就彻底结束。
分析沈从文土改时期的一封家信时,张新颖教授甚至直接援引同时期其他的书信来解读信中夜读《史记》的内容。这封信中关于《史记》的内容只有一千多字,但引用其他书信的文字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并且全篇所有的征引文字都出于沈从文之手。筛选、剪裁、拼贴,无疑是简单到极致的文字处理法,但张新颖教授直言,“在理解沈从文的所有方式中,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是个基础,就目前而言,这个基础工作仍然没有做好”。
“从沈从文来理解沈从文”虽说是“基础工作”,却对研究者有着极高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张新颖教授的角色近乎于剪辑师。如何从五百多万字、三十二卷本的《沈从文全集》中“剪辑”出意味深长的生命片段,考验的不仅是对文献的熟悉程度,更是研究者的个人洞见。
张新颖教授敏锐地指出,许多读者认为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清澈透明,很“表面”,缺乏“深度”,但这种看似挑剔的“批评”其实道出了沈从文的“好”。他先从《湘行书简》选取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继而阐发出“‘深度’是‘焦点透视’产生的,要产生出‘深度’,一定要有‘定见’‘定位’‘定向’‘定范围’,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眼光’所及的东西对象化,用‘眼光’去‘占有’景物,使景物屈从于‘眼光’,以便‘攫取’景物而产生出解释的‘深度’。沈从文的‘看’,却不是‘占有’式的,他(指沈从文)虽然未必达到庄子所说的‘使物自喜’的境界,却也庶几近之,因为有意无意间习得了‘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的观物方式”。
而回溯《边城》从酝酿到落笔的过程,作者更是将《从文自传》中的渡筏,《新题记》《水云》《关于云南漆器及其他》中民国二十二年在青岛遇见的为家人“报庙”的女孩,《湘行散记·老伴》中绒线铺的女孩子等种种场景调度、连缀在三四页的篇幅中,还原了《边城》传奇背后的一些本事。而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纠缠正是一位年轻作家的敏感心性的写照。如此读者更加理解作品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无奈与悲哀。
或许,我们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沈从文九讲》呈现了张新颖教授细心剪辑的九个生命片段,而这九个片段,连缀成作家一生的蒙太奇。将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与电影画面类比,似乎有些牵强。但耐人寻味的是,导演侯孝贤和贾樟柯都曾表示,自己的电影受益于沈从文的作品。这样说来,蒙太奇的类比是有些道理的。《聂隐娘》那些风吹影动的空镜头,《小武》里那些偶然进入镜头的路人,和《沈从文九讲》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的方法一样,都是读者对沈从文的文学传统的回应。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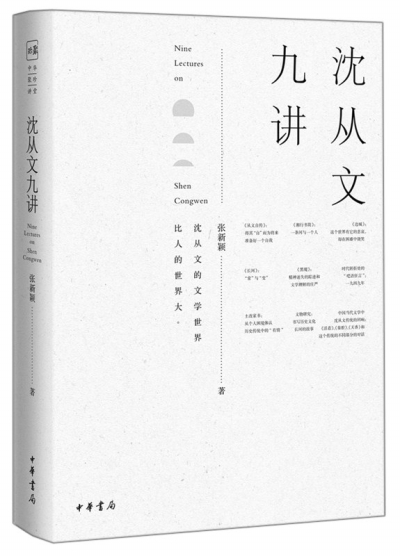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