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 合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江晓原 ■刘 兵
□许多天真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从未出过国门的——喜欢将美国社会想象成一片人间乐土,相信那里公平公正,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蓝天白云祥和安宁。其实美国的许多真相,并不是非要你亲自踏上那片国土才能接触到,你只需读读一些美国人的著作就能了解。说实在的,这本《违童之愿》所讲的事情,就让人相当震惊。
在我们以前习惯的认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法西斯利用战俘等所做的那些臭名昭著的“人体科学实验”,都是毫无疑问的战争罪行。纽伦堡审判谴责并惩处了德国法西斯医学专家的这些罪行,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所做的类似行为,也遭到世人普遍的厌恶和声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当然是美国主导的,即便是美国当局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对日本“731部队”的罪行网开一面,至少表面上也会有所谴责。总而言之,这种违背医学伦理的实验不可避免地和“罪行”联系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从《违童之愿》中看到,美国竟早就在它本土实施了类似的实验,而且实验对象竟是它的本国公民时,不能不感到非常意外。更为令人发指的是,美国的研究者们“纷纷扎到孤儿院、医院、收治‘低能儿’的公立机构,去寻找实验对象”。而且这种行动事实上早在冷战之前的19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在时间上倒是和德、日法西斯的“人体科学实验”正相伯仲。
■这本聚焦于美国医学史上一些惊人的负面内容,正如封底的提示中所说:“《违童之愿》记录了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面”。
医学,本来是为了救助人类,为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目标而发展起来的。然而,近代以来,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的,恰恰是在医学领域中,或者说打着医学研究的旗号,进行了很多从根本上违背人性的“罪恶研究”。
但这里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说,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731部队”所做的“人体科学实验”,在被人们厌恶、声讨的同时,由于“研究者”的背景,人们似乎更会将之归于法西斯的作恶,那为什么美国竟也会以其本国公民,而且是以儿童为对象进行实质上很类似的反人性的“医学研究”呢?在这些本质上均是违背医学伦理的实验之间,又是否存在什么深层的相同之处呢?当我们看到这些历史记录而对那些罪恶行为恨之入骨之时,我们是否会联想到,即使在现实中,是否还有些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一样,但实质上却同样也有某些相似甚至相同之处的实例呢?例如,前不久媒体揭露的在中国利用小学生进行的“黄金大米”实验,是不是也可归为此类呢?
□你的猜测完全正确,它们确实可以归入同一类型。从德、日法西斯的“人体科学实验”罪行,到美国国内对儿童进行的明显违背伦理的类似实验,再到美国科学项目跑到中国来进行的“黄金大米”实验(也是利用儿童,真让人有异曲同工之感),确实有一条线隐隐串联在一起。而对于这背后的原因,本书作者是这样说的:这些研究者们“很多为至高无上的目标所驱动,也有人是为了追寻名利”。这个说法值得推敲。
在我看来,且不说“追寻名利”这样的措词实在过于轻描淡写,更大的问题是所谓“至高无上的目标”。首先,对一个医生来说,“拯救人类”、“创造历史”之类的目标算不算“至高无上”?也许很多人会说,这当然可以算。如果我们同意这一点,那么当年实施德、日法西斯的“人体科学实验”的医生中,如果有人也抱持着这样的目标,或者有人真的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向着这样的目标努力,他们就可以脱罪吗?如果他们不能因此而脱罪,那么美国医生们的行为就同样无法脱罪。
再更深一层来考虑,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类侵犯人权的“人体科学实验”成果,真的可以帮助救治更多的病人,那这类实验有没有正当性?根据我目前所认同的伦理道德,我认为仍然没有正当性。无论目标何等崇高伟大,都不能提供不择手段实现该目标的正当理由。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凡是主张为了实现伟大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人,结果都是先造成了罪恶,却从未实现那些目标。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有一种目标只能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才能实现,这种目标还可能是正当的吗?
■这里实际上涉及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的伦理学问题。类似的伦理学问题,虽然在给人们带来的冲击程度可能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
曾有人设想过这样一个“理想实验”:有若干身体的不同器官患有严重疾病的院士,和一个在生理的意义上身体完全健康的民工(再极端一些甚至可以设想为其精神上亦有严重缺陷),我们是否能认为将这个民工的不同器官摘取(也就意味着以这种方式杀死了这个民工),并将其移植到多个院士身上,从而挽救这多位院士的生命,以便让他们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据说在某些很高级别的科学会议上,有人提到这个“理想实验”时,居然有不少人表示是可以接受的。虽然这只是听到的传闻,但按照我们平时见闻所及的其它情形下一些科学家的态度,我觉得,有些科学家支持上述看法,也是可以想象的。
当然,在另外更多具备基本伦理意识的人,肯定会认为这完全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在衡量伦理问题时,显然不能以考虑收入支出的经济方式,不能接受以牺牲弱小或对人类和社会“贡献小”的人的利益(更不用说生命)为代价,来换取那种所谓“贡献更大”或对更大群体“有益”的行为。因为这是在伦理意义上为人类所不能也不应接受的“恶”。
虽然《违童之愿》讲的是更极端的情形,但由于种种原因,当问题在表面上似乎有所变形而实质上却相同时,总会有些人不具有良好的伦理意识,当这些人是科学家并且诉诸实践时,就会成为科学伦理意义上的丑闻和罪恶。
□这里我忍不住又要稍微扯远几句。其实这种认为目标伟大崇高就可以不择手段去实现的想法,和我们经常批判的科学主义之间,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具体到《违童之愿》中所揭露的罪恶行径,这种内在联系恰恰相当明显。
与此有密切联系的,还包括书中揭示的一系列西方医学界的学术不端行为——这些行为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与违反医学伦理有关。例如十几年前英国的韦克菲尔德医生,宣称他的研究成果表明,儿童自闭症与MMR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有关,导致许多家长产生恐慌,停止给孩子接种该疫苗。但几年后韦克菲尔德医生被揭露是拿了某个集团的大量金钱,为的是用“医学成果”帮助该集团的诉讼,于是《柳叶刀》杂志宣布撤销韦克菲尔德医生的论文(反正这种“撤销”对那些所谓的“顶级科学杂志”早已司空见惯了)。但是这场闹剧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麻疹成为地方流行病。
违背伦理的医学实验,比如本书所揭露的美国儿童人体实验,广义来说也可以视为学术不端行为的一部分,而学术造假则是比较容易被关注的另一部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些被揭露出来的学术不端行为,很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更多的不端行为被行业的自我保护机制尽力掩盖起来了。在这样的事例中,无辜的公众一再被置于不知所措的窘境中,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其实和那些儿童人体实验中儿童及其家长的处境,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违童之愿》中还谈到了一个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事例,即在饮用水中加氟的争议。这项争议已经持续了60年,在美国,很久以来是加氟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在欧洲和许多别的国家(包括中国),并未采取美国那样全面加氟的措施。本书作者的意见是:“氟中毒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我们的儿童接触到的氟化物已经太多了。”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将此事称为“氟化物实验”,这是不是意味着,在这场争议中,几代美国人事实上已经沦为实验对象?这为什么不可以视为一项超大规模的人体医学实验呢?
■除了那些研究者之外,还有另外一些自己不做研究,但却以保卫科学的名义来努力为这些反人类行为辩护的人。仍以我们这里的“黄金大米”事件为例,不是也可以看到有那么多人在网上为其合理性找借口做辩护吗?
这些本来非常清楚明确地应为人们唾弃并坚决抵制的恶行,之所以仍不断出现,之所以仍然有人为之辩护,背后另一个重要的观念支撑,就是以功利的算计,加上为资本追求利润的目标,再加上科学研究的某种“超越性”,让一些人或是内心中无意识地默认,或是公开明确地宣称,为了科学的发展,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健康甚至生命。
但这恰恰与人们心目中发展科学的本意相违背。发展科学,本应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但当发展科学的过程反过来要危害人类时,那这样的发展本身就可以被质疑。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伦理应该成为对科学最基本的约束,而不是像某些科学家们所主张的,顾及伦理会阻碍科学的发展,因而不应过多考虑伦理。如果说,确实因为坚持最重要最基本的伦理价值而阻碍了科学的发展,那种阻碍也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正是这种对伦理的关注,才有可能保证科学自身不会成为反人类的工具。
□你的设想无疑是正确的,不幸的是有些科学家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将伦理道德的戒律,以及伦理学家的忧虑和告诫,都视为“科学发展”的绊脚石。例如,在2015年9月27日《文汇报》报道的一次关于基因组编辑与生物技术伦理安全的讨论中,卢大儒教授激动地表示:“中国的伦理学界不应该也不会成为反对科学和阻碍科学发展的卫道士”,那么他对伦理学界所抱的期望是什么呢?他要求伦理学界“为科学研究保驾护航”“为科学的发展鸣锣开道”!想想看,科学到了今天,它还需要什么“鸣锣开道”和“保驾护航”吗?它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伦理学界在今天的天职,恰恰就是要帮助社会勒住这匹野马的缰绳——如果还有缰绳的话。在今天,伦理学界应该理直气壮地扮演“刹车装置”和“减速装置”的角色。
还有一些科学家,经常以某件事情(比如基因组编辑)“外国人已经做了”或“已经准备做了”作为理由,急着要求政府同意他们也跟着做。“外国人已经做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做”成为一种常见的质问。我国政府和有关管理部门在有些问题的监管方面所采取的慎重态度,被他们指责为“不作为”。其实,正如许智宏院士所指出的:“过去,我们一直信奉‘科学无禁区’,但事实上在每一个领域,科学家还是有不可跨越的红线。”那些跨越红线的事情,外国人做了难道就能成为我们也跟着做的理由吗?
■实际上,我们还经常会听到另外的说法,即许多科学家之所以愿意在中国做研究,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对于科学实验的各种限制要比中国严格得多,所以一些人更愿意在这种更加“宽松”的环境中进行研究。其实,这种“宽松”,才是有关管理部门真正不负责任的“不作为”。
过去,环境问题也是类似的,后来更多民间的监督和干预参与进来,但就科学研究来说,由于其专业性,非专业的公众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又有着相当的困难。因此,对于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要求就更高,对于提高科学家们的伦理意识的教育就更加迫切。虽然近来国内在这些方面似乎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好的改进,但离理想的状态仍有很大差距。
所以《违童之愿》这样的著作,至少在唤起公众的警觉,以及对那些还有良知并愿意关注此类问题的科学家们的警示和教育,显然都有重大意义。虽然我对于这些问题的改进并不乐观,尤其是我们仍处在科学主义如此严重的思想环境中。但《违童之愿》这类著作的出版,作为具有反科学主义倾向的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将这种对科学伦理的关注纳入到既面向公众也面向科学家的“科普”中去,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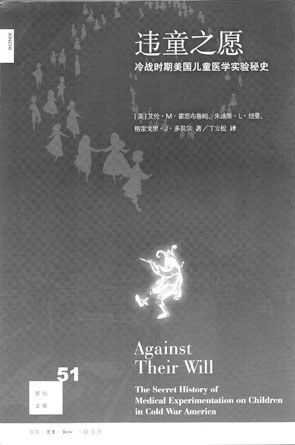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