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满怀喜悦之情阅读了黄爱平教授主编的《清史书目》,感觉这部大型工具性图书编纂主旨明确,著录齐备,体例规范,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颇值得推荐评介。因仅就该书(以下简称《书目》)编纂的主旨、特色、价值及不足,略予评说。
一、《书目》编纂的主旨
从是书《前言》可知,此书之编纂缘起于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当时,黄爱平供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推动清史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认为有必要从学术史角度,梳理清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脉络,考察百年间清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分析各个时期清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轨迹与特征,总结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与利弊得失,进而展望今后清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前进方向。由此出发,该所成立了由戴逸、李文海两位清史大家领衔主持的“百年清史研究学术史”课题,并申请重大项目且获准立项。《书目》的编纂正是作为此项课题的基础工作而启动的。正如《凡例》中开宗明义所说:“本书收录自清朝灭亡迄今,即1911年至2011年百年间中国境内以汉文发表、出版的清史著述(含译著、论集、工具书等),整理影印的清代文献档案资料等。期冀全面展示学界既有成果,为学者研究提供便利。”
《书目》不仅有明确的编纂主旨,而且还组织了很强的编纂队伍,主编黄爱平教授既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名家,又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专业的学术带头人,且有清史研究所为支撑,能组织动员一批教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参与《书目》的编纂。从《书目》扉页开列的名单可知,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达三四十人之多。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团队,在精心设计了编纂程序和工作方法之后,全体编纂人员经过两年多的辛勤耕耘,终于编成这部有很高质量的书目著述,殊属可喜可贺!
二、《书目》编纂的特色
约略言之,有如下数端:其一,规模宏大,时间跨度长,涵盖面广。《书目》全书著录各类书籍达四万余条,近二百万字。如此宏大规模,实为近年来已出版同类书目所罕见。再者,其收录书籍的时间范围,上起1911年清朝灭亡,下迄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时间跨度长达百年,基本囊括了百年间出版的各类清史研究著作与文献档案资料。
其二,体例规范,类目细致,编排合理,收录完备。我国古代著名目录学专家郑樵曾说:“类书(即类例)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编纂《清史书目》这样的目录著述,理应弘扬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制定出有章可循、切实可行的体例与类目。从《书目·凡例》中可见,该书对体例与类目的设置,可谓细致规范,既揭示出全书的主旨与收录范围,又对书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有明确具体的规定。例如“本书目收录著述以有清一代(1644—1911)历史的研究为范围”,但考虑到历史发展有其连续性,又规定“其中有关涉明朝末年以及民国初年者,亦予收录”。再如,对收录的各类图书“均著录书名、责任者、出版者、出版时间”等项,鉴于一些有影响的重要典籍或名著,曾先后在不同时间由不同出版社出版或再版,为使读者了解该书不同版本的流传情况,又规定“同一书若出版者或出版时间不同,则分别予以著录”。诸如此类的各项规定,使得全书整齐划一,条理分明。
《书目》上编收录“研究著作”,下编著录“文献档案”。其下再根据书籍的内容与性质,分别设置大类、小类,乃至小目。如上编所收研究著作,即按内容分为:总论、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边疆民族、宗教结社、教育科举、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文物考古、历史地理、中外关系、人物,凡十六大类。各大类之下,又进而划分小类,小类之下或再分出小目。以文学艺术类为例,其下即分为文学、艺术两个小类,小类之下又各分小目。如文学小类之下,便分为通论、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小说、散文、诗词、语言文字及其他,共七个小目。正是因为全书设置了比较完善的由编而类而小类,再到小目的类目体系,从而使数万种书籍有条不紊地各归其类,各入其目。
其三,将研究著作与文献档案资料汇编于一书。由于清史学科领域已有成果本身呈现的特点,不仅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性著作,还有对有清一代存留至今的大量文献档案的整理与编纂。特别是清代档案,作为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是否利用及此,往往成为衡量一部清史研究著作学术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有鉴于此,《书目》编者毅然决定既收录研究著作,又著录文献档案资料,以期全面反映百年清史领域已有成果的完整面貌。
三、《书目》编纂的价值
其一,全面展示百年清史研究的整体面貌。严格说来,现代意义上的清史研究,应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后为开始,迄今已走过百年历程。清史研究自身也经历了发展演变的各个阶段。如辛亥革命前后,曾兴起一股“清史热”,其研究内容和立场观点大多从推翻帝制的政治需要出发,充斥着排满仇满的思想观点。而后北洋政府设馆纂修清史,由于参与编纂的人大多为清朝遗老,不免站在清室立场为清朝统治歌功颂德,其编出的《清史稿》虽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仍称不上是科学的清史之作。此后,涌现出孟森、萧一山等老一辈清史学家,他们或搜集整理大量史料进行实证性清史研究,或编撰全面系统、翔实厚重的一代通史,为清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其时代的局限与烙印也十分明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清史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逐步出现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论著,但受机械唯物论与片面的阶级斗争观的影响,研究内容多偏重在政治史、经济史方面,对诸多领域的研究都付之阙如。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清史研究才焕然一新,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的启动,又将整个清史研究推向新的阶段,提高到新的水平。伴随国家清史编纂十多年来的进程,清史研究的论著更加丰富多彩,大量的清史文献档案(包括海外)资料得到整理出版。《书目》既全面地展示了清史研究成果的整体面貌,也反映和折射出百年来清史研究发展演变的脉络及其得失。
其二,为读者提供治学津梁和读书门径。清代经史考据大师王鸣盛曾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涂,方能得其门而入。”诚如其言,目录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清史学者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有必要了解清史学界的研究状况,哪些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哪些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有哪些难点尚待突破,又有哪些空白尚未填补等。对初学者而言,有必要了解清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需要读哪些书,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应该向哪些方面开展和深入等。这些问题,《书目》都可以提供参考。
四、不足与有待商榷之处
在肯定《书目》编纂的主旨、特色和价值时,也有必要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和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
其一,有所遗漏。尽管《书目》的著录已比较齐备,却仍有遗漏。举要言之,如上编总论之中国通史类下,遗漏了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系列中属于明清时期的第九册和第十册;明清史一类则遗漏了孟森著《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
其二,尚有讹误。《书目》对书名、责任者等义项的著录时有讹误,如第117页《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一条,其中的作者“湖滨”应为“胡滨”。第251页《清代理学史》上、中、下三册中册著录为“张昭军”,下册“李帆”。事实上应为中册“李帆”,下册“张昭军”。
其三,重复著录。《书目》对书籍的著录还有前后重出的情形,如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一)、(二)、(三)、(四)、(五)凡5册,既见于《总论·晚清史》一类,又见于《政治·通论》一类;卞僧慧著《吕留良年谱长编》,既著录于上编《人物·单传》一类,又收录于下编《史部·传记》类。如此等等。
实事求是地说,编纂一部工程如此浩大的工具书,且出自众人之手,存在一些疏误,势所难免。然而,作为一部研究清史常备的工具书,理应精益求精,反复核校,以最大限度减少差错,避免误导读者。
《书目》之所以出现上述讹误,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这与该书在编纂体例上类目的设置过多、过细,似乎也有一定关系。以总论一类为例,其下设有15个小类,其中既有“清朝通史”,又有“历朝”(包括入关前和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宣各朝),还有“晚清史”。而史学界所说的“晚清史”,一般即指“道、咸、同、光、宣”各朝。这样的设置,极易造成所收各书在时限与内容范围上的重叠。此外,人物类下分设“单传、合传、总传”各小类;论集小类之下,又分设“一般论集、个人论集、会议论集”等小目,皆不免失之过细。因此,如何使《书目》的编纂体例及类目的设置更加严谨和科学,还可再加斟酌与商榷。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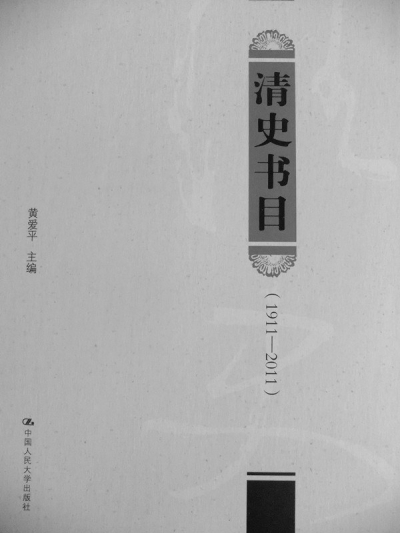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