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1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信息时代的文学教育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等专家学者,鲁迅文学院第26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文学评论班)的学员,教材编写者太原师范学院傅书华教授、阎秋霞副教授等30余人出席了座谈会。与会者除围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展开讨论之外,还论及当下高校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前沿问题。会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的主编傅书华教授接受了本报采访。
读书报:拿到这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综合教程》,觉得有些惊讶,它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大学教材的样子。一般教材都是编写者以自己的讲述向学生传授该学科的知识,而这套教材,编写者“站出来”讲述的篇幅占了很小的比例。每节7个部分,只有第一个部分“内容提要”是编写者的讲述,占篇幅最大的是“评论摘要”部分,篇幅数倍于前者。给人的感觉是,作者隐身了。请问你们何时、为何会想到以这样的方式来编这套教材的?
傅书华:那大概是在2006年左右,当时我已经在教学一线工作多年,对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有很多的切身体会。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来说,体会最深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大多数教材,学术专著的属性更强,教材的属性较弱。在我看来,教材要针对特定的教学对象,设置特定的教学内容、目的、方式、方法,最终落实于对学生的培养效果等等。学术专著型的教材,容易形成教师灌输式、演讲式、照本宣科式的教学。
第二,学术专著可以用著者某种理念统领对文学史的理解,但在教学中,却不宜如此。现在的学术专著型教材,用于教学中,往往把教材的观念预设为对文学史正确的理解,养成学生不是从作品实际出发去理解作品,而是用一种先行预设的观念去进入作品的习惯。这对新一代学生的培养是不利的。
第三,现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主要还是受西方范型的影响,对中国传统相对忽视。西方的文学史教学范型,总想在“史”的发展中,找出一个能够体现本质性规律性的理念来作统领,是以“概论”来作文学史的“本体”。而中国传统的人文教学,却是选一些在历史中经反复淘洗过的经典文本,再加上其后历代文人学者对这些文本所作的注与疏,或者对这些文本所作的经典性的阐释,来作学习者学习的对象,是以“文本”作为“本体”。这样,学习者接受的,不是对经典文本当下的既定的结论,而是一个对经典文本不断加深理解而且予以丰富的“生成”的过程。我们这个教材,之所以把很大的篇幅,给了“评论摘要”部分,而又严格考核学生对经典性作品的阅读数量,就是想学习中国这种传统的人文教学范式。
当然,这种设置与我们更多地强调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与我们对课堂教学范式与考核方式的改革的努力是非常吻合的,但如果展开谈,那说的就太多了。
读书报:7个部分中,有“精读作品”、“泛读作品”的推荐,有文学研究成果的“摘要”和“索引”,这4个部分都“链接”着书外的文本,使得整本教材像是一个“超文本”(ht-ml),或者说像是互联网上一个平台。正好关于这套书的座谈会的主题是“信息时代的文学史教学”,那么,是否这套书的编写是为了适应互联网的时代?
傅书华:你概括得很准。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学生都可以在网上比较容易地搜集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包括过去教师在课堂中要告诉学生的各种具体的知识。我们编写的这本教材,有点像一个学术向导,告诉学生这些学术的“门”“窗”在哪儿,引导学生有目的地自己进去看一看,然后在课堂中,检查、交流、深化一下学生看后的观感。譬如我们刚才提到的“评论摘要”部分,其作用有三:一是作为淘汰过程,以此构成对入选“评论”的“经典性”“史”性的肯定;二是以此把历年来对某一文学现象某一个作品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的“门”“窗”介绍给学生;三是因此而培养学生不是习惯于“一尊”,而是“对话”的思维习惯。这种编选,其实难度挺大,很考验编选者的学术眼光、“史性”眼光。我们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便利,会极大地改变原有的教学范式,我们应该正视这一问题。
读书报:这套教材强调鼓励和引导学生多读作品,不知当前中文系学生阅读作品的状况如何?
傅书华:很不乐观。学生往往没有看过作品,只是用学术专著型教材中对作品的既定理解来代替自己对作品的判断,有时是通过作品梗概或者影像来了解长篇作品的内容。如此结果就是,学生用既定结论对作品的理解看似深刻,但审美感知能力很弱。现在,各个高校都在强调学生对作品的实际阅读,包括童庆炳老师的《文学概论》教材,也强调学生对历史上各种文论原典的阅读。我觉得,学界对此的重视是非常及时的,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教学中通过有效的手段来落实这一点。
另外,我常常很悲哀地看到,学生在刚刚进入中文系时,还是有较好的文学才情的,但在四年的教学规训下,这些才情消失了。往深里说,“个人”在各种各样的“整体”规训下消失了,这恐怕是很大的问题。
读书报:文学史既是教授文学,也是教授文学的历史,或许会有一个文学本位还是历史本位的问题。如果强调以文学为本位的话,则像杨朔散文也许就不必单列一节来写;如果强调以历史为本位的话,则以杨朔散文在当时的影响,作重点的分析和研究似也合理。请问您如何理解“文学”与“史”的关系问题?
傅书华:确实,有些作品,在作品出现的特定时代,影响极大,但文学性并不强,有些作品,在最初出现时,影响不大,但事后其文学价值却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就拿我们教材中的“十七年文学”来作个例子,陈思和所说的“潜在写作”在当时影响不大,但却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及呈现当时精神生态丰富性的价值,而类如《艳阳天》《欧阳海之歌》,当时影响挺大,但文学性很弱。
当然,但凡在一个历史时段产生时代性影响的作品,总是比较典型地体现了那一个时代的精神形态、价值形态,因之,都有予以研究的意义。现在的许多学者,侧重研究十七年文学作品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看来,故事讲的什么,也仍然是特别值得加以研究的。即如您所举的杨朔散文,其作品作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帜,其精神特征,也贯穿于当时的小说、诗歌、戏剧乃至当时的人生教育之中。那么,杨朔入选,也就有较为充分的理由了。只是在十七年文学中,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所以,所选作家作品不需要多。
读书报:当代文学部分,1976年之前那一段冠以“工农兵文学”的题目,受到一些专家的质疑。包括文革结束到1980年代末这一段被名之为“新启蒙文学”也未必能获得一致认同。为什么没有采用比较通行的“十七年文学”,或者单纯时间概念的“八十年代”这类不容易产生争议的提法?
傅书华: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种命名,出力不讨好,很容易不被认可。我们的想法是,对一个文学时代,如果有一个标帜性的命名,对于学生记住、理解那个文学时代的特质,可能会有所帮助。譬如我们将“十七年文学”命名为“工农兵文学”,是因为自延安时代形成的“工农兵文学”在“十七年文学”中居于主流位置,其它处于支脉、边缘的作家作品,如路翎、宗璞、汪曾祺等等,我们是将其作为“工农兵文学”的“反题”列入的。
读书报: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谈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教学改革中,四学期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被拿掉,代之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原典精读”,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由两学期改为一学期,原来一学期的当代文学史课程则不复存在。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张晓琴也谈到,她所在学校的当代文学史课程已减掉了18个学时。这是否表明文学史课程在大学中文系里遭遇到某种危机?
傅书华:我是非常赞同北师大这一教学改革的。在我看来,这也是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价值动荡以及重新建构价值体系大厦在文学教学中的反映,那就是,不再信任原有文学史中的价值判断,而是要通过直接“回到事物本身”“直观事物本质”。取消现有的文学史课程,不是不要文学史课程,“原典精读”一定不是静态的封闭的对某一作品的解读,而是在文学长河中对作品的解读,所以,它是另外一种形态的文学史课程。如果你说这是文学史课程在大学中文系遭遇到某种危机,我觉得,表述为原有文学史中的价值理念、价值体系在大学中文系遭遇危机,更为准确。
读书报:就我所知,您在区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领域,都有着很好的研究成果,现在,您又主编再版了这样一套实用性很强的教材,您怎么看待高校教师的科研与教学的关系?
傅书华:重科研轻教学,是中国所有高校都存在的弊端,其中原因甚多。结合这本教材,我想说的是,就教学本身来说,它拿不出足以证明教师学术水准的依据来,也是被人所轻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教学改革,似乎仅仅是教学方法的改革,而不是对学术能力的考量。我们这本教材,其中的一个想法,是想提高教学中的学术水准,并成为考量一个教师学术水平的尺度。譬如,教材中的“评论摘要”部分,要求教师对所讲授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主要研究成果的切实把握,并以此指导学生搜集阅读相关文献资料,在与学生的对话式教学中,培养学生对作品的审美能力与研究能力,这些,没有相当的学术积累与学术水准,是不能完成的。
我一直觉得,我们民族在治学上,重经院,轻原创,轻应用。我们编写这部教材,属于应用范畴,又在应用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反抗经院对学生的规训。感谢贵报给我这样一个表述我们教材编写理念的机会。谢谢您。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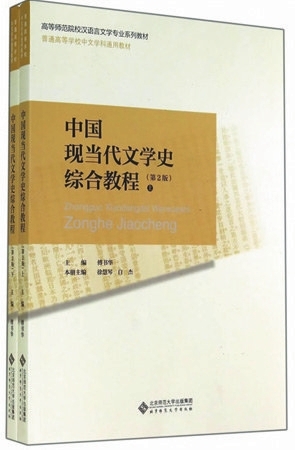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