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41卷目录
“二十一世纪”三十年风云录
胡平
一时的文学与永恒的文学
—如何评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李建军
创办周刊的回忆 潘振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何倩
送别严秀 陈四益
张季鸾:大变动时代的报人典范 傅国涌
在板门店 茅建海
自由引导人民 萧文泉
一个人的诞生 汪家明
苏联的最后一天 康纳·奥克莱利
保护长江生态的最后底线 杨欣
粟裕漫长的申诉之路 张雄文
想到张季鸾,我竟然同时想到了大胡子的爱因斯坦,这个念头貌似很荒谬,但是也不全然荒谬。一九二二年爱因斯坦一生中唯一一次来到中国,他们曾在上海同桌吃过饭。一九三○年,爱因斯坦写过一篇文章《我的世界观》,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
我想这句话可以用来评价张季鸾,他就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
张季鸾很不幸,他生在了一个战乱连绵、动荡不安的时代。张季鸾又很幸运,他生在了一个个人还可以成为有尊严的个人的时代。所以他作为一个普通的记者,一个普通的报人,竟然可以凭着他手中的一支笔,影响一个时代。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新闻史,更重要的是,影响中国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
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大致上是由三代人书写的,即(一八)八○后、(一八)九○后和(一九)○○后。八○后的代表是宋教仁、鲁迅、蒋介石、张季鸾。九○后的代表是一八九一年生的胡适之,一八九三年生的毛泽东,还有晏阳初、陶行知等都是九○后,二十世纪的思想史、政治史大致上是他们这些人书写的。○○后的代表人物是一九○四年生的邓小平、一九一○年生的蒋经国,他们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海峡两岸,一直到今天。
八○后的张季鸾,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一年他主持《大公报》笔政的这十五年间,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到他去世,中国报纸获得迄今为止最高的国际荣誉——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奖章。这十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张季鸾时代,张季鸾生逢其时,死得其所。他死后举国哀荣,超过同时代所有死去的人。国共两党、举国新闻界、知识界一致表示哀悼。
在张季鸾身上包含了太多值得我们回望的因素,我想用三个字来概括他一生的作为:
第一个字是“容”,有容乃大的“容”,不仅《大公报》在他掌笔政的十五年中,能包容各种各样有才华的年轻人,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萧乾,乃至左派的范长江、杨刚,还有很多在新闻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这些其他的报纸也能做到,他的有容乃大,更重要的在于与外部的合作,《大公报》在那个时代,做到了一件事,他和中国当时非常重要的几个知识分子圈子有极好的合作关系:
第一个是胡适所代表的北大、清华教授圈子,一九三四年元旦开始,《大公报》推出的“星期论文”就是他和胡适圈子的合作。“星期论文”最开始约了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个撰稿人,后来扩大到两百多个作者,以胡适圈子为核心,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这一脉络的精华。
第二个合作关系从一九二八年开始,是跟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等人的合作。南开经济学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最好的经济学院,方显廷和何廉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经济调查,把当时中国的工业和手工业情况进行了摸底,他们把所得到的学术成果用通俗的表格和文字形式陆续在《大公报》上发布,对中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们的团队一直和《大公报》合作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大公报》重心南移,天津《大公报》停刊。《大公报》先后办过《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统计周刊》,都是和这个经济学圈子的合作。
第三个是定县的乡村建设圈子,晏阳初所代表的一批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留学回来拿到过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哲学、戏剧等博士学位的人,他们放弃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在定县进行乡村建设,出了很多成果,不仅是学术成果,直接在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上有很大贡献。定县乡村建设是一九二六年开始的,两年后,乡村建设的实验刚刚有一点起色,张季鸾们就注意到了晏阳初们所做的大事。第一个被派到定县采访的是徐铸成,《大公报》为此给他开辟了一个连载的版面,连载徐铸成发回来的详细通讯,并且配发了《大公报》另一位掌门人胡政之写的社评,对于定县的实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定县不是做戏,不是精英表演给乡亲们看,而是精英真正生活在乡村中,与乡亲们融为一体,这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大公报》的报道开启了与晏阳初这一圈子合作的基础,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后来他们又继续跟进报道,还一起合作创办了《乡村建设》周刊。
第四个圈子,他们于一九二七年就开始与学衡派的代表吴宓有良好合作。一九二八年元旦,《大公报》开辟了文学副刊,由吴宓在北京组稿。吴宓只写文言文,长于古体诗,反对白话文,代表中国文学的旧派,同时又是哈佛高才生,中西兼通,用西方哲学和文论概念来研究中国的《红楼梦》和古典诗词,也是别出心裁。如果说张季鸾和吴宓的合作是因为他们都是陕西人,都是陕西旧学的书院里出来的,这还可以理解。但是白话文写得不大好的张季鸾,同样能够接纳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沈从文。
第五个圈子,即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圈子。一九三○年代,张季鸾结束与吴宓的合作,开始与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新文学派别的良好合作。以后中国文学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首先发在《大公报》或其附属刊物《国闻周报》上,包括传世之作《边城》也首发于《国闻周报》。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沈从文的手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首发的。
《大公报》的副刊发掘了文学史上一位又一位的作家。一家报纸的掌舵人,有这样的胸怀,能够与社会上方方面面的知识分子圈子有那么深的关系,有那么良好的合作,这是很难的。中国人向来都不擅长于合作,但张季鸾超越了这样的民族性格,在他掌握《大公报》的时期中,他有足够的包容和胸襟与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合作。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留日出身的,《大公报》的几个重要人物都是留学日本,胡适的知识分子圈子是留美、留英的。以往有一种观点认为,留学欧美与留日的学生是天敌。北大教授当中,留日回来的是浙江人多,留学英美回来的是安徽籍的人居多,所以留学英美回来的与留日回来的人,又被看作是皖籍与浙籍的地缘、地域之争。以我看来,这不是留学地点之争,也不是地缘之争,而是意气之争。一个留日背景的学生,可以与留美回来的晏阳初们,可以与没怎样上过学的沈从文们,都可以合作得很好。这太令人意外了,我一直没看懂,不大明白凭什么他有这样一种有容乃大的气度。我大致猜想:张季鸾比较文人气,他是把自己看作文人的。张季鸾身上有一个“容”字,这在中国的土地上特别难得。
第二个字,我觉得他身上有一个“诚”字,诚实的诚、诚恳的诚,无论做人处世还是写文章,他都充满诚意,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现实,诚实地面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笔下句句都是真话、句句都是实话,因为他句句出自真诚,句句都发自肺腑,哪怕是别人不喜欢听的他也要说。如果说,一个报人要说一些当权者不喜欢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这叫有风骨、有肩膀,可以获得掌声,虽然这样做的人也不多,其中有的人这样做就被杀了,“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林白水在一九二六年都被杀了,史量才一九三四年也被暗杀了。但是,一个人要说得罪大众的话,得罪很多读者的话,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张季鸾敢干,而且干得最多的就是这件事,得罪大众。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张季鸾提出的“四不”方针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并不是“不党”,也不是“不私”、“不卖”,而是“不盲”。“不盲”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盲从于大众的舆论。看上去张季鸾真的是生不逢时,生在了“九一八”以后的中国,但是他又生当其时,生在“九一八”之后的中国。“九一八”,距离他生命的终点还有十年,这正是他一生当中的黄金时代,这十年给他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发挥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是留日学生,他懂日语,他深知日本的国情,深通日本的国民性,能把握日本人的心理,他的话句句能摸着日本的心思。所以,“九一八”之后的中国,《大公报》是挨骂的,《大公报》不知道挨了几次炸弹,有记载的是五到六次,其中三到四次是中国人扔的炸弹,要让《大公报》、张季鸾吃炸弹,有一次是直接寄了一个邮包给张季鸾个人,他没有拆,那里面就是炸弹。因为他们不主张马上抗日,他们并不反对抗日,但不主张立即抗日。他认为中国现在抗日就是死路一条,立马就是亡国灭种。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间,《大公报》的言论始终跟很多报纸、跟整个公众的呼声是拉开距离的。这个过程中《大公报》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唾沫,张季鸾并不受大众的待见。但是,他跟胡适他们是相通的:都认为中国今天还没有能力跟日本开战,希望能够拖延时间,让中国的国力、交通、兵器工业都能够得到一定的预备,时候到了再跟日本有一战。选择这样一个立场,在当时中国就要得罪大众,就是不盲从大众,大众就要给你各种各样压力,但是他们对日本从来没有小看过,他们始终把日本看作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
我们都知道《大公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破天荒地开过一次编辑会议,做出一个最高决策,被称作“明耻教战”。“明耻”是要办一个专栏:“六十年来日本与中国”,让王芸生去编一八七一年以后的史料。“教战”即是请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来办一个军事周刊,向国民普及军事常识。“明耻教战”是《大公报》的决策,它是要抗日,但不是现在,而是将来。他们的决策正好与蒋介石的决定不谋而合。蒋介石也是留日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留学日本的学生,他们对日本的认识要远高于当时中国的一般大众,也远高于很多对日本没有认识的知识分子。这就是《大公报》的厉害,一个人可以这样影响一个时代,一个报人可以这样影响一个时代。所以他曾私下说:“一个记者就像是一个政治家。”他亲口对徐铸成说,做一个记者跟做一个政治家是一样重要,有的时候可以影响国事。他这么看也是这么做,所以充满了自信,不仅充满了知识上的自信,也充满了道德上的自信,更加充满了职业的自信。
张季鸾不是做教育的,但是他做报纸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报纸不是包子,包子只能满足我们肚子的需要,满足不了我们精神的需要。但是报纸不仅可以满足我们物质的需要,它在物质上可以用来包花生米(张季鸾说,他写的文章上午还有人看,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而且可以满足我们精神上的需要,可以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我们去应对各种的艰难、挑战。我说张季鸾作为一个报人对于自己的职业有自信,事实上他在《大公报》的十五年和他办《大公报》前的十五年,他一生三十年的报业生涯充分体现了,他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诚”字,诚实地面对,一个人只要诚实地面对自己,诚实地面对别人,诚实地面对世界,他就有尊严。
张季鸾的第三个字是“勇”,他有容,有诚,都是需要有勇气的,需要有所失去,并不是得到。这样的勇气在我看来,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勇气,第一是不盲从大众的勇气,这是最大的勇气;第二是承担责任的勇气,无论选择什么,你自己和所在的报纸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三是直面现实的勇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你都要挑起来,都要面对。
日本人打过来,“九一八”发生了,要面对,不能闭着眼说日本人没打过来。卢沟桥打起来了,也不能说还是“九一八”的那个状态,所以“七七”之后,《大公报》的选择是全力抗战、焦土抗战。所以,他在《大公报》汉口版写了几篇影响中国至深的社评,比如《最低调的和战论》《置之死地而后生》等,那都是当时应对现实的需要写下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张季鸾在他的一生中,如果论文章,他未必是完美的,未必是无懈可击的。但他确实做到了用他的文章去影响他的时代,他是有诚意的,有勇气的,所有的一切取决于他的责任意识,需要有表达的技术,更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本文作者傅国涌,摘自《阅读MOOK》第41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5年5月出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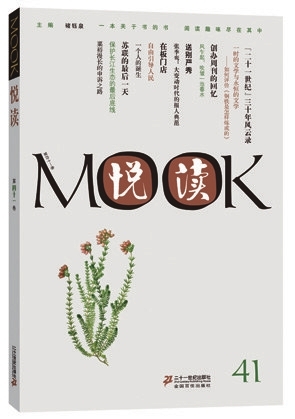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