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刘兵
□让我们先以一则科学八卦开头吧。安德鲁·布朗在《科学圣徒——J·D·贝尔纳传》中文版序中说,1954年贝尔纳访问中国时,曾被要求提供一个适合中国大学博士生(研究论文)选题的清单。布朗相信,贝尔纳“显然能够拿出数十个好主意来”,不过他不知道当时贝尔纳的这些主意有没有被中国采纳,也不知道这些主意是否对当时正在快速成长的中国科学界产生过什么影响。布朗认为,此事对于当今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有趣的课题。这个看法我十分赞成——它本身就可以成为博士论文选题。
引起我对这一则八卦感兴趣的原因,至少有两个:
一是如今在中国,有价值的博士论文选题已成稀缺资源。不信你随便找一位博导,让他当场开列“数十个”博士论文选题试试?当然,在这则八卦的叙述中,布朗的措词可能会引起一点问题——在1954年的情况下,“中国大学博士生选题”和今天同一措词的意义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一定要类比,我想这至少应该相当于今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吧?
二是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J·D·贝尔纳(Bernal)生于1901年,那个时代的英国知识青年中,有一个大大的时髦——正如布朗在中文版序中所说的,“就像许多一战后的学生一样,他的政治信仰被塑造成了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当我们谈论贝尔纳时,这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
■我倒是真没想到,在我们商定谈贝尔纳的传记之后,你开篇先会提出这个有些“八卦”的话题。当然,这也还不能算是一个完全八卦的话题。因为我们商定要谈贝尔纳,其实也还有另一个背景,即我们这一代在国内学习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人,从一开始,差不多没有没读过贝尔纳的书的人——毕竟,那时国内有关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资料奇缺,而贝尔纳的两本书《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是当时为数不多相对方便找到的读物。
不过,说到你说的这件轶事,还需要再讲一些你还没说清的背景。从你说的那篇序来看,当时贝尔纳来访时,还曾“大多数时间都在做报告,经常每天四五个小时,演讲的科学主题也非常广泛”。但作序者却同样没有提及这些报告的题目是什么。把这两个背景再结合起来,也许我们还可以存有疑问的是,在当时那种特定的形势下(当时科学界的国际交流并不多),邀请贝尔纳来访、请他做报告,甚至要求他提供博士论文的选题时,究竟是主要把他当作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呢?还是主要当作一位以科学作为对象进行历史和社会学研究的专家呢?抑或是两种身份兼具?相应地,我也可以据之猜想,当时想要请他提供博士论文的选题,是想要他提供具体的科学研究的选题呢?还是科学史或科学社会学的选题?
这样的疑问显然是又有一些潜台词的,因为,毕竟我们这次会选择谈贝尔纳的传记,又正是因为他的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的身份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虽然我们是因为贝尔纳的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身份而选择他的,但我几乎可以肯定,当时中国方面主要——如果不是完全的话——是将贝尔纳视为一位科学家来接待的,对他的期望也主要是在科学方面。因为在那个时期,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之类的学科领域,几乎还没有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科学技术领袖人物的视野。
这样的推断是合乎常理的,因为中国当时急于将非常有限因而显得极为珍贵的资源用到“一阶”的科学技术发展上去。这让我想起已故何丙郁教授在谈到李约瑟——注意布朗将李称为贝尔纳的“伟大朋友”——时曾说过的一段话:“可是引述一句一位皇家学会院士对我说的话:院士到处都有,我从来没有听说李约瑟搞中国科技史是英国科学界的损失;可是在50年代,要一位钱三强或曹天钦去搞中国科技史,恐怕是一件中国人绝对赔不起的买卖。”我前面将布朗所说的贝尔纳的选题类比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而不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正是出于对这种背景的认识。
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回到贝尔纳本人身上来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包括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背景,类似贝尔纳、李约瑟这样“左倾”的科学家,总是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受到特殊的欢迎?如果这个判断可以成立,那么随之而来的,对于他们的学说或著作在中国一两代学人心目中获得的某种特殊地位(例如你上面所说几乎无人不读贝尔纳书的情形,本书中译者在“译后记”中也生动展示了这方面的例证),我们作分析和评价时,也就需要注意这个维度了。
■你看,这样说来,就可以将当时的某些背景显示出来了。你最后问的,关于像贝尔纳这样的“左倾”的科学家,会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受到特殊的欢迎的问题,对此,我似乎没有看到什么直接的证据,但从其他许多出版界的事例来看,这就是完全可能的。因为,那时我们这里对于图书的出版,还是控制颇严的,尤其是对于外国著作的翻译出版,那甚至会是学术界的“大事”了。因而,我们看到,在那个时期,我们这个领域仅有很少的国外著作被翻译出版过来,而在这“很少”之中,还有不少从一开始制订出版计划时,就是为了要对之进行批判的。
这样,由于当时我们这个领域的读物的匮乏,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是在(精神、学术)食品的短缺中成长起来的,是先天的营养不良,当然这种营养不良甚至会有某种后遗症。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准备考科学史专业的研究生时,要复习竟然几乎找不到什么正式出版的科学史著作。
一个相关的例子时,应该大约也是在那时吧,丹皮尔的《科学史》的出版,也对我们这个领域影响很大,甚至直到今日,许多论文和著作的参考文献、甚至在一些研究生的考试中,都会经常见到这个一百多年前首版的“古老的”科学史作者的名字。为什么丹皮尔的书当时也能出版,具体背景我不知道,但发展到后来,似乎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丹皮尔的《科学史》似乎比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在中国科学史界和其他相关领域里影响要更大一些。你觉得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猜想,一个重要原因,是丹皮尔著作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淡,而贝尔纳是“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的人,在他的著作中,或多或少会有这方面的影响吧。当然,要对这样的猜想进行学术论证是非常困难的。
布朗在《科学圣徒》中,对于贝尔纳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有不少论述。他说贝尔纳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立志尽他所能,用纯粹的应用科学为发展中地区造福”。贝尔纳多次到“他喜欢的国家”去度长假,这些国家里当然包括苏联和中国,通常都是由这些国家的科学院出面邀请。布朗说,贝尔纳对于这些邀请“不知疲倦并且容易请到”。在第19章中,布朗也顺便证实了我前面的一个猜想——中国是将贝尔纳作为一位科学家而不是科学史家或科学社会学家来接待的。布朗用稍带夸张的语气写道:“对于资源有限的新兴国家,‘圣徒’就是物理学、化学、晶体学、材料学和冶金学、建筑业以及农业专家。”他访问的国家当然还有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包括印度等国。
想想看,如此“左倾”的西方学者——李约瑟在这一点上和贝尔纳堪称异曲同工,当然会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享有其他西方同行难以望其项背的声誉。这显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你上面注意到的现象: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读者很少能够读到西方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著作的中译本,但贝尔纳的著作却得以一枝独秀。
■话题到了这里,我会联想到两个问题。其一,是关于贝尔纳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著作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其二,在仔细阅读此书时,人们会发现,在这样一部关于贝尔纳的详尽的长篇传记中,除了科学工作、生平、社会政治活动之外,竟然没有专门的章节对在我们这里更熟悉的贝尔纳的科学史家和科学社会学家的身份和工作做专门的介绍,尽管在不同的地方,曾简要地提到了他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的一些观点。由此,我们是不是能够推论,实际的情形是不是就像我们开头所谈的,不仅195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仅仅将贝尔纳作为一位科学家,而且就连在这本传记作者那里,也根本就没有重视贝尔纳在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中的贡献呢?
如果这种推论成立,那么,对于回答我刚提到的第一个联想,也许就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以参考的评价背景。也即,贝尔纳本人在国际上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领域中,地位和影响究竟是怎样的?连带地,就是在当年中国学者很少能够读到西方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著作的中译本,但因为种种原因贝尔纳的著作却得以一枝独秀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领域中,早期被引进的到底是什么样水准的学说?
□你所想到的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令人难堪的问题,即使曾经隐约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中国学者,多半也会下意识地回避这个话题。不过,当我们谈论贝尔纳时,我们就无意中为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语境。
首先,正如你已经注意到的,《科学圣徒》的作者布朗甚至没有为贝尔纳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工作安排专章——需要注意,本书包括“尾声”在内共有23章之多。对于这一现象,一个最容易想到的合理解释,当然就是:布朗不认为贝尔纳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工作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值得在一部有23章的传记著作中为它们安排专章。而且,布朗的这种判断,在西方学术界,好像还不是特立独行力排众议,而是至少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如果上面的推断不太离谱的话,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接踵而来了:既然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主要将贝尔纳视为一位“科学家”,那为何又对他的在西方学界看来仅属“玩票”性质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工作给予很高地位呢?对这个问题,仍然只能回到当年世界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旧战场上,才可能求得合理的解答。
其实我们不难理解,在当时的思想习惯中,科学技术基本上没有“阶级性”,没有意识形态属性,但是“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却被认为肯定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我们不会翻译丹皮尔的《科学史》,但是肯定可以接受贝尔纳的《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因为贝尔纳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并且相信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承诺”的人啊!
■对于贝尔纳的科学史著作很早就被引进,考虑到当年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这应该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答案。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看待、评价贝尔纳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著作的影响了。
在以科学为对象的人文研究,即像科学史这样的学科的发展初期,一些科学家而非科学史的专业人士的著作,曾在学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实,当时职业的科学史家还为数甚少,而且与后来不同的是,即使当时的为数不多的职业科学史家也大多是科学家背景。当然,科学家到科学史这类学科客串的传统,直到今天也还在继续着,也仍有少数做得非常出色甚至影响很大的,例如像写科学社会学著作《真科学》的齐曼,还有像原来的科学家后来成功转型成为科学史家(研究爱因斯坦和物理学史)的派斯(尽管对其科学史研究也仍有不同的评价),但这些突出成功的事例毕竟是极少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贝尔纳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在这些学科中,就算还有些影响,也不能说是第一流的,以至于连其传记作者都未曾认真看待。但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较早地引进中国,对中国的这些学科的发展又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不过,在这些学科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前沿学术的意义上,也不必过于高估其学术价值了,而更应关注那些更能反映当下学术发展水平的作者和著作。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更新一代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生中,贝尔纳的影响已经远远不像在更老一些代际的学者中的影响了。在中国,随着学科的发展,科学史也在告别其青涩的少年时代吧。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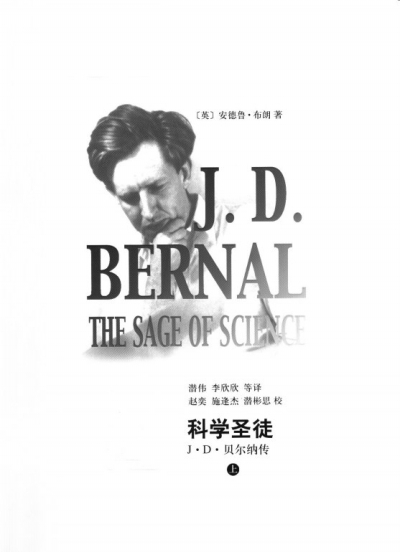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