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勒是带着遗憾、忧虑甚至一丝“绝望”离开“熊猫项目”的。2008年他再来中国,却发现当年种下的种子开了花——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大熊猫保护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乔治·夏勒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大熊猫及野生动物保护界几乎无人不晓。1980年,也就是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国门初开的时候,他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委托来到中国,开始大熊猫保护的调查和研究(“熊猫项目”)。他与熊猫专家胡锦矗等中国同事一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在四川的深山竹林里整整坚持了5年的野外科考,为人们认识大熊猫,建立保护理念开了先河。
作为“熊猫项目”的成果,他与胡锦矗教授合著了《卧龙的大熊猫》这部科学文献;同时,他将自己5年中的思考与感触写成《最后的熊猫》一书,这是一本更加带有科学家个人色彩的纪实性作品。
正如夏勒所说:“20世纪80年代在熊猫漫长的演化史上极为重要,也是文献最详尽的时期。这期间的事件若不逐一记载,难免会被遗忘。我以科学使者的身份前往中国,去了解和记录,为一种不能言语的生命充当翻译,把熊猫的生存状况留诸后人。这本书就是那笔遗产的一小部分。”
在“作者序”中,夏勒说,熊猫是“一个集传奇与现实于一身的物种,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神兽”,它“跳脱出它高山上的家园,成为世界公民,它是我们为保护环境所付出努力的象征”,“能跟熊猫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演化历程发生交错,是我们的运气”。WWF在1961年就将大熊猫作为自己的会徽,并发表宣言:“大熊猫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珍视的自然历史的宝贵遗产。”中国刚一改革开放,WWF就通过美国驻港记者南希·纳什与中国方面联系,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
从书中我们读到,夏勒和他的中国同事,是怎样爬冰卧雪,风餐露宿,坚守在海拔2500多米的卧龙“五一棚”营地,日日夜夜对野生大熊猫的活动情况进行追踪和观测的。他们测量留在密林中的大熊猫足迹、粪便,统计大熊猫吃过的竹子,每天还要将熊猫粪便背回营地,称量后进行分析,借此搜集四川大熊猫种群现状、栖息地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冬季天寒地冻,他们在野外观测,只能以冻得硬邦邦的干粮充饥;夏天要忍受蚊蝇蚂蝗的叮咬,全身被露水和雨水湿透时,只能用自己的体温烤干。在最酷烈的环境考验之下,他们一天天重复同样的工作,而常常会一无所获。但他们不以为苦,反而乐在其中。
然而毋庸讳言,在这本书中我们读到的经常不是高昂的情绪,而是沮丧、无奈甚至愤怒。夏勒性情鲠直,以直言著称,他深知“生物学家不仅要研究自然,也要促成保护行动”,而行动,就一定会“涉及政治层面”(《作者序》),何况熊猫本来就是“政治动物”。
他写到合作双方因动机和理念不尽相同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艰难谈判,写到对官僚体制的低效及地方政府打击盗伐盗猎行为不力的不满,写到作为外国人在一个陌生文化里感到的孤独,也写到关于大熊猫珍珍的一场观念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以中外专家夏勒和胡锦矗为一方,反对给经常造访营地的雌性大熊猫“珍珍”喂食,以免她对人产生依赖。他们的理念是,不要去打扰和干预自然状态下的动物,保护它们的栖息地,远远地观察它们;哪怕因为距离的原因,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取得一点研究进展,也尽量不要干预。另一方是几位初出校门的年轻人,他们舍不得放走珍珍,瞒着教授们继续喂食,以致珍珍经常来蹭吃蹭喝,登堂入室,还引来一些围观者。这可把夏勒惹恼了,他给中国有关部门领导写信,说珍珍的事已对“五一棚”的研究工作构成了干扰,“五一棚”已从研究营变成了观光营。后来有个新华社记者把这事写成内参,惊动了中央。国家林业局专门派来调查组,几个年轻人被撤了职,珍珍也被人抬着放归到离“五一棚”十英里的地方。这时她已经十七八岁,相当于人类的老年。无线电监测表示,她一直朝“五一棚”方向移动,足足走了39天,终因年老体衰,又经过两次长途跋涉,最后死在了“五一棚”自己的巢域附近。
珍珍是夏勒最早捕获,戴上无线电项圈进行观测的熊猫,夏勒对她感情很深。这件事令夏勒耿耿于怀,他由此对中国的熊猫保护事业忧心忡忡,做出比较悲观的判断。这也便是《最后的熊猫》书名的由来。
如今“熊猫项目”已过去了30年,我们该怎样看待上世纪80年代在四川大山里发生的这场冲突呢?
我们不应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刚从一场长达10年的大浩劫中挣脱出来。社会动荡带来文化落后,人们长期被灌输的理念还是“向自然进军”“与天奋斗”,自然保护、动物保护观念远不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还有,长期的农耕社会养成了人们对自然界无节制索取的习惯,树木是伐来烧的,动物是抓来吃的,珍稀动植物是拿来换钱的。人们也养动物,但那还是以人为中心,满足人们衣食、观赏或研究的需要,很少有人意识到动植物也是生命,也有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
往远了说,西方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就拿熊猫来说,自从法国神父、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在四川宝兴发现了这一神奇物种,引来的是西方人对大熊猫近乎疯狂的猎取和掠夺。从最早的“熊猫杀手”罗斯福兄弟,到第一个冒充“哈巴狗”把活体熊猫带出中国,在西方引发大熊猫热的露丝·哈克纳斯,到贩卖熊猫最多的“熊猫王”史密斯,西方人早期对熊猫的热情伴随着赤裸裸的血腥屠戮和金钱交易。
西方人建立环境伦理的新观念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在《大自然的权利》一书中,美国思想史学者罗德里克·纳什提出,大自然自有其内在价值和天赋权利,人根本没有理由和资格滥用自然。继解放了劳工、黑奴、妇女和印第安等少数族裔之后,人类开始解放动物。正如著名动物保护主义者珍妮·古道尔所说:“就像黑人不是为了白人,女人不是为了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样,所有的野生动物,它们也不是为了人类才来到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要重新与他们确立一个关系——和谐。”
夏勒80年代来到中国时,西方人的环境伦理观的确比中国人超前了一点,因此产生那样的困扰和冲突也不足为奇。令人欣慰的是,夏勒还是在中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知音,有着令人愉快的合作。他非常喜欢和钦佩中方合作者胡锦矗教授:“胡锦矗是一位优秀的博物学家,教我很多有关鸟类及其他森林生物的知识。跟他做野外工作是一件乐事。”他赞赏从秦岭佛坪保护区来的雍严格:“他对工作兴趣浓厚,不时陪我到处巡视,我很乐意把我们搜集的资料给他看。……我多么希望我们的项目也能找到像雍严格这样投入的年轻生物学者。”他称北大的潘文石教授是“投缘的同伴”,说他“后来启动并主持了中国最好的熊猫计划”。这些说明,中外科学家和动物保护工作者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共同为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也为中国人环境伦理观的进步打下了基础。
就是那几位初出茅庐就遭受挫折的年轻人,后来经过艰苦努力,也个个成长为我国大熊猫研究保护领域的专家,在保护事业中做出了杰出贡献。
诚如夏勒在书中所言:“我们至少要把我们的经验做成记录,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唤醒全人类的慈悲心,鼓励保护物种的行动。即使在道德至上的世界里,破坏也不会终止,但至少人类精神经过一番洗心革面,我们可以用更高尚的情操看待自然。”
《最后的熊猫》1994年在台湾出版了繁体中文版,199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在内地出版简体中文版时,沿用了台湾译者张定绮女士的翻译。张女士曾译过多部文学名著,译笔优美老练,还十分认真地加了不少译者注,但囿于资料匮乏与信息隔阂,人名、地名和术语等失误也在所难免。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启动了此书的出版,责编遍访当年“熊猫项目”的参与者,终于请到夏勒的最佳中国搭档胡锦矗教授对全书进行校订。胡教授以科学家的严谨,对书中人名、地名、动植物名称及一些史料一一进行了修订,还为新版作了序。因此,新版《最后的熊猫》,又是两位中外顶级的大熊猫专家携手合作的结晶。
1985年,夏勒是带着遗憾、忧虑甚至一丝“绝望”离开“熊猫项目”的。2008年他再来中国,却发现当年种下的种子开了花——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大熊猫保护事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动物保护有了立法,栖息地扩大了,野生熊猫种群数量也有所上升。正如胡锦矗教授在《中译本修订序》中所说:“野生大熊猫种群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衰退之后,到21世纪初已达约一千六百只,目前估计已近两千只(这个估计已为第四次全国熊猫调查所证明——引者注)。……当代野生大熊猫仍保留着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潜力。”
2011年,珍·古道尔在中国出版了她的新书《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其中提到了夏勒。她说:“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带着悲伤离开了中国,而今他在这本书的《引言》中写道:‘现在,拯救大熊猫的前景无可限量。’”
这,应该是夏勒博士为《最后的熊猫》画上的圆满句号。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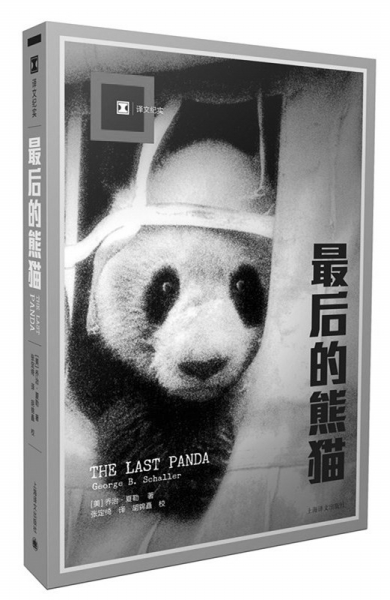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