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文文学史,大陆1999年出版过汕头大学陈贤茂主编、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但该书内容并不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而2015年2月成功大学马森教授由台北“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三卷本《世界华文新文学史》,空间上包含了海内外,时间轴则横跨清末至今百余年。它是首部探讨海峡两岸、港澳、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华文作家与作品的文学史专书,力图记录百年以来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源流与传承。这是前无古人的填补空白之作,其雄心可嘉。
这部内容庞大的著作理应有像陈贤茂当年那样的团队分头执笔,现在却由马森一人独立完成,这私家治史的好处在于观点和文笔容易得到统一,不必为贯彻领导或主编意图,将个人见解消融掉,但个人撰写不能集思广益,有些自己不太熟悉的领域,亦不可能像“编写组”那样请专门家写得深入,部分章节写起來有时难免会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以马森本人来说:自已熟悉的海外华文文学部分写得详尽完备,戏剧创作更是泼墨如云,而作为王蒙高中同学的马森,毕竟不可能像王蒙那样了解大陆文学,故凡写大陆作家部分,大都用“点鬼簿”的写法抄抄生平和排列著作目录了事;而对于台湾新世纪文学,则因“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马森可能看得不太清楚,这就有可能写到这部分时会令人错愕又意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举双手赞成隐地《文学史的憾事》(《联合报》2015年3月21日)对马森的尖锐批评。《读隐地书评〈文学史的憾事〉有感》(《联合报》2015年4月11日)的作者陈美美,在为马森辩护时攻击隐地书评所刮的是一股“歪风”,其余部分只是泛泛而谈。她要求批评者应做一个“温柔敦厚的长者”,这并不符合文学批评的功能和原则。
马森所作的情绪化反应《吃了一只苍蝇》(《联合报》2015年4月25日),其实一点也不“温柔敦厚”。他除借机攻击隐地是“谣言”的制造者外,并未对隐地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做出具体回应。他指责隐地“只注目于细微末节”,可有一句名言叫“细节决定成败”,如马森把以写长篇小说《野马传》著称的司马桑敦列为“报导散文家”,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误。隐地用“真是岂有此理”形容读马著的感受,也许态度欠冷静,但隐地写的是有个性、有情感、有体温的“辣味”批评,不能用“甜味”批评准则苛求他。此外,隐地指出:“将杨牧列入‘创世纪诗人群’,将‘现代诗社’的梅新归入‘未结盟诗人群’,均属不妥。”这也是精辟之论。以杨牧而论,他在意识形态上心仪“创世纪”,但不能由此说这位独行侠加入过“创世纪”诗社。
马森这类硬伤在大陆部分比比皆是,如说大陆作家吴祖光是“不左不右”的作家,其实他是“大右派”。又在新出版的某刊连载的该书部分章节中,不止一次把“江青”误为“江清”,这有可能是手民之误,但说“以江清为首的四人帮”,这应该是作者之错。其实,“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中的江青,在“四人帮”中只居第三位,真正为首的是时任毛泽东接班人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该书还认为“在累次整人运动中”,巴金、沈从文“都停笔不写了”,事实是巴金还在创作,哪怕文革伤痛还未痊愈仍写了直面十年动乱所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扭曲的《随想录》,沈从文同样写有鲜为人知的少量散文。郭沫若、茅盾也非“绝不再从事任何创作”,相反,茅盾在反右派斗争后陆续出版有《夜读偶记》《鼓吹集》《1960年短篇小说欣赏》《鼓吹续集》《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读书杂记》;郭沫若在十年浩劫中虽然严重缺“钙”,他当年那气吞宇宙的“天狗”气势再也一去不复返,但仍于文革期间的1971年出版了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世界华文新文学史》第二十九章标题为《社会主义的诗与散文》,这也是很奇怪的提法,难道大陆除“社会主义的诗与散文”外,还另有“资本主义的诗”与“资本主义的散文”?君不见,大陆早就停止了“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不再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类的政治挂帅文学分类法,可号称“不受政治意图、意识形态左右”的马森,仍沿用这种分类,可见其未能与时俱进。
作为大陆学者,我非常景仰对岸“宽厚溃堤”:哪怕是老朋友,也亮出自己的锋芒这种不留情面的批评。而我们这边,流行的是“友情演出”和“红包”式的捧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马森老友的隐地说《世界华文新文学史》读得瞠目结舌,甚至说马森“写成不具出版价值之书”,这虽然是印象式批评,但决非网络上的乱飙狂语,它是发人深省的辛辣之论。马森很不情愿认错,声称读隐地文章“犹如吃了一只苍蝇”,而我的感觉却是吃了一只爽口的辣椒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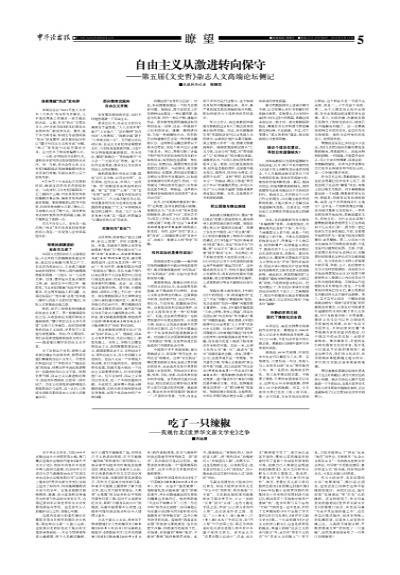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