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夜推敲“热点”发布辞
本届论坛以“2014年度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发布作为开幕式,几乎是在筹备工作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之前,作为“热点”主要发布方,《中华读书报》原本打算在北京组织专门的发布仪式。最终,鉴于多方面考量,特别是考虑到两条“热点”涉及儒学,而本届论坛恰好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为题,“热点”发布遂与论坛开幕式合并。这可忙坏了相关的编辑人员。
一方面,必须赶在开会前几天,请相关专家写好比较详细的热点点评。另一方面,作为合作义务,《文史哲》编辑部必须抽调编辑对热点点评进行浓缩,形成每条约三百字的发布辞。
4月30号下午是论坛正式报到时间,晚饭过后仍有学者陆续到达。与此同时,《文史哲》编辑部一正三副四大主编,外加执笔发布辞的编辑齐集会场,集体对发布辞作最后推敲。集体推敲的过程并不轻松,时间很快由晚七点到了晚九点,又由晚九点过了晚十点。而负责发布式PPT制作的李扬眉副主编,则干脆熬过了凌晨一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发布式一炮打响,“热点”条目本身连同发布辞的切入角度,一并受到与会专家高度评价。
很难找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了
本届《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从去年秋天的编辑部务虚会开始,就已经在酝酿与策划之中了。在这次内部会议上,王学典主编曾如此研判形势:“传统与现代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方抬头,另一方必然反弹。目前,儒学复兴呈星火燎原之势,新一轮的古今中西之争一触即发。”《文史哲》服膺“知出乎争”的格言,乐见两军混战人仰马翻。本届论坛冠以“‘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题目,实际上正有挑动论战之意。
然而,似乎已经很难找到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了。第一轮邀请函发出之后,从收到的论文题目和发言提纲来看,“儒学和自由主义并不矛盾”立场占主导地位。面对曾经强势的自由主义话语,学界似乎正在进行深度调和。然而,作为策划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有力的对头——激进地反儒学的自由主义学者。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联络人请求部分确定与会的学者,推荐深受他们尊重的自由主义学人。尽管我们和盘托出了“寻找对头”“挑动论战”的初衷,结果却并未因此收获哪怕一位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纵观学界气候,自由主义从激进转向保守,或走向所谓成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历史文化传统深刻影响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作,这一认识,已经成为训练有素的自由主义学人的普遍共识。
部分儒者试图向自由主义开炮
带有儒家情结的学者,却时不时地想刺激一下自由主义。
慕朵生认为,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在于基督教,“人人生而平等”基于“上帝造人”,“法治精神”旨在对治“人性堕落”,“政教分离”源于“人神或圣俗二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自由主义者批判质疑儒家文化,乃至投身基督教怀抱,乃是中华文明衰微的重要原因。作为对比,儒家“政教合一”传统植根于“天人合一”“圣俗不分”思想。基于文化自觉地考虑,慕朵生认为应该对自由主义保持警惕。
颜炳罡教授针对会议主题,提出“以仁义为体,以自由为用”。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用“体-用”范畴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体”是“本根”“主体”,“用”是“作用”“显用”。中国哲学原本讲究“体用不二”,牛之体不能有马之用,然而置身现代化与全球化处境,颜教授希望能基于“仁义”本体吸纳其他文明之精华。然而,“以仁义(而非自由)为体”这一提法,明显蕴含“以儒家价值为本”的诉求。
究竟何为“自由”?
众所周知,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评价王国维之死。但是,考虑到王国维之死带有浓厚的“殉清”与“殉中国文化”(三纲“大伦”是其核心,而这常常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色彩,唐文明教授追问:这究竟是怎样一种“自由”?作为回答,唐教授提出所谓“伦理自由”概念,并认为基于现代以来出现的个人自由观念对五伦进行规范性重构,仍是我们应当面对的重要时代课题。此论一出,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黄玉顺、方朝晖教授,试图从学理上予以进一步补充。林安梧教授则认为王国维身处三纲与皇权意识高压底下,根本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萧功秦教授在承认唐文精彩的同时,毫不客气地认为此乃走火入魔的附会之作。张祥龙、谢文郁教授则强调,特定的西学话语(特别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不能垄断关于“自由”的话语权。
高全喜教授试图将讨论从“自由”拉回“自由主义”。他指出,自由主义有多种形态,无论从理论上、制度实践上。实际上,苏格兰启蒙思想自由主义、法国斯蒙思想自由主义、德国思想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现代自由主义,在人性问题上众说纷纭。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话题,我们不能简单化。要想简单化处理,那就只能大致说一下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核心、针对的问题是什么。但无论如何,自由主义和自由的关系,是一个不该回避的问题。与此相关,郭萍博士和黄玉顺教授强调,应该从前主体性即生活本身角度,回答个体自由如何产生的问题。
问题回到“究竟何为自由”。对此,孙向晨教授提出一个较为宏观的勾勒。他指出,西方思想史上存在两种自由观念,一种以霍布斯、洛克为代表,另外一种以卢梭、康德为代表。霍布斯传统很明确地讲权利和自由是一回事,这是一种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康德一路则讲自律,乃是一种道德性自由。权利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是一种非常关键的区分。这两种自由概念都带有个体本位特征,但是个体不足以支撑个体本身。所以,黑格尔除了讲基于财产的外在的自由和内在化的主体性自由,特别指出还需要一种社会自由、伦理自由,需要伦理生活里面把自由展开。与此相关,谢文郁教授指出:在儒家,责任意识的建立过程往往带有外在强迫性,比如通过家族制约的形式进行;然而,一旦你接受了响应的责任意识,对你来说这就不再是一种强迫。这里面并非像林安梧教授所说的那样“没有自由可言”。
此外,针对颜炳罡教授的“体-用”论构想,张祥龙教授提出商榷。张教授认为:“自由为用”如果是指限制性的、狭义的“自由”,那未尝不可;但若上升到人之为人层面,其他动物受制于本能,而“自由”(在更深长的时间意识中做选择)则构成人的本性。当然,这种“本性”意义上的“自由”,已经超出狭义的“自由主义”,而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哲学”问题。
权利政治还是责任政治?
回到政治哲学议题——能否相对简明地概括中西政治传统的差异呢?谢文郁教授提出的“责任政治”与“权利政治”分野,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
谢教授指出,康德在分析自由与责任关系时认为,自由是责任的基础,处于强迫的不叫责任。自由主义即这种理念的落实,它强调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结社权,乃至持枪、推翻政府的权利。这些基本权利受宪法保护,自由主义因而首先是一种“权利政治”。但是,社会成员需要在一定的责任意识中行使这些权利。以美国为例,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不负责培养责任意识,这个任务主要通过另一个社会机构即基督教教会完成。对此缺乏认识而简单移植这种“权利政治”体制,在世界各地已经造成有目共睹的社会灾难。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体制,谢文郁教授认为,则采取“责任在先,权利在后”的模式。这种“责任政治”模式要求政府主导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社会成员在各尽其责的基础上享有权利。传统社会里的宗族、科举、书院、学派,均具有责任意识培养功能。官员的责任意识由此而出,相应的政治治理亦很注重维护上述责任意识培养机制。就此而言,慕朵生先生特别提到“政教合一”,可谓切中肯綮。当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运行过程中,这个体制也有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最高领袖的培养问题,即如何培养天子或皇帝的责任意识。
作为主持人,高全喜教授怀疑谢文郁教授过分夸大了教会的责任意识培养功能。对此,孙向晨教授引用“美国的法律可以让美国人为所欲为,宗教则让他什么都不能做,禁止他想入非非”一语,替谢文郁教授辩护。颜炳罡教授则试图从“仁义为体,自由为用”角度,对“责任政治”与“权利政治”划分提出质疑。颜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权利和责任根本上是一致的,责任就是他的权利,权利也是他的责任,这里面不能分先后,把责任、权利分为两边,打成两个东西”。这种“责任、权利根本为一”的提法,既让人想起“责任出于自由”的康德式界定,亦可以从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修身境界角度加以理解。当然,这是两条不尽相同的思路。
君主困境与群众路线
诚如谢文郁教授所言,儒家“责任政治”的最大困境表现为,最高领导人的责任意识培养问题。邹晓东博士称之为“儒家君主困境”。邹博士在发言中指出,关于君主施“教”,《大学》《中庸》提供了两种不尽相同的模式。《大学》基于“知识(传统共识)现成”意识,突出“知而不行”问题,将“自觉实行”意义上的“诚其意”视为“修身”之本。与此相应,对于那些自觉性不足的民众或小人,《大学》允许以君主为代表的执政者运用声色威势“强迫其自觉”。这种模式的盲点在于,传统只能在理解中发挥作用,再好的传统都有可能被误解,君主的理解如果存在偏差,上述威势教学势必只能助长社会灾难。
邹晓东博士进而指出,《中庸》比《大学》更进一步,将普遍性的“过之”“不及”问题与“鲜能知味”挂钩,充分注意到“知识—理解”问题的根本重要性。为此,《中庸》开篇提倡“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预设生而固有的“内在向导”作为解决“真知”问题的基础。顺此思路,《中庸》按理可以开出类似“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思路。但是由于深刻“真知”问题意识,《中庸》随后提出“何为真正的率性/如何做到真正的率性”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修身者自行率性的可能。如此一来,出神入化的至圣“教-化”,就成为“真知”问题的最终出路。然而,邹博士认为,这更多地只是一种想象。作为替代方案,邹博士主张取消“真正的率性”问题,而以动态的“异议表达(所有社会成员)—寻求共识(执政者主导)—继续体察(执政者与被治理者一道)”模式作为“真知”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对此,任锋教授感觉这很有一点“群众路线”的意味。邹晓东博士则坦陈,在他看来,中国许多现行政治理念实际上都带有深刻的传统底蕴。
唐文明教授则对上述演示颇为不满,认为邹博士对经书和解经传统缺乏敬畏。在他看来,《大学》《中庸》作为《礼记》中的两篇,思路总的来说应该一致才对。谢文郁教授则指出,尊重经书文本和遵守特定解释是两回事,不应混淆。不过,对于邹博士“真正的率性”提法,谢文郁教授认为值得商榷。
缺乏个体本位意识,导致目前道德缺失?
沈顺福教授从当前的道德缺失危机谈起,认为:两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缺少自主决断和自由选择的观念,个人只能被动接受圣贤关于何为善恶的告诫,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理性的价值判断机制。最后,他得出结论:价值判断机制的缺失,使传统儒家无法有效地适应于市场经济时代。换而言之,只有树立个人自己作主的观念,从而建立起价值判断的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当前的道德缺失危机。此番言论,可谓自由主义思路在本届论坛发出的最强音。
对此,孙向晨教授的发言颇有“补偏救弊”效果。孙教授指出,支撑起现代社会的“个体”,并不是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个体,而是一个权利意义上的个体。个体本位思想的积极意义在于,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其消极意义则在于,教条化的个人主义往往导致社会生活的无根化、松散化。最后孙教授认为,儒家真正要做的不是努力从传统文化“开发”现代价值形态,而是应该从制度设计层面考虑如何消解现代主体本位带来的消极影响。就此而言,林安梧教授的“公民儒学”建构与陈明教授的“公民宗教”设想,乃是很有意义的尝试。但是问题在于,本世纪以来城市化建设运动导致乡下没人了、宗族解体了,现实中的儒家究竟还有哪些集体生活模式,可以资纠正现代“个体本位”偏颇?
冷静的东西已经取代了情绪化的东西
本届论坛,最后安排萧功秦教授作总结发言。萧教授从1984年进入公共学术领域而没未间断,迄今已历31载,乃是与会学者中资历最老者。萧教授从回顾中国学术界的变化谈起。
他指出,80年代初期,中国的学术生态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是情绪化,只要你说一句话,其他人马上本着各自的“自由”情怀批判几句。第二是西化,极端的反传统。第三是学理比较空虚。不需要学理性,只要你有感觉就可以发言,这里发言10分钟就跑路,那里讲上10分钟再跑路。但是,今天的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第一点不同是,它有非常深厚的知识积淀,这个积淀不是一天两天完成的,而是二三十年沉淀下来的。第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在专业领域说的话都非常有道理。第三,比较冷静,冷静的东西已经取代了情绪化的东西,情绪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这一点萧教授觉得是可喜的变化,也是时代变化的缩影。他作为这种变化的见证人,觉得很欣慰。
萧教授还说自己参加过不少会议,而《文史哲》选择的确实都是各路的精英,都是聪明人。谈起来特别的舒畅,一听就懂,不需要多说什么,马上大家互相理解,迅速达到一种理解的愉悦。许多与会学者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一点令他印象非常深。
作为学术总结,萧教授指出,现在社会思潮已经非常多元化了,因而出现了社会的“撕裂”状态,网络上的分裂尤为强烈。对于秦晖教授提出的一个问题,萧教授非常有共鸣,那就是:到底有没有共同的底线,或者,这个共同底线在什么地方?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在当前的集体文化经验中,一种共同的东西开始出现,那就是儒家文化、传统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萧教授观察思想界至少正在形成如下几点共识:第一,西方那一套已经丧失其普世性地位,左派、右派都开始将其作为一套地方性知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二,中国本土的文化被视为可资吸收的资源,不是完全可以抛弃的东西。左派、中派、右派都已经开始有这种认识,而随着时间的增长这种认识只会越来越广泛。比方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和谐、公正,这在儒家文化当中是特别强调的。自由派当中开始出现儒家自由主义(如黄玉顺教授所言),强调人心内在的自由可以作为选择的基础。尽管自由与道德的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已经开启,唐文明教授在内都试图从这方面开出新路。第三,是不是可以说有一个儒家的威权政治模式?儒家“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的理念,以及在对当政者进行道德的约束同时赋予其人生价值,对于当政者实际上非常重要。儒家文化完全可以作为调动官员积极性的资源,比如“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等强调为官责任意识的提法,对于现实中的官员实际上是很有滋味的。萧功秦表示,在座的各位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是不是可以就此开出新的领域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文化共识、共同底线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会迎来更新的高潮。
萧功秦教授感谢论坛组织者选择了这么好的题目,成为大家讨论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会议主题不是拍脑袋一下子想出来,而是从很多学术观点与学术现象中提炼出来的,会议选题体现了《文史哲》杂志的学术洞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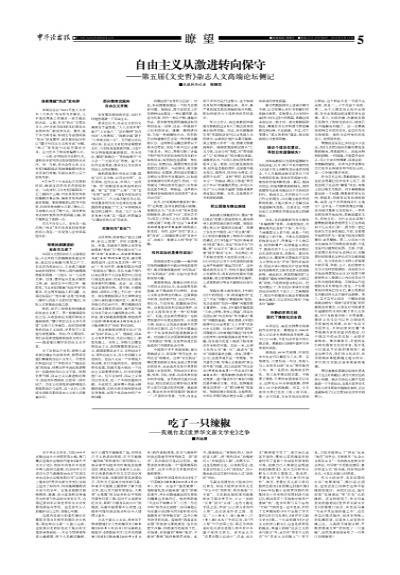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