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买书历史追溯起来可以从毁齿之龄即开始。九十年代中的人民医院斜对面那段路便是书店聚集地,栉比的门面中时时都能见到有人在挑拣。父亲是六零后,也曾为这“热”所感,在青年时代闹过一阵文学的,积得小半墙的新诗集和外国文学书。父亲固然是“学书不成”,但在当年仍残余着文学青年的习气,好逛书店即是其一。有一回他顺路带我钻进一家书店,我望见高一层的架子上立着一部硬皮的《白话聊斋》,或许是受了电视剧蛊惑,便心动了,回家后央他去买。好几百页的鬼故事集对二年级的我而言太繁重了,不久就被打入冷宫。很多年后,在我读铸雪斋本《聊斋志异》遇上拦路虎的时候,才又想到将这部岳麓书社的白话本翻出来参考一下,却发现译文切实准确,实在是一部用心之作。
我开始持续的读书是从金庸的书开始的。而这套书也像那《白话聊斋》一样,是父亲应我的要求买的。当时一般家长是不许小孩读这类书的,怕妨害举业。我所以能读,还得益于父亲的文艺气息。他泛泛地觉得,学生也该受点文学熏陶。街面上并没有分册的《金庸作品集》,是托一家书店老板去武汉进货时候捎回来的。我记得拿回来是一箱,三十六册,每种书的书脊各是一色,共两百多元。从此我开启了一个新天地,沉浸其中不愿出来。我还把书带到学校去看,同学渐渐也传阅起来。更有一次是什么考试,监考老师竟问我借了一本《天龙八部》来消磨时间。
除了小学去“新堤厂甸”买过一册《少年史记》外,我真正的独立买书当从高中算起。高中几年背井离乡,虽然在住处不能“举动自专由”,但个人空间反倒宽松。盼头有两样,一是《体坛周报》,一是《萌芽》。后者虽说是杂志,但也算书。高二一整年,我几乎一出便要买。那上面文章的水准与价值,现在可以不谈;但这杂志却引得我掏出本就不多的零花钱去买了另一些书。我买过李碧华的锦句集《只是蝴蝶不愿意》,买过安妮宝贝的《蔷薇岛屿》,买过王小波的《青铜时代》,还买过一本张爱玲的传,大抵都是些《萌芽》上常提的人。卡夫卡我反而没买,是因为实在看不下去。有一回下晚自习回家的路边,一个摊子上侧立着一整桌“名著”,我竟在里面撞见了弗洛伊德的《释梦》,翻都没翻便领了回去。自然不免要猎奇地尝试几回,却无不废然而返。鲁迅说得好:“伟大也要有人懂!”所幸毕业清理时我没舍得扔掉它,携它回去。大二那年,我的猎奇心理再度爆发,坚持啃完了老弗的《精神分析引论》。心犹未餍,又将此书抓过来,一气读完。后来我也看过一点外国书,译文令人气丧。而这路边捡的十元译文竟能明晰,着实让人庆幸。这本书我至今仍想重读,这在当年买的那些书里,堪称独例。
大学的头两年是在漳州郊区度过的。周边除了几家小饭馆和几家书店,一片荒芜。晓风书屋走的是高端路线,种类相对全,我一去便要从头至尾的捋一遍。那时无由来地觉得要补习古典文化,一面从图书馆借了唐诗论语回去琢磨,一面也想自己买一点。我在晓风买的第一本书好像就是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因为底子太差,就着注释也半懂不懂。但当时想,一看就懂还算什么古典文学?于是咬牙硬读。实在不懂了,就为文“造”情。这经验训练了我读书不避繁难的因子。后来又陆续在晓风买了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马茂元的《楚辞选》等书,读来就没那么费力了。
漳州的旧书店,是朋友领我去的,藏在那堆饭馆后面的小巷里。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书论斤卖,这是我后来在山东、上海的旧书店都不曾经验过的。摸完书的手又涩又黑,这是在旧书店淘书最不愉快处。
以上所谈,都是传统的买书。至于网购,是在我入大学时已经兴起的。我在电子方面永远后知后觉,但眼看便宜,也慢慢少在书店买书了。书店也还去逛,当作散心。偶尔也忍不住出手,要是碰到饭点,便独自到街对面的川菜馆点个盖饭,边翻书边等,十分充盈。有本陈鼓应谈《易传》的书,就是那时买的。然以陈先生执着于以道抗儒,这书我至今没读。在临毕业的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样“躲进小楼”的惬意光景,于我是难得而又不可少的。
回顾这十几年的买书生涯,要问:“于我何有哉?”结果不过是空得了“一肚子不合时宜”而已。王静安先生有句“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这话王先生可以讲,我辈还讲不得。这些年买书所得的知识,似乎还不足以“疑古”,却不免让我对“今”有些“疑”了,因为以书来看,实在是“今不如古”。而这话岂不正是“不合时宜”的么?那么,总该有些“悔”了吧?我想,“悔”也是有的,在今天还好买书的,剔除当生意做及装门面者——也或者这两类本是一类——外,有几个能“不悔”?但也无能太悔,太悔时,就定然不会再去买书,于从前的买书也要叹“悔不当初”,自然也不会来作这篇文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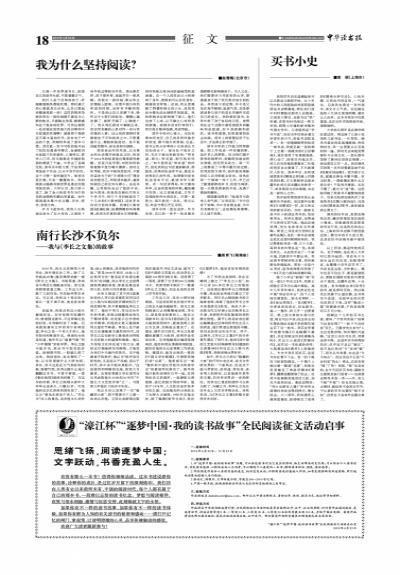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