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那时候自学英语,没有合适的书,逮着什么读什么。胡乱读过的书早已不存,唯独一本当作宝贝珍藏起来,后来偶尔也会翻翻的,是《约翰生词典》(1755)的现代选本(Johnson's Dictionary. A Modern Se-lection. By E. L. McAdam, Jr. & George Milne. London: VictorGollancz LTD.1963)。书是从上海福州路的一家外文书店淘来的,大约我这年龄的沪上读书人都知道这爿店,在那里买过影印的外文书。前两天,为写这篇文章,我又翻出三十多年前买的这本书,打算重读一遍,却先被里封盖着的三个戳子吸引:“上海市半工半读师范学院图书馆”;“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调拨图书”;“收购图书”。半工半读师范,这类学校如今已不见踪影,上海的这所后来并入了师大;上海师大自然还在,估计是当年校图书馆管事的不稀罕这书,处理给了外文书店。书不是影本,是精装的原版,收购价两块六,售出价三块二,薄利而已,现在翻上一百个跟头我也不卖。这些听起来跟李翔君即将问世的著作《约翰生<英语词典>理论与实践研究》没有关系,可是没有这些,他来北外读博我大概不会建议他研究约翰生词典。
年轻时读约翰生词典,能懂上十之二三就算不错;即使现在重读,也不敢说条条都能读通。但因为十余年来亲自编过词典,写过评析词典的文章,对于词典之学略有所识,再来读它便能领会更多,感悟也大不同前。现在的书市上,最不缺的就是英语词典。比之当今众多的英语词典,约翰生词典能有哪些好处,让它至今值得我们欣赏呢?大的方面读者从李书中自能了解,这里我只谈两个细节:存疑和有趣。
凡是自己不懂、不解的,约翰生就会直说“我不知道”、“我不清楚”。于是,在名词etch底下我们读到:“一个乡下人用的词,我不知道它的意思。”这能算释义吗?现代读者肯定会失望。虽然接下来有例句,摘自某一部农书,仍不足以明了词义。就mum(缄默)一词他写道:“我不知道这个词本该怎样拼写,不过可以观察到,在发音时双唇是闭拢的。”goose(鹅)这个词,再普通不过,谁都说得上它指什么,可是约翰生觉得还不够明白:“goose,一种个头较大的水禽,民间常以为它很蠢,原因我不清楚。”类似这样的坦诚,在今人眼里几乎是多余的。倘若问过许多人,仍不能确定一个词的意思,这个词想来够生僻,不必收入词典;而既然收了,无论如何也得给个解释,哪怕一时说不清楚。mum,就连莎士比亚也这样写,难道拼法会有疑问吗?至于“鹅”,英语里向来转指傻瓜,何必管它有没有道理呢?索绪尔说过,词语属于任意的符号,音与义乃是约定俗成的关系。一项词义,社会上怎么用,我们跟着用就是了,毫无必要问为什么。可是约翰生偏偏要问;问了不算,还如实记下疑思。于是我猜,坦诚在约翰生身上恐怕主要不是一种态度或品格,而是一种工作的习惯或问学的方法。就词典编纂而言,坦诚无非就是存疑。
英语拥有词典,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比汉语至少晚一千五百年。学术史的悠久无可比,学术的门道却可以比,而古代词典编纂的门道之一便是存疑。东汉许慎撰毕《说文解字》,在叙文里谈到自己处理字条的办法:凡遇疑难,首先“博采通人”;求诸通人也不得解,便只能“闻疑载疑”,“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由是《说文》全书留有十余处“阙”,也即不予解释,相当于《约翰生词典》中频频出现的“不知道”。至清代乾嘉时,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1815),继承了存疑之法。例如“符”字,《说文》的解释是:“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段注则说:“按许云六寸,《汉书》注作五寸,未知孰是。”六寸或五寸,究竟哪个准确,他也无法断定,便坦言不知道。
现代词典家诠释词义,已经很不可能用诸如“不知道”这样的字眼了。存疑作为一种问学的方法,在词典界的用处越来越小了。因为古人把词典看作学问书,学问之道是必须存疑的;今人则把词典视为工具书,而工具是供人使用的,必须标准可靠,不应存有疑义。词典之为工具,公众还要求它是万能的:最好是个词都收,每收一词都要解释明白。所以,历来词典家承受的社会压力明显大过其他著述家。对此约翰生感触良多,也发过牢骚,不过总的说来他有足够的自信支撑着他去完成词典大业。他曾对一位朋友说:“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很懂得怎样去做,并且做得也很好。”(I knew very well what i was undertaking,——and very well how to do it,——and have done it very well.)过去我读这段话,只是从修辞的角度赏析:一个普普通通的“very well”,一再重复使用,力道居然胜过任何状语。现在重读这段话,我便想问:约翰生何以会如此自信?面对社会压力,他一定有应对的办法。办法之一前面说过了,即用“不知道”来化解重压。此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部分压力转嫁给行家。大量带有百科性质的条目,约翰生宁可直接引用他人,也不轻易自撰释义。例如chameleon(变色龙):
变色龙有四条腿,每一条腿上长着三个爪子。它的尾巴很长,它便用这尾巴和腿攀抓树枝。它的尾巴扁扁的,鼻口长长的,带着圆钝的端头;它的背脊相当锐利,表皮带有凹凸如齿状的褶子,从脖子直到尾巴的尖端有如一把锯子,而脑袋上长着的东西则宛若一把梳子。其实它和鱼一样,并没有脖子。有人说,变色龙只须呼吸空气就能存活,可是有人却目见它用舌头捕食苍蝇。它的舌头长十英寸、厚三英寸,白色的、圆圆的、肉鼓鼓的,顶端则是扁平的;也许舌头里面是个开放的空腔,一如大象的鼻子,会缩短,会伸长。据说,这种动物会随外物而变易体色,不过现代的观察者告诉我们,当它栖伏在树荫底下时,它的自然的体色以蓝灰居多,黄色或绿色的种类比较少。一旦暴露在阳光下,它身上的灰色就变深了,几乎转为暗褐,而未晒到太阳的部位则会呈现各种色调。(Calmet)
还有bat(蝙蝠)、crocodile(鳄鱼)、elephant(大象)、lizard(蜥蜴)等条,释义也都取自同一人。这样大段直接地引用,岂非太过容易?今人是不屑效法的。然而今人编词典,移借或摘取现成的释义其实更多,只不过是变明引为暗袭罢了。
上引“变色龙”一条,虽然显得冗长,读来却不无趣味。不仅百科词条有趣,许多语文词条也很有趣。在撰写语文词条的释义时,约翰生喜欢夹入自己的看法,包括对事物的褒贬;或者,透过他所引用的解释,可以看到他对事物抱持的态度。这在今天也是少见的,现代词典学家告诫我们:对概念的定义应是客观的,释义所用的表达须是中性的,不可掺杂个人好恶。试看以下诸条:
arbitrator(仲裁者、公断人):“有权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不受任何约束或控制的人。”
army(军队):“持有武装的一群人,他们必须听从一个人的命令。———洛克”
excise(消费税):“一种对商品征收的令人痛恨的税种,不是由普通的财政官员颁令收取,而是由敛财者雇用的一帮恶棍强征。”
geomancer(风水先生):“算命先生;占卜者;使用除占星术之外的手段,假装会预卜未来的骗子。”
luggage(行李):“任何沉重、累赘而又不得不随身携带的物件;任何徒有分量而实无价值的东西。”
lunch,luncheon(午餐):“多到手上端不下的食物。”
mortgage(典押):“赎不回的抵押物;落入债主手中的东西。”
oats(燕麦):“一种谷物,在英国一般用来喂马,在苏格兰则是维生的口粮。”
对强权的不满,对金钱的睥睨,对流俗的厌恶,等等,这些都是很显然的。至于他称燕麦的用途因乡土而异,是视为一种民族情绪的流露,还是理解为一种谐谑无害的调侃呢?这恐怕取决于读者的立场。
以上所讲的两个细节,李著其实也谈到了。有些内容也许著者已经想到,只是来不及展开,我在这里略写几笔,就算作一篇补白。《约翰生词典》之于英国语言学史,犹如《说文解字》之于中国语言学史,其地位、价值国内学界并非不知,只可惜始终未见专门而深入的研究。李翔君的这部专著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对于英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如能都像这样一篇一篇详加考察,再加上中国人看问题的视角,那么,书写的英国语言学史就会很好看了。
2013年处暑后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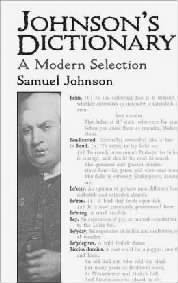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