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布瑞克认为,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
当我们在自由和枷锁之间进行方向选择时,那种只为精英和权贵服务的现代化观念逐渐隐退了。与此同时,普通人即人民的现代化进程却开始起步:不仅是在美丽的莱茵河畔,而且也在中国,勇敢并且是永不停顿地起动了。
16世纪初期,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两场来自于市民和农民的运动,再次震撼世界,使德意志成为欧洲令人瞩目的焦点。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德意志只是哈布斯堡家族王朝广袤领地的一个组成部分,市民阶级与德意志皇帝结盟无望,诸侯称霸一方,地方贵族横行乡里,既算不上是个完全独立、主权完整的国家,也算不上是个全国统一、政府机构高度完善了的民族国家。这样,把德意志向近代推进的历史任务,就完全压在了市民和农民的身上。
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被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深深关注。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这位1938年11月26日出生在柏林的人,后来被人熟知的称谓是在瑞士伯尔尼大学任教的“德国历史学家”。据布瑞克看来,德国既没有开明君主,也没有市民与君主结盟的繁文缛节,由百姓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印记显得更为清晰、纯粹些。百姓们无职无权,也并不在帝王贵胄的政府里当官,他们推动历史发展的途径是“自下而上”,而其所用的方式就是“革命”。与君主和市民结盟、削平地方贵族、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建立民族国家的方式不同,德意志显然是走了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
然而问题接踵而来:真正采用革命模式的人是谁?是市民抑或农民、还是包括市民、农民在内的“普通人”(百姓)?这些普通人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是要抵制贵族的专横、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利,抑或是要参与政治、建立新的体制,甚至是建立由他们自己当家作主的共和国?这些问题表明:布瑞克开始关注宗教改革,其后又透过宗教改革关注农民战争,最后又透过农民的村社而关注农民的更大的诉求。点点滴滴的思考与零零碎碎的史料连成一片,出现了“人民通过革命推动近代政治产生”的诠释模式。布瑞克宣告:在德意志,近代政治是由人民推动和建立的;尽管德意志四分五裂,近代政治仍然是能够从层层岩壁的缝隙中夺路而出,并且闪耀出民众革命的光辉。更有甚者,相信王朝战争可以改变一切的英国和法国,其结果却是君主专制和二次革命(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而被人低估了的德意志百姓革命则将直接产生共和国。当共和政治在意大利和欧洲城市中隐退时,德意志的农村却成了共和国的故乡。村社、议会、共和国三连星,不仅折射出了德意志政治发展的轨迹,更是凸显了德意志迈向近代政治的民众特色。
这些零碎但深邃的思路,最终在1975年汇集成《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这本书德文版出版不久,就由现为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布雷迪(Thomas A. Brady, Jr.)教授等人译成英文,1981年在美国出版。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中文版,钱金飞、陈海珠、杨晋和我把它翻译成了中文。这部作品不过20万字,但一出版即成为经典学术著作。与众不同的视角,大胆而又深刻的分析,迅速以“布瑞克命题”的形式广为流行。今天,只要是稍微涉及过近代早期欧洲史研究的人,布瑞克这个名字几乎是无人不晓。布瑞克的作品,不仅揭示了民众运动的深刻背景,也为近代欧洲政治的产生,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的诠释体系。
布瑞克也许是当今欧美世界中把农民的作用提高到最高程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一个德国教授,却服务于瑞士的伯尔尼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是服务于一个崇高的使命:正确阐述农民对于缔造现代社会的作用。为此,他几乎穷尽地研究了有关十五六世纪德国农民的所有原始文献,包括各式各样的农民的冤情陈述书、农民运动的纲领和乡村组织的史料。
无法否认,在我的学术发展史上,布瑞克教授的影响无与伦比。早在1987年,当我准备以德国农民战争作为博士论文题目起,布瑞克这个名字就开始与我相伴。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了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但却没有很好地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而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他们的领袖中不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兄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使命。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没有推翻领主、诸侯封建统治的愿望。
正是在这扑朔迷离的图像中,我接触到了布瑞克的名著《1525年革命:德国农民战争新概念》。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封建经济范围内的分配问题。封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为参加政权而发动起义,希望用革命手段来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 为此目的,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积极建造者。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社区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途径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把农民革命的政治目标解释成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议会斗争和最后建立共和政治。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同德国历史学家弗兰茨和布塞尔隆所建立的“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解释。
布瑞克认为: 不仅农民和市民必须联合起来(宗教改革运动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便利),而且农民的经济、社会斗争的目标也必须通过政治革命(建立百姓的共和国)来实现,而这就是1525年革命的深刻内涵。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布瑞克学派的要点,那就是:“近代政治和社会体制主要是由百姓建立或推动的,因此并不存在脱离了民众需要的现代化”。布瑞克认为,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结构中去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
在农民的需要是什么的问题上,布瑞克认为:农民的需要是同16世纪德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相关的。在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民也不再仅仅是“做工的”,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觉悟的新阶层,农民要求改革农村的农业秩序。农业秩序一词,首先是从制度层面来说的,它不以单个农民是否改善了其经济地位(如减少租税额度、废除农奴身份),而是要建立其一种新的机制,以缓和德国社会变化赋予农民身上的压力。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大诸侯加紧收缩领地、地方上的小领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以及通过货币地租和领主自己对不动产剥削的发展,这些都最大限度地剥削了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领主扩大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权,加重赋税(dues)和劳役,并削弱农民的财产权 。这种举措的一种方法就是农奴制(serfdom)。在这种制度的帮助下,对农民剥削从15世纪以来就不断加剧,到1525年时状况更糟。正是这样的背景,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布瑞克不同意把农民的行为完全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化的被动应付,而是强调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经济的主动性,强调农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这种超越农民战争源自剥削与反剥削的视野,使布瑞克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农业秩序的博弈之中。这不仅是因为地方贵族在南部德意志推行领主制的做法已经到了登峰造极,还在于1525年爆发了伟大的德意志农民战争,无论是起义者提交的冤情陈述书,还是其颁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政策,都显示了要从根本上调整农村经济秩序的意图。笔者以为,地方贵族所标榜的农村秩序不过是旧有的封建领主制、农奴制的一种翻版,其结果是严重损害了农民与土地结合的方式和农业生产;相反,1525年起义者的经济政策,却是一种新制度,旨在通过改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维护和推进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近代性。
布瑞克指出:在政治结构的具体问题之外,普通人的要求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籓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1525年的思想家试图将这些要素纳入理论上可接受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体系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布瑞克怎样总结出这些目标的两个特征。首先,布瑞克是把农民运动放在现代化的框架里来探讨的,因此凸现了农民在建立新体制方面的作用。其次,农村社会的内容范围很广,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教育、社会平等各个方面。人民的革命既然与建立现代体制紧密相连,那么,没有民众的参与,欧洲的现代化就无法起步。布瑞克区分了古之法(为自己争取权力习惯法)和神之法(即利用不加修饰的“上帝之言”来改变社会制度),以为前者只是封建社会里农民保卫自己权益的传统运动,后者却旨在建立百姓共和国,即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人间天国”。
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呢?布瑞克认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布瑞克提出:既然农民运动“领地城市、帝国城市的平民和矿工都卷入了,那么普通人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泛呢?称这场战争为普通人的革命是否真的更恰当呢?”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考虑普通人的需要,因为农民和市民是联合在一起的,况且农村的社区组织和城市的社区组织也具有类似性。
这样,在布瑞克那里,现代化的人民性质(或称共和的性质)就这样被规定了:在他的著作问世前,少数领主、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用改进社会体制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也被当作一种了不起的进步被渲染;与此完全不同,布瑞克的农民学研究学派出现在伯尔尼,告诉人们: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只是指那种由人民直接参与、推动的、根据人民需要来完成的现代化。即使16世纪的德国民众尚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但是,他们无疑是建造现代社会体制的先驱,他们的伟大之处,应当为世人所重视。
我和布瑞克教授仅见过一面,却得以窥见他那良师、益友和思想家的风范。1998年的一天,我从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蒂宾根乘坐国际火车去伯尔尼寻找布瑞克。我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来听听布瑞克的教诲,二是要征求一下布瑞克教授的意见,是否同意我把他的名著《1525年革命》翻译成中文,并且在中国出版,以便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了解他的农民学研究学派的意义。
布瑞克教授是那种热情、友好、机智、幽默并且极富感染力的人:“你要研究农民,首先需要知道农民要的是什么”,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我们的谈话就这样无拘无束地展开了。我告诉他自己对他著作的批评意见:《1525年的革命》写得过于理性、系统化了,似乎完美到无懈可击的地步,这恰恰有点可疑,因为16世纪的德国农民,是无法具有这样的理性头脑的。我接着问:“自1975年《1525年的革命》出版,至今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你是否认为你书中的有些观点需要部分修正?”“不”,布瑞克说:“我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因为随着我现在研究的深入,我愈发感到自己探索的方向并没有错。”在这里,布瑞克表明了自己的旨趣:人必须不断向前走去,不断去发现去解决新的问题,而不作茧自缚似地把精力放在修正自己以往的观点。在布瑞克看来,一本著作不过是作者留下的一个脚印,只要前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却不必过于硬求每个步骤的标准化,因为那是极其危险的。
我把布瑞克包括在当代少数的最杰出的学者之列,不在于他思想的深刻性和创作了学术界公认的经典学术著作,而是他通过逻辑上的认真演绎,展现了他对农民和百姓的挚爱,即通过一种完整的有意识的学术劳动,在百姓前进的路上放上了一块指示牌。当我们在自由和枷锁之间进行方向选择时,那种只为精英和权贵服务的现代化观念逐渐隐退了。与此同时,普通人即人民的现代化进程却开始起步:不仅是在美丽的莱茵河畔,而且也在中国,勇敢并且是永不停顿地起动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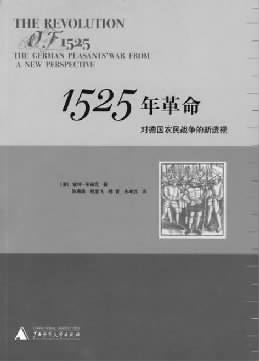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