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脑科学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每个具有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可能都在独自发呆的时候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是自我的主宰吗?还是受一堆神经元操控的傀儡呢?自由意志问题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重点,关于自由意志的哲学著述汗牛充栋。但这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科学家们的禁区,如果有哪位科学家敢贸然涉足这个领域,就等于拿自己的学术声誉和科学生涯冒险。但近些年来,科学家们终于决定放弃谨小慎微的做派,不再刻意回避意识和自由意志的问题。在一些科学家的不懈努力下,自由意志问题的科学化研究终于形成了一股潮流,并正在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在这些弄潮儿中,领军人物是两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克里克因与詹姆斯·沃森共同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获得了1962年的诺贝尔奖,埃德尔曼则是因对免疫系统的研究于1972年获得诺贝尔奖。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学术生涯投入到了对意识的大脑机制的研究。毋庸置疑,是以前的学术生涯积累的声望让他们有底气从事这项有争议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术氛围下,进行这样的研究所冒的风险是巨大的,也正因此两人的举动才更让人敬佩。
2000年之后,已年过7旬的埃德尔曼仍然保持着旺盛的产出,先后撰写了三本关于意识问题的书籍:《意识的宇宙:物质如何转变为精神》(A Universe of Consciousness: How Matter Becomes Imagination);《比天空更宽广》(Wider Than the Sky: The Phenomenal Gift of Consciousness;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二自然:意识之谜》(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Yale,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版)。埃德尔曼在书中介绍了自己的神经元群选择理论,并用其来解释各种心智现象。在埃德尔曼看来,要证明意识研究的正确性,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用提出的神经机制构造出人工意识。虽然目前离实现这个目标还很遥远,他却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在他的研究所中,以达尔文命名的神经网络机器人已经发展到了第10代,可以产生一些简单的认知行为。埃德尔曼的书虽然对大众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却极大地鼓励了学术界对这个领域的探索。
1994年,年近8旬的克里克出版了他关于意识研究的著作,《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Astonishing Hypothesis: The Scientific Search for the Soul;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在书中,克里克旗帜鲜明地提出:“科学的信念就是,我们的精神(大脑的行为)可以通过神经细胞(和其他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行为加以解释。”并对视觉意识的神经机制进行了阐释。作为这个领域的先行者,克里克并没有太多直接涉及自由意志问题,只是在书后附了一个简短的跋,说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并简要提到了“异手症”等脑损伤症状可能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这方面的实验和病例分析并不深入,用科学证据彻底否定自由意志的时机还不成熟。
克里克的另一贡献是,他当时带领的几位同事后来都成为了这个领域的佼佼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克利斯朵夫·科赫(Christof Koch)。2004年,科赫出版了《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理学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版),这本书对意识的科学研究进行了综述,并介绍了自《惊人的假说》之后克里克和他的研究的新进展。
迈克尔·加萨尼加(Michael Gazzaniga)是自由意志研究科学化浪潮中另一位重量级科学家,他以对裂脑症患者的研究闻名。
在上世纪60年代,医生开始对癫痫患者实施裂脑手术。裂脑手术能阻止癫痫病灶蔓延到另一半大脑。手术很成功,但人们发现,病人能够同时做不同的事情,比如一只手画圆,另一只手同时画三角形。加萨尼加与其同事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向裂脑患者的左脑闪现小鸡爪子图片,向右脑闪现雪景图片,然后让患者选择能够与他看见的图片相关联的图片,结果患者右手指向小鸡图片,左手指向雪铲图片。当被问起为什么这样选时,负责语言能力但又没看见雪景图片的左脑会回答说,是因为要用铲子打扫小鸡粪便。加萨尼加认为,右脑中的潜意识程序正确选择了图片,而左脑中的解释机制负责为行为编造合理的解释,当理由不存在时,它也会不断自圆其说。在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行为是一回事,意识对行为的解释又是另一回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脱节了。据此加萨尼加认为,自由意志根本不存在。在新书《谁人操控?自由意志和大脑科学》(Who's in Charge?: Free Will and the Science of the Brain,Ecco,2011)中,加萨尼加对此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
将自由意志问题的科学化推向高潮的是著名的年轻神经科学家大卫·依格曼(David Eagleman)的新书《隐藏的自我:大脑的秘密生活》(Incognito: The Secret Lives of the Brain,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依格曼是贝勒医学院感知与行为实验室的主任,从30岁开始就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数篇关于神经和认知的论文。值得一提的是,依格曼也从克里克那里受教良多。依格曼对研究方向具有敏锐的把握能力,并且能够向大众深入浅出地介绍前沿研究和未来的影响。依格曼从大众熟悉的各种错觉、通感、技巧训练、异手症、裂脑症等现象着手,逐步揭示出一个不可辩驳的惊人事实:意识活动只不过是次要的配角,是冰山一角,位于意识层面下面的无意识或潜意识活动才是大脑活动的主宰,是冰山的主体;人的行为更多是受无意识活动掌控。
在揭示出这一切后,依格曼并没有停下他的脚步。如果自由意志不存在,那么人们应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呢?这并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因为法律系统就建立在人们具有自由意志,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假设之上,因此自由意志问题的科学化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法律系统。1966年,查尔斯·惠特曼在德州大学冷血地射杀了13人,射伤了33人。惨案发生后,警官在惠特曼家里发现他还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母亲。看到这样的事情,每个人的第一反应可能都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事后对惠特曼的尸体解剖发现,他的大脑中长有肿瘤,严重压迫了杏仁核。杏仁核有调节情绪的作用,与恐惧感和攻击性有很重要的关系。知道了这些后,你对他的看法是不是有了变化呢?如果他活了下来,又该怎么给他定罪呢?
大脑决定我们的行为,然而在对大脑的影响因素中,有太多因素我们无法自由选择:基因、母亲怀孕时滥用药物、幼儿期受忽视、儿童期受虐、接触含铅玩具、环境、精神疾病,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大脑,从而改变我们的行为。在法庭上,如果精神病医生有证据证明被告患有某种大脑疾病,被告就会被轻判或免于刑责。在被告应当还是不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之间有一条界线,在界线的这边有罪,界线的那边无罪。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有越来越多的行为得到了生物学解释,也有越来越多的辩护律师用到这方面的证据,从而究责的界线被不断从无罪的一端向有罪的一端推移。而处于有罪一端的行为也并不意味着被告就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可能只是目前的技术手段还无法发现其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原因。如果自由意志被科学彻底否定,建立在自由意志假设基础上的法律系统应该怎么办呢?这条究责的界线又应该划在哪里呢?
这时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依格曼在书的最后给出了他大胆而极富争议的方案:法律系统的判罚不应再基于人们的意志和责任,而应着眼于服务社会的未来。刑期的长短不是基于报复的渴望,而是用再犯的风险来衡量:再犯的风险高则刑期长,再犯的风险低则刑期短。监禁的目的不再是惩罚,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为犯人提供帮助,改变他们的行为。为此依格曼特地提出了一个前额叶健身的方案,借助最新的脑科学研究成果,通过对大脑进行训练,提高大脑面对诱惑时的自控能力。
依格曼提出的这些建议肯定会引发争议。但面对这一全新的课题,我们不能苛求太多,毕竟探索才刚刚开始。重要的是,依格曼将法律系统这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带入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显然自由意志的科学化研究带来的问题还远不止法律系统,将来还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教育,一个学习不好、顽劣的小孩不能简单归结于品性不好,而应从大脑的角度分析其自控能力差的原因。
自由意志问题的科学化不限于学术界本身。近几年来这方面书籍的集中涌现并不是偶然的。除了学术发展阶段本身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市场的需求,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大众的关注,社会对自由意志问题科学化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潮流。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新书《自由意志》(Free Will,Free Press,2012)的出版则是大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达到高潮的标志。哈里斯是畅销科普作家,《信仰的终结》(The End of Faith)和《道德领地》(The Moral Landscape)两书的作者,从科学角度分别讲述信仰和道德问题,两本书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果要找一个人来通俗化地介绍自由意志问题的科学化,哈里斯可说是最合适的人选。《自由意志》的出版对自由意志问题科学化被社会接受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依格曼的观点类似,哈里斯也认为,否定自由意志并不意味着为犯罪开脱。他也同样指出,法律精神应该从惩罚过去转向客观地评价罪犯继续危害他人的可能性。否定自由意志不会让犯罪行为泛滥,反而能让我们更加“注重于评估风险、保护无辜的人和阻止犯罪”。
自由意志问题研究的科学化才刚刚开始,可以想见的是,它必将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社会。如果它不能改变我们的世界观,至少也会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看法。
(本文作者为《隐藏的自我:大脑的秘密生活》一书的中文译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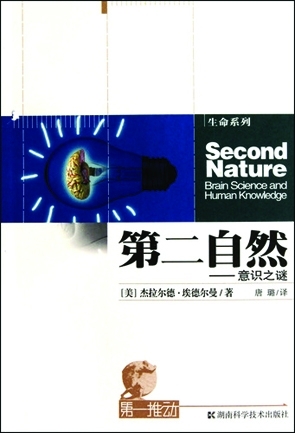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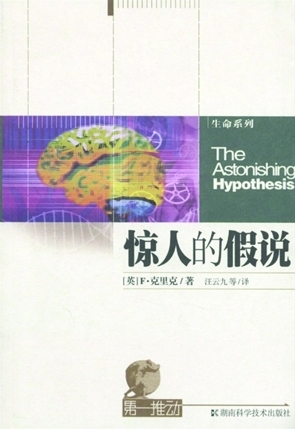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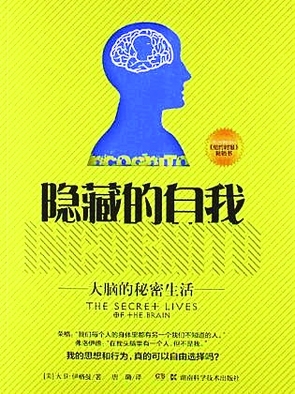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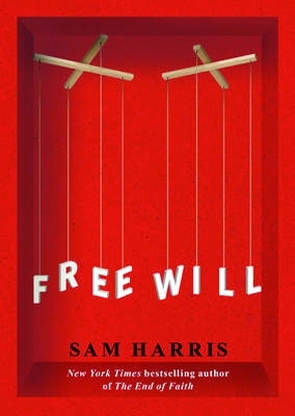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