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在人文学科领域,与相当完备的外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研究相比较,我国西方美术史与美术批评理论研究一直处于滞后和短视的境地。这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不断涌现的美术史与美术批评的重要文献未能及时地翻译进来。一旦少了寒灯苦烛的文献翻译工作,美术教育便难以推进。近年来,幸赖范景中、沈语冰等学者奋起直追般的努力,这一现状渐渐改观。但是,当这些“新批评”著作被引入之后,我们发觉,一种吸纳新的批评方法、凸显辩论性进展的西方现代美术史教材却难以寻觅,对于美术教育而言真可谓迫在眉睫。
这种对艺术史进行认知更新的渴求在近期得到了满足。由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购买引进、中央美术学院易英教授担纲主编的“牛津艺术史”丛书(第一辑)出版面世。其中,著名美术史家理查德·布雷特尔(Richard R.Brettell)的“现代艺术史”权威之作《现代艺术:1851-1929》(Modern Art:1851-1929)聚焦于现代艺术勃兴期,展现了艺术与文化、经济和历史状况复杂互动的发展状况,颇具洞见地强调展览制度、图像普及化技术与现代艺术的联系。此书将“新艺术史”和“新艺术批评”的诸多议题(女性主义与身体美学、社会阶级与意识形态、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等)鞭辟入里、包罗万象地容纳进来,摆脱了干巴巴的事实陈述,呈现出迷人的趣味和深度,不愧是“现代艺术史的必读之书”,也是“新艺术史”的典范导读著作。
新艺术史与艺术批评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左翼激进思潮、女性主义、欧洲文本和社会学理论的促动下,大量质疑艺术史方法论的理论批评之作轮番出现,迅速改变了艺术史研究的方向。
60年代中后期开始,政治和社会的激进思想涌进了文化讨论。经历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新艺术史一代宗师T.J.克拉克(T.J.Clark)在1974年的一期《泰晤士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中撰文提出:应该对艺术史进行重新叙述。他认为,艺术史的主题应该回到那些具有知识分子的严谨和责任感的艺术史奠基者(里格尔、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身边,并指出艺术史研究应从丰厚的传统源泉中汲取灵感。艺术史的实践不能脱离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沦为实证主义和考古学。自此,艺术史研究辐射性地与社会学、经济学、技术史学、政治学、性与精神分析学产生密切联系。
布雷特尔教授的求学、著述生涯适逢 “新艺术史”转向。他的《现代艺术:1851-1929》显示出“艺术社会史”视角,注重考察现代艺术产生的历史环境——经济、政治和技术的飞速变革,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与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此书副标题“资本主义与再现”所指明的,这“是一本将社会-政治力量看作现代性首要因素的书”。此书被选入“牛津艺术史”丛书,从侧面印证了“新艺术史”在当代西方艺术史界的统治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第二章《现代艺术的条件》直接回应了克拉克《艺术创作的环境》(The Condition of Art Production)一文。布氏从“奥斯曼巴黎大改造”论及城市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并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艺术商品化和艺术批评是如何推动、塑造现代艺术景况的。他还批判性地介绍了历代马克思主义艺术社会史家的观点,并在第六章《社会阶级和阶级意识》中借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等作品,深化了对现代图像再现中“社会阶级”问题的认识,饶有兴味地比较了现代艺术中农民和工人阶级形象,读之豁然有得。
“性与身体”这一前沿辩题也在书中得到体现。布氏引用了著名女性主义艺术史家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和诺克林(Linda Nochlin)的观点,但其阐述视点却超越了性别论: “现代艺术的注意力聚焦的并不仅是女性淫乱者的身体,而是人体本身。”对现代艺术中的裸体与色情作品、生命周期主题、寓言等有趣联系的探讨,特别是对高更画作的“殖民主义和裸体肖像”解读,无疑是此书的亮点之一。
现代展览、图像流通和图像/现代主义
布雷特尔教授不仅是国际著名印象主义和1830-1930年间法国艺术的研究权威,也是享有盛誉的博物馆长和策展人。他曾担任芝加哥艺术学院欧洲艺术馆长,参与筹划多项博物馆计划,如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和伦敦国家美术馆等,还是FRAME(美法艺术交易协会)的协调会长。这一职业背景使他尤其注意现代艺术的展览状况,及其在现代艺术发展中的作用。
在《现代艺术:1851-1929》导论中他写道:“本书的限定参考标准所确认的是,现代艺术是并继续是展现在眼前的城市景观的一部分,现代艺术的展览被置于城市观众的不同群体面前,这些展览对于理解现代艺术的本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要对现代艺术进行忠实的研究,就必须将艺术品的公众展览与艺术品的个人创作同等对待,共同着眼。”不管是科技工业展览还是艺术展览,还是政府、企业或个人举办的展销和展览,都对现代艺术理念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布氏强调,展览本身便具有纯粹的现代性。《现代艺术》描述的源点时刻不是1846年波德莱尔写作《沙龙画展》,也不是1863年的落选者沙龙,而是1851年,那正是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举办的年份,而1929年则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向公众开放的年份,它将现代主义制度化为20世纪再现的官方模式。
作者认为,1851年世界博览会显示了全球意识、工业主义和殖民主义,同时也定下了现代生活的主调:没有了边界的世界(world-without-borders)。图像世界在复制媒介的工业化、图像流通的全球化浪潮中成长起来,影响所有城市人口。石版印刷术、摄影技术等与现代展览一样影响了现代艺术。在19世纪与20世纪初,“图像流通”急剧频繁,博物馆、艺术交易市场、商业画廊急剧增长,艺术家便以千变万化的方式利用所能接触到的艺术复制品或艺术真迹。布雷特尔指出,从象征主义到超现实主义的各派艺术家们共同创造了一种可称之为“图像/现代主义”的新现代主义。这是一个新名词,它将现代艺术史拉回到以复制技术、图像传播为底色的历史画卷之中,可谓别有新意。
现代艺术的殖民主义、民族性与国际性
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使现代艺术世界的“欧洲-全球性”得以形成,这一过程亦伴随着“殖民主义”。一直以来,高更被冠以“殖民主义画家”名号,他抛开现代城市文化的“逃离”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的。布雷特尔却不这样看,他的结论是:高更完全清楚自己的现代主义特性,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在地球上寻觅世外桃源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那些以往指责其画作《死者灵魂的审视》体现了“殖民地性别歧视”的文章都错了,此画正是高更对异族统治的质问,这才是高更更大的主题。布雷特尔指出,殖民主义系统允许高更去探索欧洲以外的世界,但欧洲文化却始终与他同在,这无疑是极其新颖的观点!
布雷特尔的观点可能会让民族主义者不满。他认为,即使是艺术中的民族主义,也是具有国际尺度的,就算是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激进而自觉的墨西哥艺术,同样受到了源自于巴黎-欧洲、伴随着现代技术进步与城市资本主义而生的现代艺术思潮的影响。
正因为这种全球性的开放视野,使得这本精美著作超过一半的插图都不是法国作品。像波兰人马泰伊科(Matejko)、俄国人康定斯基(Kandinsky)等,他们往往被本国认为是 “现代世界”大环境中坚守民族文化的民族财产。这种观念显然太过守旧,因为在这个全球化图像流通的时代,现代主义早已呈现跨国性,民族主义往往被利用为推销工具,反过来证明了现代艺术的开放性、渗透力,以及可交易性,布雷特尔说,正是这些特性,才使它们具有了现代性,而不是它们的特殊形式和图解特征,更不是它们的内在观念。
最后,《现代艺术:1851-1929》在后记中告诉我们,正是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城市景观和生活的现代性、世界化的文化交流,定义了现代艺术自身的价值,“只有拥有了这些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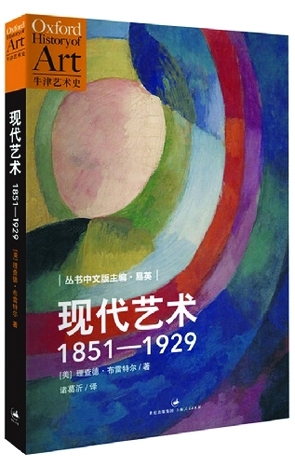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