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写这本诗集,用心之一,在如何于现代语境下,重新认领汉字的神奇。在他的理解中,汉字的确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个符号系统:它是语言,它又不是语言,因为它不会说话;它是图画,它又不是图画,因为它不描述;它是书写,它又不是书写,因为它呈现自己,并不用替代来再现。说它是个符号系统,是因为我们用它来做日常生活的传达:卖掉田里的青菜萝卜,牌价几何;买进《道德经》三千言,无价之书,其中完全没有符号的等价关系。我们至今能读懂《论语》,哪怕孔老夫子说“学而时习之”,口音比今天的广东话还难懂,比今天的上海话还“难听”。而任何其他民族,要读懂他们“自己的”三千年前的古籍,就要另学一种语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血统已经混杂,却依然是一个伟大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而欧洲人基因类似,却四分五裂成几十个民族,各拥有自己的一堆诗人,在鼓噪自己的诗句。
因此,毕加索说他愿意做个汉字的书法家,“如果当不成毕加索的话”;因此当庞德说“我们在汉字中找到一整套价值观,就像文艺复兴找到希腊”,纳博科夫闻之大为惊恐,气急败坏地骂庞德是“老骗子”;因此那个天才的保加利亚女子克里斯台娃,发现汉语实际上有两套语言:汉字书写是“生成文本”,像根茎,可以长出许多不同的口语式的汉语土豆,作为“现象文本”。因此沈奇发现汉字魔术般地随机、随意、随心、随缘。是的,汉字本质上是诗性的,只有汉字,才是诗意栖居的家园:其他语言是砖块砌成的,汉字则是绿莹莹的婆娑树盖。
沈奇写这本诗集,用心之二,在如何于现代语境下,重新认领禅的神奇。多少现代诗人向往禅诗,犹如大旱之望云霓:中国汉语诗歌发展到新诗,后天失调,因为它用的语言不是诗的语言。现代汉诗,被沈奇妙称为“一个伟大而粗糙的发明”,长得太难看,实际上是个畸形儿。伟大是让步修辞,是因为只此一个,不伟大也只能伟大,而粗糙确是人所共睹。但是现代诗歌又是先天太足,中国文化史的积累足够丰富,其中的一个镇宅之宝就是禅诗。
禅非常神奇,它是靠自己从内部解构才得以存在,也就是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解构自己:说出来的就不是禅,不说出来的才是禅,禅就是说了没有说的东西;但是诗是禅翻个面儿的镜像:写出来的才是诗,不写出来的不可能是诗。所以禅诗是双重解构,而且是从相反方向解构:禅诗因为是写出来的,必不是禅;禅因为拒绝被说出,因此不会进入禅诗。如果一定要形诸语言,禅要说得笨拙,诗要写得漂亮,完全是南辕北辙:禅诗如果可能,必定是吞噬自身的意义漩涡。
我们写诗读诗的人不可能得到禅,我们只是与禅在玩游戏;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得到诗,我们只是让诗在玩我们。这种意义的逗弄,才是诗的真谛。如果我们真正把意义抓住,我们就扼住了自己的喉咙。只有在禅诗中,我们才真正进入了人生的游戏:我们作为凡躯之人,肉身之人,心里灌满七情八欲的脏秽,得到禅悟是非分之想,要想读一首诗的短短几行字,就得到禅悟,岂非狂妄?
既然禅不是禅诗,禅诗说的也不是禅,那么是否诗必非禅,禅必非诗?那么现代诗人写禅诗不是注定失败?也不是,因为他有一套接近禅境的工具,那就是汉字。无怪乎教主菩提达摩知道,他在用梵文或巴里语的印度,不可能有传教的希望;他也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这个用特殊符号当文字的中国人,以及跟着学的韩国人和日本人,那里才是禅的希望所在。于是佛劫之后,达摩祖师一叶过海,来到东土;一苇渡江,南北景从。
汉字是诗的符号,也是禅的符号,汉字是不说出来的,是一种沉默的文字:一个“日”,可能读成ri,读成zhi,读成ni。汉字是不再现的,是一种非图画的图画文字,它超越此解彼解,自成一义。静观此字,犹如遥望西天海上那悬鼓之日。
由此,沈奇说,当他写下“茶渡”两字,诗已经写成,余下的诗句,只是给出一种衍义可能:它可以是crossing after tea,可以是crossing while drinking tea,可以是crossing by tea:这些翻译都是解释,这些解释都马马虎虎可以,就像“茶渡”两字可以用任何笔墨,写成任何形状,但是写出来的都不是原来的二字。面对此种文字,西方译者肯定束手无策,他们的逻辑语言肯定迫害诗意,破坏禅悟。哪怕模仿中文,写成tea crossing,趣则趣矣,已经失魂落魄。而东方诗人和读者望之莞尔一笑——
没有比现在更暧昧的时刻 (《晚钟》)
静下来,稍安勿躁。“茶渡”对面,就是婆罗密,就是Piramita,就是彼岸。
沈奇的《天生丽质》是一本奇书,它让三个对抗的元素——汉字、禅、现代诗——相撞成为一个可能。就像建在瑞士地下五百米深的环形隧道里的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在近光速的粒子相撞后,或许会产生一个黑洞,宇宙生成状态之前的黑洞,吞噬一切的黑洞:于是我们这个浑浑噩噩平平板板自以为了不起的庸常世界毁灭了,在几十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内,但是另一个宇宙从黑洞里爆炸产生了。那是个什么样的宇宙呢?是不是会充满诗意呢?是不是会有生活的生灵来感知它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必知道,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宇宙塌缩和诞生的辉煌,我们已经可以想象一切:我们的想象已经能够超过一切。
……那人兀自涉水而去/身后的长亭/尚留一缕茶烟/微温 (《茶渡》)
汉字在理性的宇宙创造一个黑洞,在那里,几世几劫世界冰凉之后,茶尚有微温,因为我们已经得到禅悟,我们可以释然。《观无量寿佛经》第一观,就是“日观”而得“方便”。太阳是我们心中造出的。看到日落之后,世界已经新生——另一个非此色非此法的世界。那么眼睛还有何用?诗还有何用?留一缕余温,提醒我们,凡人肉眼竟然也看到过如此天生丽质的境界。(赵毅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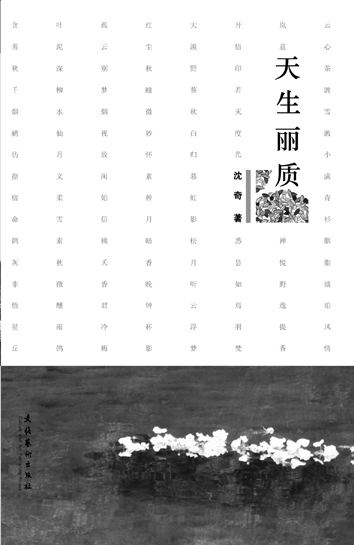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