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期以来,一直喜读刘绪源先生的理论批评文字。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自己也做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我的学术成长曾多次受益于绪源先生的提掖、指导,他是令人钦敬的学术前辈、师长;另一方面,则源于我对绪源先生批评文风的偏爱、激赏:明明是一清如水的闲谈,其间却如似如缕,寄寓深广;看似随意率性的时评,内里却涵容宽阔,思维缜密。如此一来,他的批评文字往往融敏锐、犀利与睿智、深邃于一炉,呈现出理论批评所难得一见的优雅和诗意。这在今日西方术语泛滥成灾、批评文风艰深晦涩的当代文学批评界,呈示出一种有别于“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的“独立批评”之风。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一清如水”“极清浅而又极深刻”的批评文风对于当下饱受诟病的“学院派批评”和“媒体化批评”不独显示了鲜明的对比、参照价值,更有映衬文弊、倡示风尚之功。
绪源先生的批评文风并非独创,而是有所师承的。正如他在《学术美文传统不应丢弃》一文中所述:“五四以后那几代学人和他们的文章论著……也深入到大量艰深的学术领域,其中也包括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但他们的文章,仍能写得一清如水。”作为学术兴趣广泛、且对现代文学深有研究的当代学者,绪源先生不仅对前辈学人的学术美文传统深以为意,而且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中身体力行。一个文学理论研究者,自己如果搞过创作,当提笔再来谈论作家、作品时,理性评判之外,自然会多一些直觉的敏锐和感性的深邃,让人于感受深沉思维力量的同时,顺带欣赏到了鲜活而饱满的审美体验和理论激情。这不啻为一种理论批评创造和思维阅读享受。
通观绪源先生收录于《儿童文学思辨录》中的文章,大多虽为文学时评,却往往并不拘泥于单一作家、作品立论,而是由具体篇章、现象的解析拓延开去,进入更加宽广的文学范畴,通过抽丝剥茧般层层剖析,从中引出深刻的理论命题。比如在《波兹曼的失误与中国式误读》一文中,当就“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与王泉根先生展开理论商榷时,绪源先生写道:“美并不是一种表现形式或表达方式,被用以表现‘真’或表现‘善’,从而可以‘以真为美’或‘以善为美’,美是人类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在这一点上它是与真并列的,二者可相互支撑,相互辉映,却未必要以另一个为基础……相反,恰恰倒是‘善’,是必须以‘真’和‘美’为基础的。”由对童年现象的不同理解,引申出美学层面基本命题的辨析。比如在《一只鞋子的故事》中,在陈述了与青年批评家的观念交锋后,绪源先生又写到:“文学性就是文学性,这本来就是统一的。不能说中国有中国的文学性,外国有外国的文学性,王蒙有王蒙的文学性,《故事会》有《故事会》的文学性,它们都不可互通(即不可比)。只能说,在不同地域、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中,文学性的表现形态会有不同,文学性的含量会有高下。”这是就文学评价尺度的具体争鸣,引出了关于文学本质属性的理论辨析。类似这样草绳灰线、寄寓深广的“时评”,在文论集中“文心雕虎”这个小辑里中还有不少。
同时,刘绪源关注创作现象,在喧嚣、繁复、斑驳、迷离的童年文化世相中秉持文学性原则,每每发出让人震耳发聩的审美判断。这方面,最典型的文例就是《试说杨红缨畅销的秘密》。这是一篇曾引起儿童文学界极大关注和争议的文章。面对在原创儿童文学中缔造了销售奇迹的杨红缨系列作品,刘绪源没有妄下断语,而是操起了“经典儿童文学”这把尺子,横度竖量,比照出了畅销故事与世界经典儿童文学的差距,揭示出“畅销”背后的秘密,以及“畅销”与“文学性”之间既疏离又呼应的奇妙关联。
坚持事实论述,弃绝泛泛而谈,倡示以文本细读与艺术分析为研究策略的儿童文学批评之道,此可谓绪源先生对当下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一大贡献。这样的文章,在论集中为数不少。比如,新世纪前后,国内文学界曾对世界超级畅销童书《哈利·波特》的文学性持质疑乃至贬斥态度。当此争议时刻,刘绪源没有仓促发声,而是选择深入文本解读和艺术分析,让事实说话,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尽管其论尚属个人判断、一家之言,但因其西方幻想文学传统参照下文本细读和艺术分析的批评策略,比起当今文坛上盛行的那种不读作品而雄辩滔滔,弃绝分析却高谈阔论的“空头批评”来,更让人信服。原因很简单——这是一种有品味、有体察、有分析、有判断,血肉丰满、体骼清俊的“真批评”“阳刚批评”,不是满口术语、装腔作势、昏昏昭昭的“死批评”“石化批评”,或趋炎附势、邀功献媚、空洞无物的“伪批评”“软骨批评”。
综观刘绪源的批评文字,横贯古今,总揽中外,以儿童文学经典为参照衡定现实创作,厘清儿童文学发展脉络。我们通常所见书评,大多就作品而谈作品,视线逼仄,涵容拘圄。而绪源先生写书评,却总能将所谈作品置于更加宏阔的文学背景中来上下对比、引证分析,最后再娓娓道出其文学层面的利弊得失和审美范畴的价值定位。比如《作家丢掉了什么》中,由获奖儿童小说《蔚蓝色的夏天》,谈到创作贵有“真生命”;还比如《重新审视“早恋”话题》里,从德国儿童小说《本爱安娜》所涉及的“早恋”话题,论及儿童文学中,“青春期情感”题材抒写所应该遵循的“人性原则”……等等。
除此之外,绪源先生还在一些评论文章里谈到了儿童文学新人、新作。如在《青春做伴好还乡》里,联系参与评奖时的阅读感受,谈到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中文学性与独创性逐渐衰退的趋向,在深表忧虑的同时,也为《到你心里躲一躲》《我和妈妈的粥》等新人新作在童年情感上的卓异表达不吝赞美之辞。而对一些成名作家的新作,绪源先生也往往能在第一时间及时关注,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赏、分析。比如《非凡的马鸣加》中,对郑春华“马鸣加”系列的推崇;比如《作家成熟需要多少年》中,为彭懿儿童幻想儿童小说新作《欢迎光临魔法池塘》大声叫好;比如《生命中不能缺少之重》中,对周锐童话集《出窍》当中诸多篇目生命蕴涵的深度阐释;还比如《一篇小小杰作和它的当下意义》对张弘短篇少年小说《玫瑰方》文学性奥秘的细致剖析……在这些篇章里,绪源先生关注儿童文学现实创作,为老作家宝刀不老、笔耕不辍欣喜,为中年作家才思如涌、频出新作欣慰,为创作新秀出手不凡、才华初露鼓呼,充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儿童文学批评家文学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总而言之,在笔者看来,《儿童文学思辨录》作为文论集,既是一位成熟的文学批评家对儿童文学林林总总诸多命题静观默察、洞幽烛微的思维结晶,也是一个秉承现代学术美文传统、治业严谨、学养深厚的当代学者对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逡巡、俯瞰的批评成果。其于诸多篇章所倡示的审美高标、文学原则,值得我辈儿童文学同道深思而慎取。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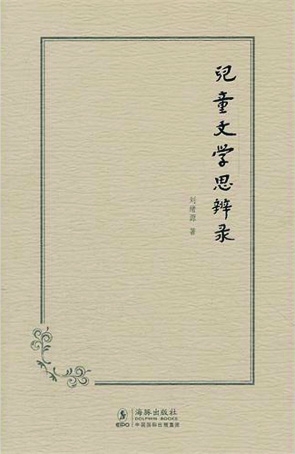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