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
沈石溪(儿童文学作家)
吴秀明(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
刘玉洪(中国科学院哀牢山生态站常务副站长)
读书报:在三位看来,生态文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吴秀明:所谓生态文学,首先与人类的生态意识是密不可分的。就人类的发展来看,生态意识几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潜意识,比如早期人类对大地和各种自然神的崇拜。在我国传统文明中,也一直受着“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注重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和息息相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受进化论观念和工业文明的影响,人类开始对自然进行肆意妄为的破坏,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和质疑人与环境间的主仆关系和潜在的排序规则。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学中,就是自然界中的许多物种以新的姿态进入文学话语,生态文学也就成为新观念下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
沈石溪:由于人口爆炸,由于掠夺性的资源开发与野蛮的生产方式,地球上的物种在迅速地减少,大片森林毁坏,许多动物濒临灭绝,大自然食物链断裂,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出现了沙尘暴、温室效应、臭氧层破洞等等生态危机。我们要修复良好的生态系统,建设绿色家园,除了植树种草、减污降耗等基础性建设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良好的生态道德。什么叫生态道德?就是要用平等、自由、博爱、仁慈之心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可以这样说,人类的道德光芒不仅照亮人类社会,还要照亮大自然,照亮动物世界。
读书报:关于生态文学是否有明确的定义呢?
吴秀明:关于生态文学目前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比较通行的看法是,生态文学是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文学,是揭示生态问题的文学,也是面对问题试图摆脱危机、探寻生态之路的文学形态。它反对人类对自然的肆意干涉,提倡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大地伦理”,表达关于生态危机的警示,呼唤着人与自然万物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协调,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读书报:生态文学研究和写作的现状如何?
吴秀明:生态文学的研究在国外开展较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具有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形成比较晚,作家有意识地思考自然生态问题,出现带有普遍性创作思潮的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逐渐行情看涨,尤其是像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等一批作品的相继推出,它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文学似乎再也不能忽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存在了,当然它也由此引发了一些争议。
读书报:文学介入生态保护的作用如何呢?
沈石溪:我是个作家,我热爱动物,所以写动物小说。除了用文学表达我的动物保护理念外,我也曾试图用实际行动来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大约十几年前,我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想在哀牢山自然保护区开办一个野生动物救护站,为那些受伤、丧偶或遭遗弃的野生动物提供救援。这纯粹是一项公益作为。遗憾的是,由于审批手续繁多和其他种种原因,这一美好的设想至今仍是纸上谈兵。我觉得我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生态保护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所以我只能继续埋头写动物小说。潜意识中我可能是想通过动物小说创作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实现自己的梦想。
刘玉洪:对于生态的保护,是需要全民参与,但是生态环保的意识是需要时间及科普教育来完成的,所以非常需要文学的介入,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的介入也是必须的。
读书报:沈石溪是知名的动物小说作家,最近在浙少社最新推出了两本生态文学作品。那么,您认为动物小说与生态小说两种创作形态的差异是什么?
沈石溪:其实作家的创作,并没有事先过多地考虑创作的形态。给文学创作划分形态,更多的是理论家的事,作家不应该过于越俎代庖。但创作《野马归野》等作品时,我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作品往生态文学上定位,这不是赶时髦,因为这之前,我的不少作品人们已经将它归类为生态文学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总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在强烈地驱使着我,用理论家的话来说,也许就是那种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吧。
读书报:那么,在环保专家眼中,文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对推动生态保护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玉洪:对环境的保护,对生态的保护,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那些兢兢业业奋斗在环保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外,形成一个全社会人人讲环保,人人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氛围,十分必要。环保不是空的,而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积聚而成。环保也不是象牙塔里少数几个人的事,而是事关每一个人的生存环境,事关你我他。这就需要大家的参与,需要舆论及宣传的广泛配合,环境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需要时间。我不太懂文学,单从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说,我认为生态文学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文学家参与生态保护事业,我们的生态保护事业就更有希望了。
吴秀明:很多时候,文学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意无意地会承担起某种社会责任,体现出某种社会关怀。比如国外盛行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学,成为当时启蒙运动解放思想反封建的先导。再比如中国的五四新文学运动,对破除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枷锁也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文学的敏感敏锐,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秉性特点,往往会使文学思潮领先于社会思潮,进而对社会进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影响人的思维观念、价值认知等方面,文学确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青少年读者会因为什么原因对生态文学感兴趣?
吴秀明:其实,儿童文学本身就是生态意识最强的一种文体,它所创造的形象特别是动物形象,所宣扬的真善美主题,其实是更加接近自然,接近原始的。儿童文学写生态也一直是我国20世纪文学的一个传统,但之前可能比较多的是体现在散文中,八十年代以后则更多体现在纪实文学和小说中。在我主编的“文化现代性与生态文学前沿丛书”中,收录了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生态小说《野性的呼唤》和沈石溪先生的《最后一头战象》。这些中外生态文学作品都是现在的青少年读者十分喜爱的。
当然,同样是生态文学,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还是有区别的。不少成人的生态文学毫不避讳动物世界的血腥残酷,往往是借动物的行为和语言表达现代性的文明理想。而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生态文学,更加强调动物的主体性,从动物的角度看世界,本质上表达的都是爱的主题。我以为,儿童的生态文学要吸引青少年读者,首先是要符合儿童文学的特征,其次是加入生态的元素,遵循动物的特征描写动物的生活和情感,给人一种新鲜感和新奇感,这样自然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沈石溪:喜爱动物是孩子的天性,很少有孩子不喜欢动物的。我始终觉得,孩子喜爱动物,也许是因为人和动物之间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不应该高高在上,人和动物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别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和谐相处,取长补短是最好的相处之道。在情感世界,在生死抉择关头,许多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忠贞和勇敢,甚至常常令人类汗颜。动物的生态,也是人类生态的一面明亮的镜子。(本报特约记者 叶 子)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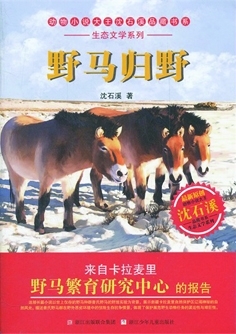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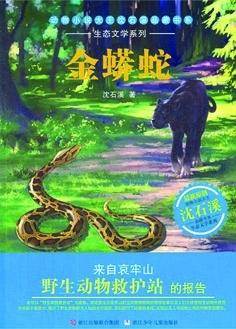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