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钱基博诞辰120周年华中师大召开“钱基博与国学研讨会”,出版《钱基博年谱》之后,从前期零星出版钱基博著作,到现在几家出版社系统出版规模庞大的《钱基博集》、《钱基博著作集》以及“钱基博作品系列”,一个“诂经谭史、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国学大师形象逐渐显得轮廓清晰起来。在钱基博这些不断发掘出版的著作中,注定会有一个巨大的遗憾留给后世学人。那就是钱基博一生规模庞大的日记,将再也不能重现于世。
钱基博一生读书治学异常勤奋,终生坚持记日记,著作也写在日记中,绵历五六十年,临终留下五百余册《潜庐日记》,堪与清人李越缦媲美。钱穆先生称之“平生所见,治学勤笃,唯梁溪钱子泉也”。1957年11月31日,钱基博在病痛的折磨下,在极度的压抑与忧郁中,溘然长逝,享年71岁。弥留之日,其将自1937年任教前国立浙江大学起,所著论学日记,历时逾二十年,都数百万言,及其他手稿,全部留给女儿女婿保管。1937年前的日记,则因抗战初未及运出而丧失。其实早在1942年,在国立师范学院时期,钱基博就已将二百余册日记赠与石声淮,作为新女婿的礼物,也寓意授受老先生读书治学之衣钵:
吾箧中日记二百馀册,即以相付;以翁婿言,则觌仪也;以师弟论,则衣钵也!吾虽老病,未尝一日废书;而来湘三年,读书三千六百馀册提要钩玄,皆有日记;而湘贤著书,居十之三。尔声淮尚其善承乡先辈之贞性毅力,不懈益修以努力所学所事,而无负国家作育之意;此吾之望也!吾儿锺书来书,欲为我撰年谱;傥有资于日记,尔声淮其助成之!”(钱基博编《金玉缘谱》)
可见老夫子是何等看重这些日记。钱基博当年力排众议要把女儿嫁给石声淮,也是何等的信任他。钱基博因为习惯把读书心得、摘钞等写在日记中,所以这些日记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学术价值极高。1935年,钱基博就说过:“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6期,1936年3月)可见一斑。
那么钱基博1937年后的日记,为什么不能再现于世呢?这是因为自1966年“文革”伊始,他的所有日记、遗稿都被“付之一炬”。1983年,钱锺霞在其整理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一书后记中云:“1966年遭罹浩劫,坐视先父仅存之手泽毁而不能救,毒楚何如。而《清代文学史》遂无一字遗留。”有人说:“文革中全部日记尽毁于火,《清代文学史》亦无一字孑遗,积之艰而毁之易矣。”(姜晓云:《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钱基博学术研究》第425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都没有明说这一把火究竟是谁点燃的。但多数看法是毁于红卫兵之手。傅宏星《钱基博年谱》:“‘文革’期间,子泉先生遗留在湖北武昌华中师范学院女儿女婿家里的五百余册、绵历数十寒暑的《潜庐日记》遭到查抄、批判,并被付之一炬。”学者王玉德:“钱基博勤于写作,每天都要写读书笔记,计有五百余册的《潜庐日记》,在十年浩劫中被查抄焚毁。”(《钱基博学术研究》第131页)《辉煌的钱氏家族》:“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钱基博一生五百多册《日记》,被‘跳踉叫嚣,如中风疾走’的无知少年付之一炬。”(《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8期)1979年,钱锺书在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他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有人问及钱基博,他庄重而惋惜地说:父亲其实还有许多未刊的遗稿,包括日记、文集等等。因为晚年与幼女同住,所以稿本多存于武汉师大教书的、钱先生的妹夫家里,“文革”时期被红卫兵们统统烧了!(孔芳卿《钱锺书京都座谈记》)他也认为父亲的日记被红卫兵所毁。
当所有人都以为钱基博的日记毁于红卫兵之手时,王继如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才透露了事情的真相。他在《钱锺书的六“不”说》一文中说:
钱基博死后,留下几百册日记,其中大量的是学术笔记(钱基博的许多学术著作都是从日记中抄录而成的,如《中国文学史》《湖南近百年学风》等),由石声淮保管。“文化大革命”中,石鉴于笔迹留存之可怕,遂全部销毁——当时连郭沫若都说过他的著作应该全部销毁,遑论他人。“文革”结束,石的朋友们无不责怪他毁弃老师的心血。他非常无奈,说当年投信错了,汲取教训烧毁日记又错了,如何是好呢?(《文汇报》2009年8月24日)
这则消息出来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如在豆瓣网“钱锺书小组”内,“钱学”爱好者们就对石声淮投之以最严厉的声讨。有人认为:“石先生难道就不能学钱锺书,把钱老先生日记中涉及私人的部分挖掉吗?把与‘嘉定钱氏之史学’‘后先昭映’的无锡钱氏‘集部之学’,付之一炬,实在是太残忍了。钱老先生地下有知,怎能瞑目?”
其实从思想改造运动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内,运动迭出,文人学者要坚持写日记,并真实完整的保留下,那是需要胆量与勇气的。“文革”中曾代替老师陈寅恪批斗并以此为荣的刘节先生,解放后一直记日记,但是简之又简,到“文革”时期日记最少时只有三个字,应该是怕给人留下把柄。钱锺书的清华老师吴宓,一生把写日记当做头等大事,事无巨细,记载极其翔实,连续性很强。但即使如此,1949年和1950年的两册日记却各仅存四五篇。原来,这两册日记,“文革”中吴宓交给朋友代为收藏,但朋友担心日记惹祸就将它焚毁了,他深为痛惜。同是在日本京都大学那个小型座谈会上,钱锺书说:在同一时期、同一环境之下,他岳父为了避祸,把他珍藏的小川环树富有欧阳率更书法风致的信,统统付之一炬,以免“里通外国”的口实,同样是无可弥补的损失。钱锺书和父亲一样,一生坚持写日记和读书日札,但在五十年代还是毁掉一小部分。“锺书起先把中文笔记和日记写在一起,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传闻学生要检查‘老先生’的日记,他就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所以这部分笔记支离破碎,且散乱了,也有失落的部分,整理很费工夫。”(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39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现在看来,钱锺书自己尚毁日记,何况托付他人?
平心而论,在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下,以钱基博的死前身份,和他一贯敢想敢写敢说的作风,加上石声淮的个性,烧毁日记也未出人意料之外。1957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帮助党整风。这一年,年刚古稀、身已患疾、作为政协委员的钱基博,响应“鸣放”号召,抱着切实帮助执政党整风的态度,“本着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良好愿望”,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写了一封后被人称为“万言书”的信。信中,他提出了很多事关党和国家建设大计的真知灼见,言语直率,措辞尖锐,对社会上、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毫无顾忌的提出看法。钱基博让石声淮寄出“万言书”,而石心有顾忌,迁延多日,朋友也都说不寄为妥,但最终拗不过老泰山的催促,还是寄出了。
6月,“反右”开始。钱基博的“上书”震惊湖北省委。省委当即将这封信转交中共华中师范学院党委,要求学校组织对其批判。1957年9月,历史系和中文系组织教师连续几次对他进行了批判。钱基博此时的身体,已是一日不如一日,鉴于此,“校党委特许他待在家里,不参加批判大会,批判大会由他的女婿、原中文系教授石声淮代为出席,批判大会结束后,再由石声淮向他传达批判意见。”(《钱基博学术研究》第402页)在这个批斗的过程中,以及去世后,他是否被打成“右派”,在学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没有来得及给他戴上“右派”的帽子他就去世了,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说,他早已内定为中右分子或右派分子,甚至是“极右派分子”,鉴于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告诉他而已。
以钱基博去世前的这种身份,“文革”开始,石声淮自然害怕被抄家,害怕白纸黑字的日记惹祸,抄家不仅自己遭殃,可能会连带出家人的不幸,对此他早已心有余悸——“反右”时替岳父挨批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与其等人来烧,还不如“先下手为强”,一把火烧个干净。或许,他的初衷还是出于保护岳父,只是全然忘记那些文字的价值了。傅宏星先生曾私下对笔者说,石声淮即使不烧日记,以钱基博“内定极右分子”的身份,他的日记也在劫难逃。石声淮的无奈凸显出那种环境下知识分子被形势左右而无措的历史现实。对此我们只能报以同情之理解。
如果一定要说这是谁的错,那只能说这是历史的错,是一个疯狂时代造就的错,而不是某个人的错。这注定是一场悲剧。“文革”之中,又何止一个如石声淮者呢?正如有些读者说的:“可恨的是时代,可惜的是文献,可怜的是人。我读石先生的‘无奈’之辩,倍感凄凉。”(豆瓣网“钱锺书小组”)钱锺书在京都大学那次座谈会最后也说:“文革”期间,更大的损失、更惨的遭遇,何只千千万万?自己的损失,相比之下,也算不得甚么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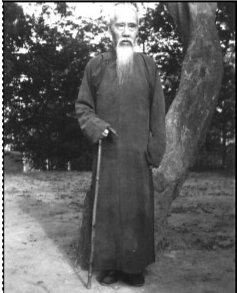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