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患者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错误的治疗。
我这样说,很多人一定不信。事实上我过去也不会这样想,直到自己也成了一个癌症病人,有了一些切身体验,又有很多癌症患者的经验教训做参照,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2007年2月,我病倒了。医生在我的颅内发现两处病灶,疑为“脑瘤”。两天后又在我的左肺发现肿瘤,由此诊断“肺癌、脑转移”的概率为98%,也可以说是“肺癌晚期”。医生当时认为,我已经活不过三个月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我的家人都蒙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与死亡如此接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癌症患者的恐惧和绝望。
我一向敬仰视死如归的人。那些勇敢从容地走向死亡的癌症患者,曾深深打动了我。有一段时间,我努力说服自己,像他们那样平静地迎接死神的降临。可是说老实话,我当时想得最多的不是死,而是生。因为死毕竟不是我们的追求。
我不断地追问自己:
难道癌症真的就是绝症?
难道癌症病人真的就没有生路?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寻找康复之路。我在一次手术中切除了左肺的恶性肿瘤,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手术切除脑瘤的治疗方案。我拒绝了一些“抗癌特效药”,也拒绝了化疗和放疗。术后出院时,我甚至连一片药也没带回家。当我意识到肿瘤治疗领域存在一些致命的弊端后,我开始尝试用一些纯自然的方法恢复自己的体能,而不是急于用药物围剿自己体内残存的癌细胞。这些方法也许在医生看来什么都不是,至少算不上医学意义上的治疗,却寄托着我生的希望。
令人惊讶的是,我并没有像医生预见的那样迅速走向死亡。事实上,我能感觉到死神离我越来越远。如今已经五年过去了,我仍然活着,而且越来越像个健康人。我甚至有余力去关注癌症治疗领域里的是非成败,结果竟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这些事实完全不符合我们大多数人对于癌症的了解,却能印证我个人的体验。
尽管大多数人都相信只有早期癌症患者才有可能治愈,我却始终期待有一种途径能给所有癌症患者带来希望。
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治疗前景感到很绝望,因为我了解到一些令人沮丧的情况。过去30年,癌症患者的数量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着。“癌症就是绝症”“确诊癌症等于宣判死刑”,已是民众中普遍的看法。专家们不断地警告我们,“癌症成为人类第一位的致死原因”。2012年,全世界死于癌症的人有可能超过1000万。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癌症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还将大幅度增加。
这局面对于我的信心是个相当大的打击。但也就在我最绝望的日子里,我认识的一些美国人不约而同地告诉我,癌症不是绝症,而只是一种慢性病。他们说,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来看待癌症的。
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于是试图考证它是否有根据。结果发现,美国的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被遏制,转而呈现下降趋势。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即医学上所谓“治愈率”,提高到81%。如今美国癌症患者的平均存活时间已经达到11年,并不比一些慢性病患者的更短。换一种方式来设想,癌症患者的感觉,可能真的类似于得了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世界卫生组织才能公开宣布,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预防,三分之一可以根治,三分之一经过治疗可以长期生存。
一些研究机构还进一步证明,癌症患者中有一部分人能够不治而愈。
即便我们对“不治而愈”的观点持有最谨慎的态度,仅仅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也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癌症患者都是有希望的。
我们要么根本就不会患上癌症,要么可以治愈,要么可以长时间地与癌共处。
我第一次知道这些事实的时候,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与我自己对癌症的认识是如此不同,与我们国家的癌症治疗现状也是大相径庭。我似乎看到大洋彼岸出现的一线曙光,然而它距离我们那么遥远,就像在一条又长又黑的隧道尽头的一盏灯烛。
在我们的国家,癌症患者面临的情况相当糟糕。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三年内死去,能够活过五年的只有20%左右(根据不同的报告,我国肿瘤病人的“五年存活率”在10%~30%)。这不仅大大低于美国,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明白癌症治疗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自己的求生机会不敢有更多奢望,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象,有没有可能让我们国家癌症患者的“五年存活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呢?如果能,那么,在那些死去的癌症患者中间,每五人中就会有一人不至于死去。进而设想,如果我们的“五年存活率”达到美国的平均水平,那么每五个死去的人中间,就会有三人活下来。
用已经公布的“世界平均水平”和“美国平均水平”做参照,我可以大致推算出,在我们国家每年死去的大约200万癌症患者中,有30万~100万人本来不至于死去,至少能活得更长些。
可惜他们最终没能做到!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深深地震撼了我,也给我带来困惑。我仔细揣摩这种情形,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癌症患者会更少地存活、更多更快地死去?是我们这些癌症患者讳疾忌医吗?或者是特别舍不得花钱?是我们国家癌症治疗技术特别落后吗?是我们缺少好医生吗?是我们没有特效药吗?是我们独有的中西医结合彻底失败,因而让患者更短命吗?是种族遗传基因让我们中国人特别禁不起癌细胞的折腾吗?
我在困惑中仔细询问身边的病友,也悉心体会自己病情的变化。我无数次地置身于医院的拥挤、混乱和繁忙中,观察病人,观察医生,也观察医院的环境和设施。一些现象很快展现在我面前。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他们每天在同一时间拥进挂着“肿瘤门诊”招牌的那些大楼,带着满脸的焦虑和绝望;我看到那些身着白衣个个拥有一大堆头衔的专家,他们在收取病人几百元的挂号费之后只不过付出几分钟时间;我看到锃光瓦亮的医疗设备摆满楼上楼下,还被告知这都是全世界最先进也最昂贵的;我看到所谓“最新最好的特效药”几乎每周都在问世,还有所谓“中西医结合”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事实上,形形色色的好消息相当多,总是宣布又有了什么伟大的“新发现”,给癌症患者带来“福音”。为了这些“福音”能够降临在自己身上,病人们排着长队往医院的收费窗口里塞钱。他们每年花在治疗上的钱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其中有很多人甚至为此倾家荡产。癌症患者用自己的希望和金钱催生了当今中国最繁荣最赚钱的一个医疗部门,可他们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都在增加,中晚期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在过去30年几乎没有提高。
我的困惑在继续,因为我找不到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国家癌症患者康复的机会更少,死亡的人数更多。
2007年从夏到秋的一段时间,我惊讶地发现我脑瘤的症状减轻了。这一段时间进行的复查表明,颅内病灶正在缓慢地缩小。看来那个迫不及待的手术计划完全没有必要,医生的“死亡预言”也被证明是一个错误。想到当初被医生的话吓得手忙脚乱的样子,我和家人都觉得有点好笑,同时庆幸自己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把脑袋锯开。
这种体验比其他任何尝试都更明显地暴露出一些不寻常的因素:癌症治疗体系有可能存在致命的弊端,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存在致命的偏差。这两个“致命”加在一起,让我们生的希望变得格外渺茫。
不过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是模模糊糊,更因为我对医学的无知而显得不那么可靠。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开始搜集有关癌症治疗的资料,并且把这些信息与癌症患者的高死亡率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有一天,我看到一些资料,在所有死亡的癌症患者中,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治死的,只有三分之一是真正因病而死。有不少人用这一组数字来概括当今中国的情形,包括一些长期致力于癌症治疗的医学专家。这表明它不是圈里人的信口开河,更不是外行们的以讹传讹。
我最初看到这消息时,认为它只是一个大致估计,并非严谨的临床检验统计。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所谓“治死”之说,于是我看到了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一些医学专家相当精确地指出,“用药不当”大范围地存在着。其中一位认定,“目前癌症病人符合规范用药者仅为20%”。另外一位则指出,“有90%以上的癌症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治疗方案”。
这些数字令我震惊,癌症患者中竟有如此多的人不是死于自己的疾病,而是死于自己的恐惧和不正确的治疗。
看起来,我们最大的不幸不在于遭遇癌细胞的侵袭,而在于我们被中国式的癌症观念包围着,同时还接受着中国式的癌症治疗。这种医疗环境正在造就一个悖论:医学越是发达,越是剥夺患者的主动性和判断力,越是造成病人的恐惧和错误。
我们恐惧,是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不了解癌症,不知道癌症其实并非绝症,只不过是一种慢性病。我们不了解自己的机体,很容易过低地估计自己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却过高估计药物的能力,不知道那些所谓“特效药”有可能正是致命的杀手。
我们会犯错误,除了因为我们恐惧,还因为我们过分相信医生,不知道即使是最权威最有经验的医生也会犯错误。事实上,医生不仅会犯专业性的错误,还经常会犯常识性的错误。然而他们最大的错误,是从来不会把自己的错误告诉患者,只一味地对患者讲述自己的成功病例。
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专家说的“三个三分之一”,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说的“三个三分之一”。它们符合我个人的体验,也解释了我对周围那些癌症患者的观察结果。
让我和家人吃惊的是,原来癌症患者求生的玄机如此简单:只要我们不恐惧,不盲从,不走上错误的治疗之路,我们就已经有66%的机会远离死神。即使我们的肿瘤已经到了中晚期,也可以长期与癌共存。
(本文摘自《重生手记》,凌志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一版,定价:35.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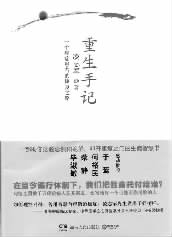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