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正在撰写一部书稿,其主题是关于古代私学与中华文化的传衍。其中一些论见,当时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之约,抽绎整理为《浅析私学与中华文化的传衍》一文,刊载于《华中师大学报》1992年第6期上(后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教育学》1993年第1期全文转载)。在文中,我依据前人的研究和史籍论叙,于孔子所创儒学学术的传衍,特地提到子夏的贡献:“在韩非所说的儒学八派之外,被荀况称作‘贱儒’的子夏,举凡孔子删定的儒家全副学问——‘六经’,其中有五经即由其通过私家讲学传出。如其传《诗》:‘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再如其传衍《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子平,平传于子地,地传于子敢,敢传于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徐彦:《公羊传疏》)”在肯定子夏传授儒家“六经”的功绩和地位的同时,在文中我还写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史记·儒林列传》),鲁国开始失却春秋时期文化中心的地位。‘是时独魏文侯好学’,以孔子弟子子夏为师,起用‘尝学于曾子’的吴起等人,使魏国国力一跃而为三晋之强,并一度成为战国初期的文化中心。”由是进而肯定了子夏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或主流思想的儒家文化的传衍所起的关键作用。
遗憾的是,文章虽然顺利刊发面世,但那部书稿写完第二章后因他故一直搁笔至今。原打算就子夏通过私家讲学传衍儒家学术的内容写成一节(至少一目)的篇幅,以论证或彰显子夏在儒学传衍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这个计划一直未得实现。然而世间诸事皆有缘,此一心愿现由来自子夏故里河南温县的高君培华代我了却,而且他以长达近三十万言的篇幅来考论子夏传衍儒术的历史真实,显然相较我的初衷要全面系统、周密深邃得多。
培华君与卜子有缘,这种缘是一种“地缘”。对此他在本书“绪论”中已作了详细的交待。而我与培华君有缘,缘自同一个生长时代、同一类学研空间,因此可算是一种“天缘”:我与培华君均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惭愧的是我比他年长数岁;在来华中师大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在中国教育史、志研究领域里也算得上是“一方诸侯”。尽管身体不太好,而且身任一个不大不小单位的主要领导,他还是以“五十而学《易》”的学研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来到桂子山上并认真地完成了人生求学最高阶段的学业,正如他在论文“后记”中所誌:“读博三效南征雁”;“老大辛勤读圣贤”。早在考博之前数年间,他就对自己故乡先贤子夏有过一定的研究,所以在攻博期间谈及论文选题时提出研究子夏,由于我有心愿已结,故而一拍即合,当即允准他的选题。后又经过数度商讨,定下以“考论”的形式和文体来探研卜商(子夏),论证他在总结、继承、传衍和发展孔子教育思想方面的历史贡献,借以求证子夏实为以儒学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明史承上启下的一流大师级人物——有如同属人类历史“轴心期”的古希腊、古印度、古巴比伦的大师级人物们一样,子夏不愧为中华文化史和人类文明史上一颗璀灿夺目的星辰。
论题的提出与确定,固然是学术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一步,但如何彰显自己的写作主旨、阐明自己的学术观点、证实自己的研究结论,实属一件大不易之事,尤其对于一个在历史年月上与自己距离十分遥远且无多少能直接用作铁证的史料可寻的历史人物,这种很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的研究更是这样。然而“困难吓不倒英雄汉”,培华君以“攀越书山第九重”的毅力与斗志,依循学界先贤的研究路径,可谓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自己既有的收获上,南来北往,送暑迎寒,钻故纸堆,翻线装书,广泛地搜求传世古籍、出土文献、地方志史和族谱家乘等所有有关卜商的资料,并由中辩讹求实、去伪存真、钩玄提要、缕析条分,较为全面地研究了子夏其人、其事、其学、其行,尤其考论了他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作出了怎样的总结和传承,也为读者乃至后世勾画出“这一个”经作者价值判断后认定为真实的孔门高足卜子夏!
当然,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研究,向来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研究者所掌握的有效资料、所持有的学术观点、所选择的评判标准以及所具备的学研功力等诸般要素的不同,研究对象的最后定像自然也就各有形象。但通过多年与培华君相处,作序者深知他数年来用功之勤和探研之辛,在一个学术浮躁之风盛行,学研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甚至“伪币驱逐真币”的时代,我敢肯定他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极力打造出一枚真币或良币。诚谓世间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论文写定后他又经过近两年的反思、搜求、修改和补充,现在以学术专著的形式面对读者,估计他还有感到不如意的地方,但人生有涯而学研无涯,总得有一个划句号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相信读者诸君读完此书后能认同我这句话:“能成一家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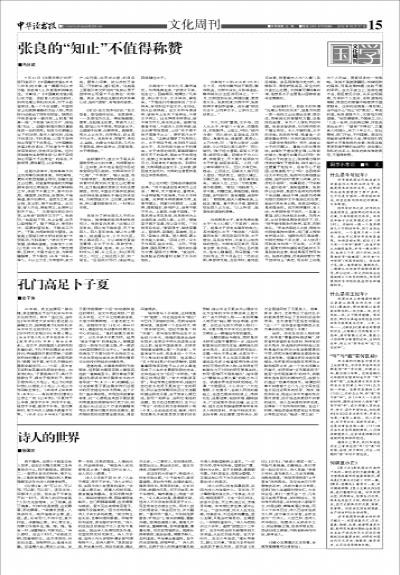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