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审查历史》列入了由我和卢春龙博士主编的“政治文化研究译丛”。这本书并不是政治文化研究的核心著作,更谈不上是政治文化研究的经典,我们为什么把它纳入到这套丛书里呢?
首先,这本书不光是在谈历史教科书问题,更是要探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怎样形成的、是怎样被歪曲的,历史教育和历史记忆对于当代社会起什么作用这样一些问题。由历史教科书引伸到民族历史记忆,再落实到公民教育,这样一个话题,和我们政治学讲的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的形成与传播这些话题是直接相关的,所以它也可以属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范围内。
在西方国家,普遍地把历史课作为公民课的一个内容。公民课里面讲政治、法律、社会、经济、道德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历史。讲历史是为了进行公民教育。在我们国家,历史教育曾服务于意识形态教育,让人们确立唯物史观。后来又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旨。当我们今天要走向民主法治、建设公民社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把历史教育转向公民教育,为公民教育服务。所以,西方人怎么样编写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怎样服务于公民教育,他们对历史教科书的批判性思考,对我们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其次,可能与我个人的兴趣有关。我一直很关注我们国家中学的历史教育。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因为历史教育塑造了我们一代代人的精神世界,有缺陷的历史教育也会误导一代代的年轻人。
我在为《审查历史》写的序言中说:
历史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精神生命的一部分,享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但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遗忘,意味着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扭曲和中断,一个失忆或记忆错乱的民族不可能具有健全的心智和人格。……一个民族只有保存对历史的客观完整的记忆——不仅保持着对历史的敬意与珍重,也保持着对历史的反省与批判,才能从真实的历史中得出真实的教训。选择性的历史、被阉割的历史是对当代人和后人的误导,失忆和伪造的历史则是致命的毒药。
西方有个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历史是置于我们身后的星座。”这意味着,它为我们今天定位,也为我们的未来指航。我们今天对现实问题怎么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历史;我们对未来有怎样一个预想,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脑子里面有一个历史。尤其在中国,像宗教这样的意识形态对多数国人的内心世界的影响是很小的,历史相对来说就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个星座并不是上帝或者造物主安排在自然的星空中,像北斗星、启明星那样忠实地为我们指航,不是的,它是人为设置的。如果人为地把这个星座错置了,它就会误导我们对今天的判断和对未来的构想。
这本书讲的是日本、德国和美国中学的历史教育问题,包括历史教科书问题、教科书的审查制度问题等等。西方人在反思、检讨、诘问,他们的教科书和历史教育对他们的公民教育有什么样不利的影响?对于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健康发展而言,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这几个国家都是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他们关注问题的角度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提出了很多共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的。
本书提到的政府与历史教科书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
第一种是政府直接控制型。例如韩国,从朴正熙时代起,教科书就由国家编写发行,学生都学习同一种历史教科书。
第二种可称为社会自主型。德国和美国就属于此类。官方不直接干预教科书的编写、出版和使用,它属于社会自主的领域,这是一种比较自由的体制。当然,很多社会力量对于教科书的编写和选用都会有一定影响,像家长、教师和图书馆人员,出版商、教会、老兵组织、反战组织,还有少数族裔组织、妇女组织等,都会参与进来,施加他们的影响,也可以说,他们都是事实上的教科书的审查者。在西方这样多元化的社会里,教科书的编写和选择是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最后形成的教科书反映了社会意识水平和分布情况,也往往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第三种是政府有限控制或间接控制型。日本就属于这一模式。政府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有一定的介入,但是这个介入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由地编写教科书,不同的出版公司拿出不同的版本,由文部省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它进行审核,不符合标准的,要求作者修改;符合标准的,由文部省发布一个目录,由各学校、各市教育机构自由选用。
多年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中日间外交纠纷的一个焦点,也为中国公众所关注。一般中国读者主要是从媒体上了解到一些信息。日本教科书的审查制度是怎样的?有一些人为什么要修改历史教科书?他们的动机是什么?效果如何?反对修改历史教科书运动的那一方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在这本书里,美国和日本的学者对这些问题都做了严肃的研究,使我们在思考上述问题时有了更多的可靠的资料。
这本书专门阐述了家永三郎的历史教科书诉讼。那是长达数十年漫长的诉讼过程。这不是家永三郎“一个人的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势力和声势浩大的运动,对文部省的审查权提出质疑和挑战。这样,文部省的审查要求,政府干预教科书的企图,官方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的努力,与民间对它的抵制和批判,双方有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家永三郎诉讼的结果,是文部省仍然保留了审查教科书的权力,但其审查权受到了限制。
由于国内的抗争和国际上的压力,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教科书基本上都会把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慰安妇、冲绳大屠杀这类以前刻意回避或者淡化的问题写进来。也就是在双方力量博弈,天平开始向家永三郎一派倾斜的时候,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比较强的反弹,这就是右翼的修改教科书运动,发起这一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是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人。
在很多国人的观念中,历史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提高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人们会觉得,这是不容置疑的常识。但是,如果要在德国这样讲的话,就是“政治上不正确”了。一个总统或总理之类的政治人物要这么说,可能会引来一片谴责。在日本不存在德国那样的氛围。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出发点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藤冈信胜一派人深深地忧虑当代日本人缺少爱国精神。他认为,这是因为日本长期的自虐史观,让日本人没有了自信心、自豪感。他曾引用了一个数据,来自美国学者英格尔哈特在世界范围内搞的一个价值观的调查。当问到“你愿意为祖国而战吗”这个问题时,在美国和韩国,回答“yes”的分别达到70%和85%,在日本,回答“yes”的只有10%。这类的事情刺激了右翼分子。他们声称,再这样讲历史,把历史都变成民族耻辱的记录,连这10%也保不住了。没有人为自己的祖国感到自豪,没有人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战斗。因此,他们要把中学历史教育纳入到爱国主义教育的轨道。为此他们就要掩盖历史上的罪行。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学校是专门培养日本公民和对其进行社会化的场所,所以不应该传授那些让学生质疑和羞愧于自己的日本身份的知识。历史应该是“光明的历史”,而不是反日本的、自虐和取悦于外国人的历史,它应该是培养国家意识所需的各种传说和故事的集合。
这些人对日本流行的教科书极为不满,于是,他们自己编了一本教科书。本来,民间出现一部这样的教科书算不上大事,毕竟那是个多元社会。问题在于,这部教科书通过了文部省的审查,这就是一个官方行为了。这是我们应该予以谴责和批评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所谓文部省的通过,只是表示它达到了基本的质量标准。同时通过的还有其他多部教科书,右翼的教科书只是若干教科书之一。各个学校和城市有权自由决定选用哪一种。据我看到的材料,选用右翼教科书的学校大概在0.4%到1%。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日本的右翼虽然有所抬头,有一定影响,但在日本的市场还是非常有限的。
本书也谈到韩国历史教科书的情况。当韩国人和日本人联合研究历史教科书以解决相关的分歧时,双方一开始就商定,只研究日本教科书问题,不涉及韩国教科书问题。韩国当年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似乎受害者怎样写历史是可以免责的。但在我看来,尽管发动侵略战争的一方首先负有反省的义务,但受害者一方也需要正视历史。受害的经历并不能成为回避历史的理由。如果受害者不能正视历史,片面地叙述历史,与施害者隐瞒、遗忘历史一样,也会害己害人。我们都清楚,当年的日本和德国就是通过强调、夸大甚至编造受害的历史,煽动起法西斯主义情绪、复仇情绪。受害者通过阉割、伪造历史,完全可以变为施害者。这个历史教训需要我们铭记。
由于历史教育对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和传播至关重要,所以,当年盟军占领日本和德国之后,在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同时,也着手禁止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教育。在日本,盟军司令部就下令停止法西斯主义的历史教育。但是,课本已经发下来了,怎么办?老师只好按盟军的意旨领着同学涂改教科书。告诉同学们说,第一页的第五行的哪几个字涂掉,第二页的第几段涂掉。老师们领着学生涂。所有宣传军国主义的、神话天皇的、编造日本历史神话的内容,都要涂掉,所以当时有一个词就叫“墨涂”。而后,盟军又指令编写体现自由、民主、和平的价值观,尊重历史的教科书。这种对历史教育的改造,对于德日两国在战后成为民主国家、和平力量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历史教育应该是民族主义的,还是超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抑或是在两者之间实现一种协调?是为了服务于塑造现代公民,还是要适应全球竞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如何在培养公民的爱国精神与其保持清醒理性和尊重事实之间达至一种平衡?……《审查历史》表现了西方人在这些问题上的焦虑。我们有没有自己的焦虑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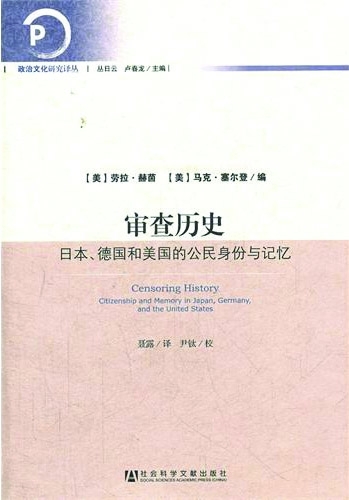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