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根本没有想到要二改拙译《百年孤独》。我以为,我翻译这本经典名著时已经尽力了,何况我还偷闲修改过它一次。我睡大觉,认为我只能做到这样了。不料该书新译出版,引起了一些评论,其中有林一安先生的两篇文章,纵论四个中译本译文的短长。谢谢他把拙译译得不到位的几处敲了几棒子,这一下才把我敲醒了,我因此才下狠心再将拙译好好修改一遍。
为了不拉长拙文篇幅,每谈到这次修改中一个容易出现翻译错误之处,我都仅举一例加以说明,而且将冗长的原文缩短译成中文,仅将可能误译的原文写出再来讨论其译法。
《百年孤独》谈的是百年来发生过了的事情,作者采用的是“那些人那时候在那地方干那些事情”的叙事手法,可是译者却不留心,有时译成“这些人这时候在这地方干这些事情”了。粗粗看去,似乎这么翻译也能看得下去,其实译者并没体会作者用“那”而不用“这”的用心。这种“小小的”错误能一错到底,我现在举小说收尾时拙译译错的一例加以说明:“他(奥雷尼诺·巴比伦)还没来得及念到最后一首诗,就已经明白他再也出不了ese cuarto了。”明明是“那房间”,可我译成“这房间”了。这类错误,我这次统统改了过来。
《百年孤独》里布恩迪亚家族的七代人,人名重复的不少,相互关系和辈分不易分清。作者就曾指出,那家族是个“错综复杂的血统迷宫”。要弄清人物之间的关系,中国读者比使用西班牙语的读者更多一层困难,因为西语中亲属人物和辈分没有汉语规定那么严格,例如tío一词,按情况可译为伯父、叔父、姑父、姨父、舅父或伯爷爷、叔爷爷、姑爷爷、姨爷爷、舅爷爷。正因为如此,我在翻译时曾费力理出一张《布恩迪亚家族家谱表》,按表检测人物之间的关系,但就这样仍不免粗心译出错误译文。例如阿玛兰塔与何塞·阿卡迪奥之间的关系,我原译为“老奶奶抚摸曾孙子”。这次改译时我细想,阿玛兰塔一生没结过婚,怎么能有曾孙子呢,于是改正为“老姑奶奶抚摸侄曾孙子”了。
人物相互关系及其辈分的难理清,莫过于何塞·阿卡迪奥的私生子——全然不知道自己身世的阿卡迪奥临刑前要求转告他女人关于他俩的遗腹子命名的几句话了。现在我按原文简化译出大意:
“告诉我老婆,叫她给女儿取名乌苏拉,随奶奶的名字。生个男的就取名何塞·阿卡迪奥,可不是随伯伯,是随爷爷。”
我原来译为:“……生个男的就取名何塞·阿卡迪奥,可不是随我伯伯,是随我爷爷。”这么翻译看来译得对,因为阿卡迪奥揣想自己是他所不知道的生父和他叔叔的下一辈。
另外有译者包括该书的英译者格雷戈里·拉巴萨译为:“……生个男的就取名何塞·阿卡迪奥,可不是随他伯伯,随他爷爷。”这么翻译看来也译得对,因为阿卡迪奥以为他是他生父和叔叔的弟弟,尽管他这样想就把他自己和他未来的儿子都提升了一辈。
可是,这两种译法都只译对了一半,缺了另一半,因而是译得不完全的、译错了的,只有完全照原文翻译,不自行添加物主代词(这里不是对物而是对人的关系,我觉得似乎应该叫“人前代词”才对),才真正理解并译对了原文,译出了阿卡迪奥不明身世、模棱两可的心境。作家这么设字,真可说是妙绝了。
一个词,往往有多种释义,可是译者不勤翻词典,一句话来了就按自己记忆最深、用得最熟的词义凑合着译出,结果译错。这方面错译的例子,我这次改译时没细心记取,就能从我自己和我的同行的译品中举出好些,足够另写一篇小文章出来。现在仅举小说开头不久就出现的一例来说明这类误译:“Una familia de gitanos来到村旁……”这句话很容易顺手译成:“一家吉卜赛人来到村旁……”。我觉得来了那么些人,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成员,因而译为“一伙吉卜赛人来到村旁……”,但这样译也是错的。因为familia这个词,除我们惯用的“家、家人”的释义外,还是“部落”的同义词“氏族”,以后作者对那批人就用了tribu(部落)一词。因此,这句话应译为“一个氏族的吉卜赛人来到村旁……”才算译得准确。
中国和西方国家语言不同,文法结构不同,应能相互学习。中国文字求简洁,不像西方文字那样枝繁叶茂,一个主语负载不了那么些修饰性词语和拖带那么些宾语。因此,西方文字的译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汉语习俗,将一个长句拆成几句。可是,我看到过我国上过西式学校的乡土作家柳青,在《创业史》里写出来的这样欧化了的主语词组:“鼻梁上架着用棉线连结白铜腿子的老花眼镜,给闺女做鞋的改霞她妈”。作家早已借鉴西方句式,写出这样的文字了,翻译作者就更应该保存原著丰满多彩的原貌,不把原著中的长句强行拆散。这次改译,我在这方面特别留意,把原来拆散了的句子统统恢复原貌。下面,我把原来我拆成了五句话的、既有主语承载众多形容词语又有主语拖带众多宾语的两句话,按照原文译出如下:“高挑瘦削、神情倨傲、总是系着肥大的泡泡纱裙子、带着种一径抗拒着岁月流逝和不愉快回忆的超脱神情的阿玛兰塔,仿佛额头上也留下了表示贞洁的灰十字。其实,她把那灰十字一直带在她的手上,包在她一直连睡觉都不取下来、而且一直由她自己来洗涤和熨烫的黑绷带里。”这么连续说出的两个长句,读起来也还是顺畅,并不觉得累赘嘛。
这次改译,我将每一个译句反回对照原文比较一次,看到译文有不切合原文之处,按原文改正译文。如果对译文仍然感到有欠缺之处,就要参考我罗列案头的黄锦炎、沈国正、陈泉译本,高长荣译本,范晔译本和英译本,把他们译得据我看比我译得到位的地方,像蜜蜂采蜜一般经过消化,或少许更动,或径直移植过来。他们的脑力辛劳有的也沉潜在我的译文里,我感谢他们的译本对我提供的可贵帮助。当然,我也并不迷信人家的译文。我尽管博采众长,把他们的精粹化作我的,可我依然是在做我的翻译,我在自行前行。
这次改译,我注意改正了译错的词句,补上漏译的词句,删除自行增添的词句,把拆散成几个句子的长句重新归拢,对译文不够流畅的句子加以润色。我初改用的是蓝色墨水,二改用的红色。红蓝交错,给我的初译开了个大花脸,改得它遍体鳞伤,有点儿惨不忍睹。我改完每一章都在日记上作下花了多少时日的记录,全书20章共花去325天才改译完毕。这样一段时间足够译一本同样的书了。经过这第二次改译,我认为译文靠近原文一大步,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本新译出来的《百年孤独》了。可是,正因为我将拙译一改二改,我体会到了译事之难。译者在动笔开译一文、一书之前,就应有特别谨慎从事的打算,决不可马虎将就译去。尽管我的这种体会迟了一点,但迟也比没有这种体会更好一些。
这样,初译就一无是处了吗?不,我敝帚自珍,觉得已经成书的译本是一个可供改善的本子,其中有些单词、短语和文句我自觉译得够出彩了。我甚至认为,如果今天拿一本西语文学佳作来让我翻译,我会不能译得那么恰当了。那么些年纪轻轻时活跃在我头脑里的美好词句,一个个、一批批跟我那曾经有过的美好年龄一道飞走了。我想起了宋人晏殊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了。可是,所幸我还没有到糊涂的地步。一个已经译成的本子摆在我的眼前,我还能知道其中文字的得失,我还会细心把它们修改得好一些。这样,我才敢二改拙译《百年孤独》。
译文改出来了,我希望拙译来日能见到西语文学专家和广大读者,得到他们的批评指正。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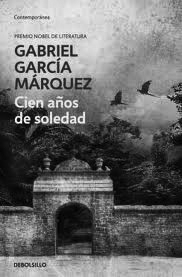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