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
合上《家人们》(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我很想借用黄蓓佳小说结尾的一句话表达阅读的心情:“该找个什么样的安静的地方,来细细地消化这么巨大的喜悦呢?”在她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完成了情感纠葛在物质富饶时代的碰撞。她冷静的笔端,流淌着人生的悲凉与无奈;她的《中国童话》(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那又是一种别样的阅读感受:纯净清澈,恍若泉水潺潺浸润心扉。
“写作是一种源远流长的东西,从生命中抽出来的一根细细的丝,总也抽不尽,甚至不抽也会自动地游出来。如果不将它及时地捺到纸上成为文字,它就要放赖一样地纠缠住我们,裹住我们的手脚,勒住我们的脖子,卡在我们的咽喉处,总之让你不能呼吸不能说话不能行动。”黄蓓佳说。她的生命,正因这写作,因这“折磨”人的“烦恼”,日益丰盈。
儿童文学是冰山上的一角,下面要有庞大的冰块撑着,作品才有份量。
读书报:《中国童话》是受到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影响与启发吗?虽然只有10篇,但这种对本土民间故事的重新发现与重新书写,其意义要远远大于这10篇童话。
黄蓓佳:很多有知识的父母崇尚外国的儿童文学,给孩子读外国的童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读中国童话少,我觉得这是缺陷,作为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哪里,对本民族的文化传承还是要有所了解。我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非常有价值,我希望把这些故事原汁原味地告诉孩子们。写这本《中国童话》之前,我做了很多案头工作,打捞收集了各个民族口头流传的故事。一篇篇看过来,这些故事中有很多相似和重复的东西,因为是口述文学,文字也简单和粗疏,甚至没有人物形象,没有场景描写。这些故事我们小时候曾经读得津津有味,但是现在孩子的阅读口味比我们那时候高得多,简朴的民间文学吸引不了他们的眼球。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把原始的故事重新分类组合,调动了一切文学手段,编写出故事性更丰富、人物更丰满、文字更华美,同时又是原汁原味的童话作品。
读书报: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心态?您希望达到怎样的目标?
黄蓓佳:这事看着容易,做起来还是费了功夫,我中间甚至都后悔当初动这个念头。把粗糙的口头传说打造成精致的文学作品,其中要丰富很多细节,我在人物对话、文字描写上下了很大功夫,希望能够体现民族的童话之美,又能在阅读时体现中国文字之美,给孩子双重的享受。我自认为尽到了我的努力。过去我写作品基本都是一稿,这些作品我每稿都磨了几遍。江苏少儿社为弘扬民族文化,跟南京艺术学院的插图系师生们合作,为这本书配上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图画。小孩子对图画有天生的亲近感,图画能帮助小孩子建立和外部世界的联系,尤其我写的是各个民族的故事,借助插图,能详细地表现不同民族的古老的生活细节,有一种情景再现的意思。
读书报:童年的经历对作家的影响很大,从《没有名字的身体》到《所有的》,再到《家人们》,虽然前者私密的东西多一些,人生的感慨多一些,后者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关注更多一些,格局更大一些——您好像不遗余力地发掘着来自故乡的人和事,能谈谈故乡对您的影响吗?
黄蓓佳:年轻的时候,眼睛总是往前看,我在40岁之前写故乡的作品非常少,总在写自己生活的大城市,写城市知识分子;40岁以后开始怀旧,对从前的回忆铭心刻骨。我不是有意识地写故乡,而是自然而然,到了年龄目光就往回看了。人的一生,印象最深的还是童年成长。文学作品要有岁月的沉淀,写当代的作品,有时效性和针对性,但是文学品质不一定最好。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站得住的。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回望历史,更有岁月的绵长味道,像茶一样越醇越香。写作要有思考的过程,这个思考需要岁月来延展。
读书报:作品出版后,您会关注外界的评论吗?手头上正创作什么作品?
黄蓓佳: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坐在家里写作,我的全部快乐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不大关心成书后带来什么效果,也不大关心评论如何,得奖与否。我是比较内向也比较矜持的人,不太善于跟外界打交道。当然,如果得奖,如果好评如潮,如果读者厚爱,我会更加开心。
我不喜欢重复自己,那不是技术活儿,没有意思。我希望每一部新作品都跟前一部不一样。目前刚写完一部“重口味”的儿童文学《鬼眼男孩》,在题材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思想深度超出儿童文学的范畴,写了失败的人生,写了谋杀和死亡,写了社会边缘地带的边缘生活,这是以往儿童文学尚未涉足过的话题。我想试试儿童文学在关注社会现实方面能往前走多远,读者能接受到什么程度。这一次写作有点风险,但是我准备承受。
读书报:如何评价中国的儿童文学?
黄蓓佳:我读过的儿童文学不多,没有资格做这个比较。作品与儿童文学作家自身的修养,以及对社会、对人生方方面面的认知度有很大关系。虽然写的是轻浅的儿童文学,写作背后还是要有很大的文化储备。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下面有庞大的冰座支撑着,这样的作品才有份量。
没有童年时候的阅读,就不会有后来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也许黄蓓佳和周围的同龄人一样安安稳稳当上街道工人,平凡度过一生。
读书报:童年的阅读对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您的阅读是怎样的情况?最初的文学滋养来自哪里?
黄蓓佳:一是来自阅读,虽然那个时候书特别少,得到书的机会少,可读的书也少,但是阅读很有效率。60年代没有儿童文学的概念,因为父母是中学老师,我读小学的时候把中学的教科书通通读了,手上能够找到的书,包括历史、地理甚至卫生知识我都读。那个时候非常渴望阅读,实在找不到书,就从废品摊上找到小纸片反复读,没事的时候上街去看大字报,也不知道批斗谁,看到字心里就很开心。二是来自外婆的影响,小时候我听外婆的童话和地方戏曲长大,受益很多。
读书报: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黄蓓佳:高中毕业后去插队,我所去的地方就是本地农场,在长江下游一个江心小岛上当农业工人,很艰苦,但是比起边远的地方来还算幸运。插队的时候我开始写东西,目的非常单纯,就是希望通过编写戏曲歌词、写点材料调到广播站或通讯报道组,把自己从农村拯救出来。
读书报:文革后恢复高考,您是在什么情况下考上的北大,当时的文学氛围对您的创作是否有很大影响?
黄蓓佳: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少年时代在学校里特别抬不起头,我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很自卑。我特别盼望考试,因为考试能得到好成绩,老师和同学会另眼看待,能赢得他们的尊敬。第一年恢复高考,每天在农场劳动,没有复习资料,也没有时间,考什么题目、有多大难度,大家心里完全没底,谈不上有多少准备。我当时特别想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那个时候很讲究政治审查,报新闻系,对政治上考察很严,报北大中文系,我又缺乏自信,因此填的最高志愿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恢复高考第一年招生,北京大学有优先选择权,录取了全国各地高考成绩好的学生,所以我们班好几个没报中文系的同学也都被录取到北大中文系了,我是其中之一。我的高考作文《苦战》后来发表在好几家报刊上,其中的《山西青年》杂志给我寄来了我生平第一笔稿费。之前在文革中发表小说散文,是没有稿费可拿的。稿费七块钱,我买了一本新华字典,一个漂亮的文具盒。
读书报:听说您当时在北大读书,《少年文艺》的编辑不断地约稿,成为您写作的动力。那时候编辑和作者接触,甚至介入创作,和现在大不一样吧?
黄蓓佳:从前编辑修改作品,改得密密麻麻,甚至重新写一遍。当然未必都是好事,但是说明那时的编辑有奉献精神,无私地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无偿地为作者做嫁衣,现在也有一些编辑像朋友、像亲人,只是在这方面不如以前,至多是改改错别字。
那时的人和人之间相处也非常纯朴,江苏《少年文艺》的一个老编辑顾宪谟,非常喜欢我的儿童文学作品。我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大概每个星期都给我写信鼓励我,从生活到写作上处处都非常关心我。他在南京工作,我在北京读书,我老家在小县城,每年寒假回家,我要在南京转车,车票不好买,他还会帮我买票,买不到就帮我找招待所住一晚。1980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拿到800多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他还写信交待我,不要乱花,告诉我要存着,结婚生孩子用得上。像父亲一样。我那时非常感动。
很难用成人文学或儿童文学作家来界定黄蓓佳,也许这样的概括本身就不够科学。
读书报:写作四十年,回过头来看,您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黄蓓佳:去北大之前是懵懂的阶段,有点稀里糊涂,包括创作上的准备完全不够,不懂得写作,完全模仿,当时还模仿过浩然。他是用北方语言创作,我是南方人,写小说居然也跟着他用“俺”。父亲看到我写这个字觉得很奇怪,还笑话过我。那种情况下居然也发了七八篇小说,在省里小有名气。可能我文字的青涩也有让人动心的地方吧。
1978年初进入北京大学,改革开放同时开始,新时代来临。在北大,我大量接触到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对过去的创作有了彻底反思和否定,但是却不知道新文学道路怎么走,很徬徨。也多次下河试水,但老是走不通。这时候开始转向儿童文学,一下子找到了感觉。那时候全国性刊物很少,读者数量又极大,作品发表后传播量很广泛,编辑欣赏,读者也喜欢,所以我现在有大量读者是四十多岁的人,他们碰到我总是说,小时候是读我的作品长大的。于是我一半时间写儿童文学,一半时间写成人文学。我一开始起步写的就是成人文学,我最喜欢的还是写成人文学,总觉得写儿童文学不足以表达人生的感慨,毕竟是给孩子看的,受很多局限。
读书报:您的成人文学,关注知识分子比较多。后来又如何转向儿童文学?
黄蓓佳:从80年代回到成人文学,写了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惆怅、迷惘、失意,现在想起来,很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是青春期的反映。但是那些作品得到了很多同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呼应,尤其是年轻人比较喜欢我的小说,因为作品和他们的思想同步,比较浪漫、华美、小资。但是也有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自我,太狭窄,在空中飘着。直到80年代末,我的整个思想有很大的转变。作品一下子从飘渺浪漫的风格变得比较现实,有一些悲凉。在90年代初,我所有的中篇、短篇都是死亡的结局。我自己的生活,家庭生活和事业都比较顺利,为什么作品中屡屡出现死亡结局?是社会观、人生观不自觉的反映。
1996年的时候,女儿小升初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有半年时间,我陪伴孩子应付考试,对教育状况和孩子成长的环境有很多感慨,也经常和同事聊孩子,他们都知道我写过儿童文学,怂恿我不如再写一部。我很快写了长篇小说《我要做好孩子》。也是无心插柳,只是想写写自己的感觉,没想到《我要做好孩子》一下子走红,不光在当年就得了很多大奖,家长、小孩、老师也都喜欢这部作品,15年过去了,这部作品仍然被各地列为学校阅读课的必读书目,发行数量早已超过百万。作家写作需要读者的呼应,如果没有呼应,也许我写完这一本,又回到成人文学的领域去了。可是就因为读者喜欢,加上出版社接二连三地约稿,重新勾起了我的儿童文学瘾,此后这些年的创作态势,基本是成人长篇和儿童长篇交叉着写。
读书报:在儿童文学或成人文学创作中间,您的心态有怎样的变化?在两种心态中,您自己获得了什么?
黄蓓佳: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儿童文学是简单和纯粹的,写作时好像自己重新变回了孩子,回到孩子们中,能嗅到孩子身上的汗味,感觉非常美妙;写成人文学则是痛快淋漓,完全释放自己,无所顾忌地表达。儿童文学是写给孩子看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考虑孩子的接受程度,我能给他们什么,都要思考,写起来不比成人文学轻巧或简单。很多人认为儿童文学很小儿科,实际上很多方面花的心思更大,因为真正让孩子喜欢不容易,他们有自己的阅读口味和审美情趣。
读书报:儿童文学的创作尤其需要不断从孩子们中间获取新的信息,和孩子保持密切联系是创作的必需吧?
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今天我是升旗手》都和孩子关系密切,我从女儿身上观察到很多。后来我的作品回到我的童年,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过去和现在,虽然时代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但是我们的所想、所爱和所恨基本都一样,因为人类的灵魂没有太大改变。而且我觉得,我写自己童年的作品他们更有兴趣探究,他们也想知道父辈的童年。
读书报:那么您认为什么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黄蓓佳: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大人和孩子都应该读得津津有味。如果一本书只是小孩子喜欢,大人读不下去,我不认为是优秀的,它可能过于轻浅喧闹,而缺失了文字背后的有力量的东西。
本报记者 舒晋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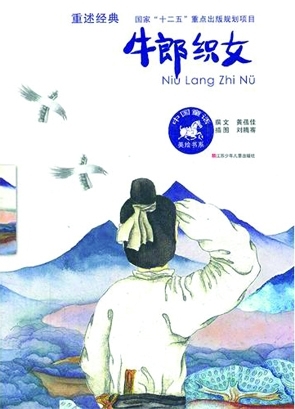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