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尔是一位来自于三晋大地的文学前辈。他的新作《路上的春天》分四部分,大略记载了他慎独所想、旅行所见、读书所得、酬唱所记,这似乎便是古来华夏文人的“例行公事”。可是,就是这“例行公事”,也有陶靖节的《读〈山海经〉》,杜子美的《赠卫八处士》这般璀璨名篇。因此,这类文字往往最不值得小觑。事实也确乎如此,这四组文字从四个侧面展示了作者内心的真诚一面,却又还原了他所经历时代的某种不移的真实。
读聂尔的文字,我会想到我的父母,二老皆是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生,一样就读于中文系,出生时家中清寒,但房中物什中,半面墙的书倒是占了很大地方。只是父母对于文字和思想的灼热似乎比不上这位作者,才气和理想也略逊,随后便“泯然众人”,未坚持笔耕。聂尔老师不同,似乎他在苦涩的生活中仍然记得把时间和情绪记下来,这使得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父辈当年的冷热酸甜和沧桑时代中的物事变化。
但是,说过去,记时代,这不是常有的事情么?瘸了的老兵对拿着玩具枪的孩子说:“想当年,老子打日本鬼子……”,蜷在地下道的乞丐流着哈喇子,发着梦:“小时候我家有十亩地,烤乳猪吃也吃不完……”,这般的自得和自卑混在一起,所记下的东西便毫无意思。聂尔的特点在于,他没有自得和自卑,只有困顿和自尊,正是这种清澈但谨慎的伦理立场,使得他的文字不同凡响。
在第一辑“诗意盎然”中,我读到了《洞头村对话》这样一篇文字,是写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作者“我”,在一个生态观光村与一个有着同样疾患的村民对话。这段对话是理解作者写作想法的一把钥匙,“我”对于“病友”有着一种亲切感,但是这种亲切感立刻遭到了自己的嫌恶。这和“村里人把我视为群体的存在有关,我的痛似也能烙印到他们心里,而城里人视我为一个单独的人。”但是,“我”却表达了“群体是一个虚幻之物”的看法。在这里,“城市”和“乡村”、“个体”和“群体”的张力撕扯了写作者,而作者最终选择了“个体”。但是,这并不等于作者选择了“城市”,因为,“城市”仍然是群体所在的场所,只是这一群人不再是自命为同类的天然共同体,而是一群互相索取个体利益的人所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无根的挣扎决定了作者写作时的情感态度:仍然保留对他人的悲悯和同情,却因此走向了对他人的怀疑和疏离。
这尤其体现在第二辑“回眸一笑”和第三辑“轻的叙述”中,这两辑中最为吸引我的文字是作者对女儿的描述和对师友的回忆。舐犊情深,似乎每个散文作家都会写到孩子,但是,聂尔的笔触却有着特殊之处——并不着眼在对女儿感情的描述,而是尽力刻画女儿与自己相似与不相似之处,自己对女儿疏离和接近的矛盾。一方面,女儿是另一个自己,她有着和自己一样“扎根大地”的天性和乐观的性情,而女儿对宿命淡然一笑的乐观态度,又与经历风霜,有着悲观想法的自己产生差异。当他对女儿跑去北京找工作,与男朋友相濡以沫的感情加以欣悦的赞美时,却直接体认了离家后女儿面对人群的疏离感和痛苦。在回忆大学师友的篇章中,这种矛盾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写宋谋瑒老师时,他着力刻画了宋老师早年被打成右派,而在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却“落伍”的辛酸经历。
这也许是聂尔最为可贵的真诚所在。可以看出,聂尔非常熟悉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方式,在书中,他不仅记下了对普鲁斯特、海明威这些伟大的现代派作家的所思所感,而且在《三短章》、《情人》等这些隽永的短篇文字中,纯熟地实践了他的阅读所得。但是,也许最萦绕他心间的仍然是托尔斯泰式的全盘托出,这使得他远离了当代很多技法炫目但毫无诚意的文学创作。但是,这种真诚和自我却是粗粝而小心翼翼的,因为长期被尘网所拖拽,这种劳碌限制了他对纯文学的完全拥护,也让他的真诚不至于归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荒谬。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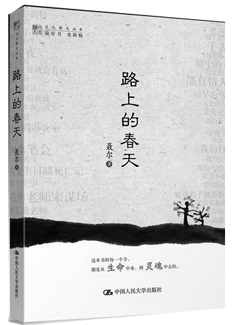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