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称:“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斗转星移,百余年弹指一挥之间,中华民族已于“极销沉沦丧”之境,再度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当初迫于西方殖民主义之威,被迫取文化守势而打出的“国学”旗号,随着国势的增强,开始呈现“出击”之势,一时世界纷纷建起“孔子学院”,讲国学成了大时髦。然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初陈寅恪氏所挽王国维之词,竟然成了谶语。历经百余年“西潮”的冲涤,千年一脉传承下来的文化,“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以至于今日,原固有学术文化的核心知识体系及观念,除了“封建糟粕”的负面意义外,已鲜有人能不误读地洞悉其“义”,晓畅其“谊”了。传统学术文化的语言“能指”(signifiant),因失去其原文化的语境依托,与其“所指”(signifie)早已渐行疏离,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关联,而不得不依赖于“文化的翻译”。文化传承面临的尴尬,使得近代那些“并识西学西理西俗西政,能为融合古今,折衷中外之精言名论”的学人著述,(吴宓称述柳诒徴与梁启超语,见氏著《空轩诗话》)很自然地成为我们进入传统经史之学的津梁。其中以史学言,柳诒徴的《国史要义》,与近世言史学的其他著作比较,既不似张尔田《史微》的迂旧,又不像何炳松、李大钊、杨鸿烈等专以西法论者与传统史学的隔膜,庶几可以视我们走向传统史学之“澄明”的津梁。
柳诒徵,字翼谋,亦字希兆,号知非,晚号劬堂,江苏省丹徒县(今属镇江市)人。生于清光绪五年十二月廿五日(公元1880年2月5日),卒之日是1956年2月3日,一生历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与陈寅恪同为民国时兼有中央研究院院士和教育部部聘教授双重荣誉的两名历史学者。其代表作有“一史一论”。“一史”,乃《中国文化史》;“一论”,即《国史要义》。
《国史要义》的写作,据柳诒徵长孙柳曾符讲,乃缘于抗战内迁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的讲授。其时正是抗倭最艰苦的相持阶段1942年。此时的柳诒徵,不仅学术臻备成熟,且值民族存亡之际,于民族文化前途的忧患与思虑,较之先时也越愈地深沉。被誉为“命世奇作”的《国史要义》,正是因为集合了柳诒徵的学术之醇与思想之厚,而有“先生文史学之晚年定论”的评价。(苏渊雷:《柳诒徵史学论文集序》)
柳诒徵所生之世,恰值中国千年未有的钜劫奇变,其危不独国家将亡,其绵延承续几千年的文化,亦不无泯灭之虞。当其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其痛苦之巨,已非今人所能想象。文化的自卑、沮丧与焦虑,交织着对国家政治前途的焦虑,在当时渐渐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情结在全社会漫漶,随之而来的则是新文化运动一些激进者自遣式的文化批判。“盖晚清以来,积腐爆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柳诒徵《中国文化史》1947年再版《弁言》的这些论述,要亦反映近代以来,内外事势压迫之下,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存续进退的曲折艰难,与吾国人的心态。当其时,如何认识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一时成为知识界争论的焦点。
毫无疑问,柳诒徵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不仅著述等身,且多是筚路蓝缕、堪传于世的巨作。然柳诒徵在新史学、新文化的发展史中,扮演的却不是一般所认同的“革命”角色,而是后人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重镇。柳诒徵认为,幅员如此广袤,融合民族如此众多,历史如此悠久之并世无俦的中华民族,其文化绝不可能虚无价值,而必有一伟大的文化力量蕴寓其中。因此,只有理解柳诒徵先生对中国文化的坚定信念、续统意识,以及护持、复兴民族文化的担当精神,才能理解柳诒徵撰述《国史要义》背后支撑的文化理念。
《国史要义》,顾名思义,就是对中国史学基本要旨思想的阐述。但柳诒徵这里所谓的“国史”,是指中国传统意义的史学,而不是现代意义的、按照西方学科模式建立起来的史学。那是“新史学”。中国的新史学,是以对传统史学的批判揭开帷幕的。清光绪二十八年,即公历1902年,号称“学界陈涉”的梁启超,继上一年《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后,于《新民丛报》再发长文《新史学》,高高竖起“史界革命”大纛,截然划开与所谓旧史学的界限。犹伐旧史学的檄文,《新史学》痛批旧史“四弊”、“二病”等沉疴顽疾。以梁氏之影响,《新史学》发表后,一时趋新者无不目之旧史学如敝屣,欲抛弃而后快。入民国十年,梁氏又有《历史研究法》问世,其论虽对旧史的批判已有缓和,但从根本上,该著仍以为中国只有史料没有史学,应该以西方史学为绳矩建立新的史学。那么,几千年文明的中国文化中究竟有没有可光大、有价值的史学呢?这也正是《国史要义》所要揭橥的问题。
《国史要义》凡十论,依序为《史原第一》、《史权第二》、《史统第三》。《史联第四》、《史德第五》、《史识第六》、《史义第七》、《史例第八》、《史术第九》、《史化第十》。以正面举证论证的方式,有针对性地批驳梁启超辈新史学论者对中国史学的曲解,申述中国史学以及中国文化的特有价值。
新文化学者专以西法绳量中国史学的取径不同,《国史要义》一本于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内在理路而“旁览域外”参校论衡。然需要指出的是,《国史要义》所论之“史”,虽说仍是基于传统经史子集的知识框架,但与传统以经为纲的知识构成观已有不同,即其史学已取替了经学,占有统摄整个知识世界的位置,而归旨于“儒学即史学”。即在其知识观念中,史学与儒学是二而一,一而二,其畴皆关乎政治,其旨俱关乎人伦教化,其要则归之于经世致用。又因儒学的核心为礼,故而《国史要义》“言史一本于礼”。
以礼释史是《国史要义》最重要的特点。这一点,柳氏的同侪好友熊十力早已指出。因柳诒徵既以儒学为史学,那么作为儒学核心的礼也就自然地成了他所谓“史”的核心。于是,理解儒家的礼,自然也就成了理解《国史要义》的钥匙。
关于礼与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这样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定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按柏拉图的idea一般翻译为“相”或“形相”,是和可感得感性世界相对的、从个别和特殊中归纳出的可知的普遍者,亦是一切人事中普遍追求的“至善”。而儒家所倡之礼,亦源自中国古代哲人对于整个经验世界普遍秩序的理解形成的观念,是使社会杜绝人与人之争,使社会和谐有序运转的“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尽管礼的应有之义在后世不断为专制君主所歪曲,但是其作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仍一直是士大夫明知不可为而为的理想追求。
惟礼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所以柳诒徴认为一部中国的文化史,亦是礼之不断展开的历史,而礼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国史学的核心——从史的起源上,“礼由史掌,而史出于礼”;从内容上,“礼者,吾国数千年全史之核心”;从编纂上,礼“为史法、史例所出”,为“史联”所贯;从道义上,礼为正统所系;而史之识在识礼,史之用亦在彰礼,在教化,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以今天的观点看,尽管《国史要义》一些观点可能不无商榷之处,但是其对中国文化温情的敬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肯定,以及坚持依循中国文化、中国史学自身的内在理路,而非以“他者”立场,揭橥中国史学价值的努力,仍值得我们十二分地肯定。20世纪后期兴起的后殖民主义,其理论所阐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构建构在西方殖民霸权之上的、对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话语暴力,解构其所建构的不平等话语上的权力-知识体系,发掘为西方文化霸权遮蔽的民族自身文化的价值。事实上,若仅就史学而言,经过分析哲学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洗礼,人们已经在质疑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标榜“客观”性和“科学”性的现代史学的局限。
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指出,任何文化都存在着譬如语言、价值和知觉框架等基本代码。这些基本代码不仅确定该文化经验的秩序,还建构了该秩序所存在的阐释,构成了该文化“对所有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加以限定的认识型”。也正是这“知识型”,划出了不同文化的界限,决定了该文化所属之知识和思想世界的特殊性。
“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哪讨桂花油!”中国史学本中国文化所自出,从史学的观念、史学的思维方式,到史学的方法和表述形式,皆表现出既不同于西方古典史学,也不同于学科体系下的西方现代史学。因此,如果以近代西方“科学”史学观来观照中国史学必然凿枘,从而显出二者不同“认识型”构成的各自的思想界限。《国史要义》竭力揭示中国史学特异性的努力,其价值也恰恰在这里彰显。
柳诒徵所生也早,其知识直接生成于还未发生断裂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他的知识和思想世界中,尚未构成对传统文化真实的遮蔽,这就使他能够相对准确地传递传统知识与思想的信息。但是另一方面,此时西方文化挟着坚船利炮已开始涌入,即使是出于民族前途的忧患,也使他不得不正视这些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于是,这样一个文化的“他者”,便很自然地,甚至可能是不自觉地被叠加到柳诒徵对中国史学要义的思考和论述当中,构成一个文化的比较视域。而这种文化格局,恰恰是我们今天所不具备的。也许我们对西方文化具有较之柳诒徵更多的了解,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文化断裂与西方知识、思想体系的遮蔽,已经使我们难于触摸到按其自身规律运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真实”。《国史要义》在此情况下,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揭开“现代化”(或西化)的遮蔽,走进传统史学,走向思想理解之澄明的津梁或密钥。当然,在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纠缠,或是在现代的学科格局中,怎样完成传统史学的创造性转换,想来也会伴着我们的思考出现于面前,因为毕竟2000多年来的“纲纪之说”早已失去了“所依凭”的“社会经济之制度”。这可能也是我们在阅读《国史要义》时有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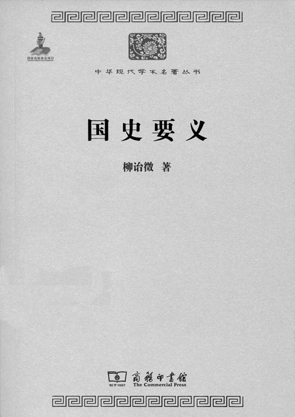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