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新义》的作者何炳松是我国最早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学者之一。20世纪初叶,他率先引进美国史学家鲁滨孙的“新史学”,主张扩大历史研究范围,倡导利用各种新科学成果对历史进行综合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此前,中西文化交流往往经过日本中介,传入中国的西籍不少是由日文转译。这些译著虽然对了解西方起过积极作用,但辗转翻译,难免有失真之处。20年代前后,大批欧美留学生的回国,使大量西方著述得以从原文译介,从而产生了由我国学者自己编撰的一大批有关论著,《通史新义》就是其中之一。本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收入《大学丛书》。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述社会史料研究法,下编论述社会史研究法。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史料考订、史书编撰等方面的表述之详尽和绵密,即使在今天的同类书籍中亦不多见。
该书《自序》十分重要。它有条不紊地讲述了著作目的,中心议题,中西史学之长短,实际上是一篇逻辑严密、思路明晰、行文畅达的高质量专业论文。相对正文因专业缘故而略显艰涩的文字,《自序》更容易理解,对非专业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
《自序》主要讲怎样编撰新式通史,洋洋万言的论述均围绕通史要义展开,对正文的其他部分反而较少涉及,这似乎有违序言必须照应著作全部内容的通常做法。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只要仔细体悟,就会发现这完全符合作者撰写此书的主旨。因为尽管作者十分重视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但根本目的在于借以改造中国史学,编撰出一部符合新史学观点的中国通史。本书丰富的内容和严密的论证,都是为编撰一部完美通史服务的。作者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序》等论著中曾多次提出下述观点:“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这可能也是该书以《通史新义》为名的原因。
作者认为,我国虽不缺乏通史,但却没有一部符合新史学标准的通史,故编撰新通史是亟待完成之事。因此,书中对编撰新式通史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作者首先从我国古代史学遗产入手,充分肯定了章学诚等人在分清材料和著作(即记注和撰述)之畛域,明确其在通史义例等方面的贡献;同时,也批评章氏对通史编撰并无切实之方法的不足,认为西洋史家能够补其缺憾。作者对如何利用西方新方法,以及这些方法各自的缺点作了详细论述。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说的新通史与我国旧式通史的主要不同在于,前者是用综合方法写成的整体史,即不但纵通,更要横通,以反映历史的整体性,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体现历史之“浑仑”;而后者则是以时间连续为特征的纵通性史著。
对通史的重视,自然会涉及史学本身发展过程的研究。何炳松是继梁启超之后第二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并付诸行动的学者。本书下编开头两篇《中国史学之发展》、《西洋史学之发展》专讲中外史学的演变,实为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发展简史。他重点分析、比较了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独特贡献,总结了他们在史著义例、体裁等方面的建树;还根据中国史学自身的特点,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旧式通史因旨在供统治者资鉴,仅关注政治,已经完全不符合时代需要。通过中西史学的多方面对比,作者厘清了通史与专史,以及各种史料之间的关系。指出,专史不足以使人了解社会的演化及整体性,只有通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通史是“一切专史之连锁”,其所展现的事实是“专史中事实之配景”,并明确了专史家与通史家的不同职责。以上所述,论证了新通史撰写的必要性,为编纂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史坛主流之所以重视断代史和专史,与前者明了一代史事,后者畛域清晰,容易成功,而通史则易重复有关。但是,断代史和专史显然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这是它们最大的不足。何炳松极力倡导通史,体现了其独到的史识。
作者认为,通史家和专史家分工合作,是撰写理想通史的最佳方式。这个观点还见于其多种论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并曾付诸实施。据郑振铎回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何炳松拟定过一个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全书分作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请国内史学家分头完成。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郑氏回忆有误,实际出版十余本),就因“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寇炸毁,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上述已完成的著作都属于专史,是撰写通史的前期工作,于此可见其规划的通史撰述规模之宏大、组织之周密。
由于史学研究必须依赖史料,该书对考订史料的目的、方法、步骤,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作者指出,历史是过去之事,不可以直接观察,所以只能从观察史料入手,再推理出原貌。作为过去事实的一种遗迹,史料有原始和孳生之分。这些史料都可能因各种原因失真,而人们由于相信书籍、政府和团体,养成了轻信史料的习惯,所以史料考订就尤为必要。为了辨明真伪,就要考察撰者心术,查明史料来源——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考证和外考证。考订有三个步骤,即诠释之考订,可决定史料意义;诚伪之考订,可决定撰人所述诚伪;正确之考订,可决定撰人是否自欺,观察是否无误。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三种考订功夫往往同时使用。
作者指出,经过考订史料可以得到史实,但这些史实往往是杂乱无章的琐事,要使用这些史实,需要先行分类,然后编成史料书,再汇编成类纂,最后由通史名家进行“编比”,即据以撰写成专著。编比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同一时间各地事实联成一气”,这是并时事实的编比,意在描述社会之浑仑;另一种是将各时代事实联成一气,这是连续事实的编比,意在研究一个社会之演化。作者特别指出,所谓演化,并不仅仅是变化,而是“一种专向一方未尝间断之变动,实则指今日情状之渐异于古者”,意即进化。作者认为,理想的史著应该既能展示社会整体状况,又能反映它的发展情况。
作者还详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史研究法。由于社会科学包括统计学、经济生活科学、经济原理及计划史,所以除了直接观察外,还必须追溯过去,这就要依赖史料。而所利用的史料只有文字材料,它们属于过去之历史,要通过间接方法去研究,故必须使用历史研究法,所以社会现象研究往往就是历史研究。由于社会史事实比其他各种历史事实更难获得,因此易犯“通概”即以偏概全的错误,所以必须使用综合研究法。作者指出,算学法、生物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逻辑学等方法都有裨研究,但均不足以说明全貌,因此不能单独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因为“社会中决无所谓特殊经济的、宗教的、科学的或政治的之事实,各种人类与各种习惯常在互相牵制之中”,它们呈现一种“联带性”关系,所以只有综合地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成果,尤其是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全面考察,才能得到正确认识。
在该书《自序》中,作者明确表示,此书理论采自法国史学家塞诺波(今译瑟诺博斯)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自己仅做了“疏通证明”的工作,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不过,本书虽以西方理论为依据,却做到了尽量与我国传统史学理论相结合,所举例子亦多为我国史事,可见作者融合中西史学之努力。
本书也存在某些不足。由于拘泥原著,加之专业缘故,行文较生涩,内容亦有重复之处。本书对历史是否一门科学,是否存在因果律的矛盾态度,反映了作者对有关学术问题的曲折探索,似不必苛求;至于书中的一些专业词汇如“浑仑”、“编比”、“通概”等不易理解,则反映了当时的语境。作者还有一本同样讲述史学理论的著作《历史研究法》,相对易读,如能参阅,当可获相得益彰之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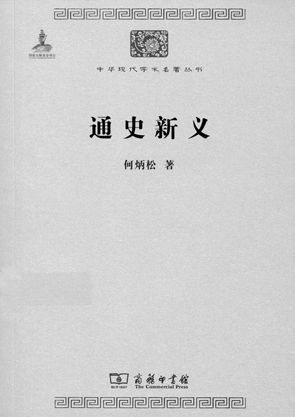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