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是自始至终贯穿费孝通学术生命的一个关键词。何谓“士绅”?费孝通给出了一个外延很广的定义: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属,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他们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一定地位、发挥一定功能的一个阶层。士绅是费孝通在20世纪30到40年代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费孝通从最初的乡土工业的讨论引出士绅问题,探讨士绅以及近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所承担的责任与使命。到了晚年,费老重回“士绅”这个原点,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将士绅作为中国文化的几个基础之一。
《中国士绅》写成于《江村经济》(1939)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1945)这两份田野报告之后,是费孝通在一定的田野经验基础上,对士绅和城乡经济关系这两个问题所作的专题性研究,较为完整地呈现了费老早年对士绅问题的系统思考。
通读全书,会发现在费孝通的心目中存在着属于两个世界的、具有不同意义的“士绅”概念。一个是作为研究对象的“士绅”,即对士绅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另一个是作为理想信念的“士绅”,即费孝通一直秉承的士绅的精神和道统。
《中国士绅》一书的前四章可为一部分,主要是历史研究,其脉络可概括为如下几点:(1)从士绅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入手,讨论了士绅阶层的政治意识:士绅秉承道统,或与政统对抗、或向政统屈服,最高理想则是寻找道统与政统的真正结合——王道。(2)士绅依靠由知识的特权构建的道统影响政统、规范社会,而不是依靠技术。(3)士绅除了依靠道统发挥社会规范的作用之外,还在实务层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士绅阶层作为管事的地方自治团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权力体系“双轨制”中由下自上的一轨。
书中后三章可为另一部分,费孝通从历史回到现实,其脉络可概括为:(1)通过分析村、镇、城市与通商口岸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西方大机器生产带来的工业品倾销大大挤占了乡村手工业品的市场;另一方面,城市中以乡村地租和利息为生的食利阶层为消费西方工业品而加速对乡村的剥削,乡村手工业的迅速衰退导致了农村“不饥不寒”的生存底线崩溃。以士绅为代表的乡村食利阶层殊不知正是乡村手工业决定了基本地租,也决定了自己的未来,他们对西方工业品的大肆消费和对乡村的大肆剥削在埋葬乡村手工业的同时,也埋葬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2)乡村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同时,人才资源上也遭受“社会侵蚀”: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不能促进中国实现现代化,反而使小康农家的子弟流入城市,但城市又不能为他们提供有价值的就业。在费孝通的笔下,这些原本应当回乡扮演士绅角色的读书人成了“寄生阶层”,这个阶层的产生与西方工业文明对中国的冲击有密切联系。西方文明带给中国的只是物质享受和满足的渴望,而使其变得有意义的物质基础——工业主义并没有真正引进,这种基础的缺乏制造了一个表面上生活在西方文化中、但又没有东西方传统基础的特殊阶层。(3)费孝通为此开出的药方是重建乡村工业,在谈到如何让新型士绅回到乡村,为乡村工业贡献力量时,他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回到乡土伦理层面,将答案指向人与土地的“象征性亲缘关系”。通过强调对土地的依恋来吸引士绅回乡发展乡土工业,他有意识地将乡土伦理和乡村工业相结合,触及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讨论,但并未对乡土伦理和工业发展相互联系的体制机制作进一步探讨。
作为理想信念的“士绅”则指费老本身作为一名士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士绅道统的长期坚守。费孝通在其跌宕起伏、饱尝百味的一生中,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士绅,这种认同不仅是学术生命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王铭铭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记得几年前,我陪同一位英国教授拜访费先生,英国教授问先生到底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先生面带微笑地说:‘我还是士绅,没变!’”对费孝通的“士绅”的理想信念的解读,应当放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中去理解,对于他本人来说,解读他的理想信念实际上也是在解读他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所秉承的“士绅”的理想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士绅研究的客观性。费孝通笔下的士绅大多是以伦理的传承者和道统的捍卫者角色出现,较少触及士绅的消极作用,但士绅的消极作用却是不可全然回避的。瞿同祖就认为:士绅利用特权逃避包括田赋在内的一些税负,导致普通百姓的税负加重了;士绅还通过为普通百姓充当缴税代理人,按普通百姓的应纳税率收取,再按士绅较低的税率上缴,从中赚取差价;士绅有时还为了袒护亲属或是攫取金钱而干预司法,或与官府勾结。可见,费孝通的士绅研究一定程度上受到其价值观影响,具有较强的观念色彩。
费孝通的作为研究对象的“士绅”和作为理想信念的“士绅”统合于一个根本问题之下:士绅在面临社会转型时应当如何转变自身,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在围绕这个根本问题的探讨中,既是相互融合的,也是互有张力的。
先来看融合的一面,费孝通的有关士绅的学术研究生涯逐步建构了他对于士绅的理想信念。费孝通对士绅的研究贯穿其一生,从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到英伦游学,再到云南三村的研究,到后来皇权和绅权的讨论,直到他晚年的“文化自觉”,他继承了绅士的道统,也继承了士大夫的“天下”想象,将其描述成政统和道统合一的“王道”。
再来看张力的一面,《中国绅士》的前四章与后三章的联结就体现了这种张力,即费孝通似乎并没有很好地将对士绅的分析与乡土工业有机勾连。在前四章中,费孝通着重从文化、伦理层面探讨了士绅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后三章中,费孝通则是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分析了乡土工业的破败对士绅阶层的影响,但费孝通对两部分的联结仍然停留在政治经济学层面。他认为:乡村的侵蚀最主要的原因是人才的流失;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社会知识分化的格局,但与他们的前辈相反,学会了技术知识,却没有学会这些技术知识相与配合的规范知识。但是,在面对“士绅阶层的道统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将何去何从”,或者更直接地说在“士绅阶层如何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变”这个根本问题上,费孝通在书中没有予以正面回答。费孝通对传统士绅强调的是道统,是伦理;但对近代知识分子强调的是科学技术,并认为“技术本身是没有伦理的”,那么伦理和道德的位置应当安排在哪?费孝通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1946年在伦敦政经学院的演讲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在吸收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要为道德和伦理找好位置。但士绅的道统究竟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产生应有的作用?费孝通似乎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费孝通无法圆满地将士绅的道统融于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根源是他赋予了士绅阶层超乎其历史使命的责任,作为理想信念的“士绅”逐渐脱离了客观历史,两个世界的“士绅”的张力至此达到了最大化。杨清媚认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帝国政治的官僚体系中,费孝通没有重视相权在皇权和绅权之外发挥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费孝通缺乏对心性学的足够了解,而心性学和治平学是儒家的两大主干,“心性是内圣之学,治平是外王之学”。费孝通的心史脱离了客观历史,客观历史对他来说成为单纯的“社会事实”,因为他不断地在社会范畴中去解释它。
费孝通在心性学上的匮乏固然是其心史脱离客观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断裂的客观历史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相反,费孝通关于士绅的心史是源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是延续的,即传统意义上的士绅应当在大一统的皇权下保全自己及宗族,而现代意义上的士绅则应当担负起社会团结和意识形态结合的责任。或许,社会结构的转型本身是不带有伦理意涵的,西方技术与中国传统伦理本身是难以相互融合的,因此,费孝通延续的心史和断裂的客观历史之间的张力是其赋予士绅阶层超乎其历史使命的责任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两个世界的“士绅”的张力的来源。
但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重提费孝通的士绅研究是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我们在改革进程中不仅应该在政策和制度上下功夫,也应该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对官僚阶层而言,我们在制度上、法律上给予其约束的同时,更不应忽视人心层面的工作。如何进一步从传统士绅的道统中挖掘、利用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有利因素,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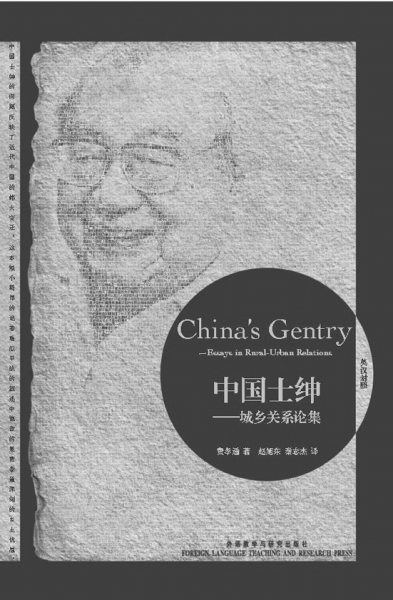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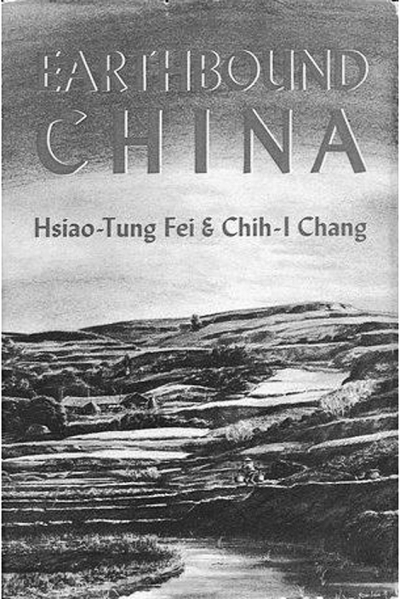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