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今夕何夕,见此邂逅”。
初春时节,我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作关于“伏尔泰与中国”的学术报告,大厅听众席一片静穆。忽然,一位皓首老者步入会场,朝讲坛挥手致意,接着情不自禁地趋前跟报告人紧紧拥抱,放声说:“大仲马写了小说《二十年后》,咱们可是30年后重逢啊!”这一突如其来的情景,令报告厅内满座惊讶。我赶忙向众人介绍来者。
光阴倏忽,花开时节又逢君,而且在这样的场合!相见大欢。霎时间,我脑海中浮现20世纪80年代一个春花放候的晴天。是日一大早,我为考证“巴黎公社墙”的真伪,在巴黎历史博物馆借阅罗什古德侯爵所著《巴黎街巷漫步》和《拉罗氏月报》等一系列书刊。继而转至巴黎装饰美术馆专门查询关于雕塑艺术的文献。我从数十卷《二十世纪雕塑杰作集》中找到法国美术家保尔·莫罗-沃蒂耶雕砌的所谓“巴黎公社墙”。这一作品的法文确切题名为“Aux victimes des révolutions”(“献给历来革命的受害者”),上边还有沃氏在完成浮雕墙后站立其前的留影。这一证据表明,保尔·莫罗-沃蒂耶的作品并非如法国历史学者吉·德拉巴杜在《巴黎街石》一书里所描述的那样,根本不是装饰在真公社墙——拉雪兹神甫公墓内夏洛纳墙上的浮雕。沃氏墙单独坐落在另一处甘必大街心花园,“鸠占鹊巢”,在全球广泛讹传为“巴黎公社墙”,而实为否定巴黎公社及历来革命的反动作品。
在装饰美术馆时,我借出贝奈特主编的《美术家辞典》(1948年版)和彼埃尔·克热尔贝格撰写的《巴黎雕像指南》等多部书,堆在桌上逐一翻阅。我见对面一位文质彬彬的法国学者也在查资料,就冒昧向他请教法文“Aux victimes des révolutions”的确切含义。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这一题词是说,革命造成了受害者,所以立碑追悼亡灵。”陌生人瞧我面前摆满一大堆书,好奇地问我忙着查找什么。我说自己在考证“巴黎公社墙”。他对一个中国人的探求产生兴趣,说:“我是专门研究建筑艺术史的,知道保尔·莫罗-沃蒂耶的浮雕颇有名,但从不曾考究过它的底蕴。您的努力很有意义,我应该帮助。”
异域遇知音!我跟他进一步攀谈起来。他深思片刻说:“保尔·莫罗-沃蒂耶的雕砌墙立于甘必大街心花园,属巴黎市内,肯定得经巴黎市议会讨论,作出有关决定。我可以进出巴黎市政厅档案馆,能领您去查找巴黎市议会竖立这堵墙的决议。考证关键在兹。”言罢,他中断自己手头的研究工作,交还所借阅图书,让我跟他一起直奔巴黎市政厅。路上,我得悉他是巴黎拉维莱特建筑学院教授米歇尔·维尔纳。
抵达市档案馆,已是下午三点钟,再过两小时就要闭馆了。我俩赶紧分工查阅巴黎市议会历年会议纪录合订本,最后将范围锁定在甘必大街心花园竖立“沃氏墙”的1909年。但是,就只查这一年的卷宗也像法文里所说的“干草堆里摸针”一般,更何况时间异常促迫。到四点钟了,仍不见一丝影迹。实在让人有些莫可奈何,我翌日得乘飞机归国。一念及此,顿觉心事难竟。“今天查不到没关系。”维尔纳教授安慰我道,“您回国后,我继续查找,一有结果就转告您。”我为法国学者的热忱激励,继续翻动面前厚厚一册巴黎市议会会议记录合订本,瞧着一页页、一行行密密麻麻的铅印字母,在文海里捞针。时间一分一秒毫不容情地过去。突然,恰在一筹莫展之际,我有些茫然的目光被法文名词“érection”(竖立)吸引。凝眸定睛细看,正巧是我们要找的巴黎市议会《关于在甘必大街心花园竖立保尔·莫罗-沃蒂耶所雕“历来革命受害者纪念墙”的决议》,载于1919年会议纪录第1302页。
依据这一文件中的记载,我们很容易就按编码查到1908年巴黎市议会就此事开始讨论的纪录及其他相关文件,其中都明示“沃氏墙”题名为“献给历来革命的受害者”。至此,沃氏作品真意辨明了了,假公社墙的真面目昭然若揭。维尔纳教授显得很兴奋,分享我的喜悦,两人握手惜别。
我对米歇尔·维尔纳教授心存感激,回北京后时时忆及,但无法再跟他联系,不知其所向,几度重返巴黎寻觅,一直杳无音信。去岁,我妻子花了不少功夫在因特网上查找维氏下落,但有一大串同名者,打电话屡屡碰壁,只得一时搁置。今年是巴黎公社140周年,我们夫妻俩去拉雪兹神甫公墓瞻仰“公社战士墙”,自然又想到米歇尔·维尔纳教授。维氏曾获“法国国家建筑艺术评论大奖”,著作等身。我们再在网络上搜索,查到他的主要著作由位于奥尔良市的“伊柯思出版社”出版,于是给该出版社打长途询问。那边确认米歇尔·维尔纳教授的近作确系由他们出版,允诺帮助我们联系,但不知何故久久没有回音。3月中旬,妻子又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终于从值班编辑处得到维尔纳教授居住巴黎维维耶奈街的电话号码。
“请问这是维尔纳教授家吗?”我妻子拨动电话,心存侥幸地问道。
对方正是米歇尔·维尔纳本人!我妻子惊喜至极,继续问道:
“您还记得30年前一位中国人跟您一起去巴黎市政厅档案馆的旧事吗?”
“当然咯!”对方毫不迟疑地回答,“他勤求真理的精神让我至感!我们一起去巴黎市政厅档案馆查到了竖立保尔·莫罗-沃蒂耶雕砌墙的决议,澄清了巴黎‘公社墙’的真伪。”
妻子告诉维尔纳教授我又来法国了,即将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作一场学术报告。他一听立即表示一定要赶来见我。
及至在中国文化中心见面,真可谓有缘万里再相会了。久违容貌,见伊年垂八旬,一头银发,感概万端。维教授幽默地称自己的白发是智慧象征,声扬智慧是在不断求索中积累的。
“当年,正是您的求知欲望打动了我。”他回首往事说,“咱们分别的30年间,我数度赴中国讲学,在一个伟大的国家里增长了见识,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中国迷’。我迷上了中国秀丽的山河,自然非常热爱中国人民。在南京上课时,一个中国女学生来讲台前对我说:‘老师,我们看得出来,您喜欢我们!’她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确实热爱中国,欣赏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
我向维尔纳教授介绍来文化中心听报告的几位中国留法女博士生,宾主欢悦,欣然合影留念。
那是异邦塞纳河畔一个夜晚的邂逅。在探求真理的途径上,我认识了一个法国知识界的睿哲。30年里,虽然只两回谋面,却在心坎留下了超越疆界的交谊,益信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情此理永世不泯。
我再来时人犹在,宛若曼殊上人在《花朝》一诗中所云:
但喜二分春色到,
百花生日是今朝。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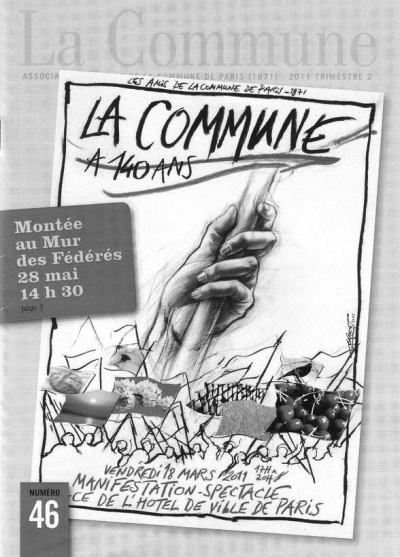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