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教授
■何乏笔(Fabian Heubel):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当代转化
李雪涛:你上次谈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如何转化为可以思考世界当代问题的方式。我觉得这个转换成功意味着中国资源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我以前读过一篇用《文心雕龙》的文艺批评的范畴、概念来作西方文学批评的尝试,总的说来是“方圆共凿,金石难和”的感觉,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也可能是因为从我的知识结构和储备没有办法认同这样的批评方式。这次你和夏可君在宋庄策划的有关“当代平淡绘画”的展览和研讨会,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你前两年来北外的时候,我们共同上过法国哲学家和汉学家“于连(Fanɕois Jullien)批判”的课程,也是在课上我们讨论过“平淡”的概念:这一概念首先是于连1991年在其著作《淡之颂》中触及的,他将中国文人的思想和美学作为一种参照来思考欧洲文化的特质。通过你组织的展览和研讨会,如何能把传统的中国绘画的范畴和概念运用到当代艺术中去,对此我充满了好奇。诸如“平淡”一样的具有传统中国审美观念的文艺批评范畴是不是可以被普遍地接受,或者是怎样让他们接受?
何乏笔: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没办法简单地予以回答。昨天有一位中央美院的教授来看这个展览,他邀请我明年在中央美院进行有关“平淡”的系列演讲。他觉得这是很值得讨论的主题,因为他也在寻找有助于反省当代中国处境的艺术创作和美学话语。文人美学的资源,在当代的问题脉络和危机意识之下,该如何发挥作用,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先回答:在何种意义下,平淡是一个美学的范畴?请不要忘记,美学是现代学科分类下的范畴。如此,我们在这个具体的例子方面,又要面对传统和现代学术之间的动态关系。
汉学、国学与二谛义
李雪涛:我上面提到,“汉学”也好,“国学”也好,把它们作为一个学科我觉得都是有问题的。我举个例子,佛教三论宗有“二谛义”之说,我想很适合汉学、国学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学科间的关系。根据《中论》“观四谛品”的说法,一切事物本来就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即所谓的实体、自性),为无生无灭之空。明白了此等空无之理,就是第一义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谛。不过,一切事物的空性,为保持空性的作用必须在假现的事物上显现,而由其相依相待的关系产生认识作用。知道了此等假名之法,就是世俗谛。佛教并不认为“得意而忘言”,而是认为,世俗谛虽为不究竟之法,但是却可以借助它来探索、趋近真谛。如果不借助于言语、思想、观念等世俗谛,则根本无从向众生解说超越世俗谛的真谛。三论宗认为,仅仅从“有”或“空”来理解事物,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从“空”、“有”两方面来体认,方能得到实际情况。
具体到汉学与国学作为学科,我认为都是不能成立的,也许为了一时之需或者说在过渡时期它们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从究竟意义上来讲,最终还是要归到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等具体学科之中去的。尽管中国学术本身有其特殊的地方,但我依然认为,目前按照现代学术划分后的中国学术的某一领域与它所属学科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举例来说,中国历史与历史学科的关系比它与中国学术其他领域的关系显然更加密切。尽管我认为汉学系应当慢慢地将中国学术的各个专业慢慢分离出来,应将这些专业归入各个现代学术专业之中去。但我还是认为,中国学术之间的联系也还是很重要的,毕竟中国学术的各个方面曾经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影响、共存了几千年之久。实际上,汉学系最主要的任务是教授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包括语言、文学、历史等,而不能取代各个专业系科对中国学术进行的深入研究。但是至少从目前德国汉学系的状况来看,汉学家们很少能在西方与主流的学术展开对话。很多大学汉学系的教授只能是万金油,他们是有关中国学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一般德国人的心目中,汉学系的教授应该对中国的所有方面都很了解,而在今天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汉学家很难与各个学科的学者进行学术上的交流。
何乏笔: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汉学已面临严重的正当性危机,但是新的学术架构还没有形成。在美国,中国研究已经逐渐分散到不同的学科,但在欧洲这个发展非常缓慢。问题是,我们应如何促进这个发展?你的视野比较宽阔,应该从未来发展的潜力思考这个问题。包括中国大陆的文化政策,都是要从这个问题、从未来的发展来设想。例如,要不要赞助汉学的领域,还是某些专业学科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的策略性选择。面对国学和汉学的问题,你应该怎么设想它的未来发展,尤其是汉学,你怎么看?
中国学术的正当性
李雪涛:如果面向未来思考汉学的出路的话,我认为中国学术要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首先要强调学术分类的共性,而不是只重视中国学术的特殊性。具体地讲,就要让中国学术进入西方大学体制的不同专业之中去,因为汉学系无疑是殖民时期的产物,显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只有进入了不同的专业学科之中,中国学术才能获得正当性,那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才可以正常地与欧洲史学者进行对话。另一个方面,我也一直强调汉学的过渡性价值,以及东亚学术之间横向的、内在关联性。在一定程度上讲,设立一个类似东亚研究中心的虚体机构,也同样是很重要的。
何乏笔:这就是跨学科的串联。例如说,海德堡大学所设立的“雅斯贝尔斯高等跨文化研究中心”(Karl Jaspers Centre for Advanced Transcultural Studies)。这个中心属于“全球背景下的亚洲与欧洲:文化流动的不对称性”卓越研究群(Cluster of Excellence "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 Shifting Asymmetries in Cultural Flows"),由联邦政府所赞助。这个计划能获得批准是因为连接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做法——德国政府所赞助的大型卓越计划都是要凸显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基本方向。这种学术政策恰好要打破学科的封闭性。这样,汉学就融入到跨学科的架构里,而在这个架构中确实能获得新的意义。那么,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发展不让我满意,因为它不代表中国的古典哲学被德国哲学界肯定。在新的跨学科的趋势中,哲学本身也被边缘化了。但无论如何,我们能看到新的知识结构的形成。知识结构的变迁使得传统汉学系关起门来做学问的方式加速终结,当然也使得以思想和文学文献为核心的经典研究进一步解体。
李雪涛: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好,这是一个实验场,对于以后德国乃至欧洲的汉学发展提供一种可能性。反观国学,我一直认为这是由于在当代依然有很多的人担心源于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类方法会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主体性与独特性而形成的。而真正的问题是,现代的学科体制能否充分凸显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价值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又回到之前提到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去了,而不再是“东方与西方”的问题。今天我们还可以拒斥现代学术体制吗?国学的一部分内容我认为可以归在“古典学”之中,不过我也在考虑,其意义究竟何在?
何乏笔:在欧洲,“古典学”或“古典文献学”(klassische Philologie)曾经是汉学的重要参照系统,但对当今的德国汉学而言,这种研究方式已经彻底边缘化了。在当代法国汉学中,情况不完全相同。
汉学与国学的未来面向
李雪涛:我还在思考一个小问题,就是国外学者如何定位当代中国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比如清华国学院的院长陈来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单就哲学这个范畴,按照1904年张百熙(1847—1907)、张之洞(1837—1909)等人进呈的《奏订学堂章程》中的观点,它就不是国学了,因为当时在大学堂的课程中设的是“经学”科。反过来,陈先生肯定不是汉学家。你会称他是什么家呢?前些日子我在北大开德国女汉学家的一个研讨会,见到Kristin Kupfer博士,她曾经师从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辜学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尽管她现任弗莱堡大学汉学系的讲师,但她向我介绍自己的时候说自己是政治学家。但别人总是称呼她为汉学家,这让她自己觉得有些尴尬。
何乏笔:我的专业是哲学,但德国汉学家对哲学没有兴趣,而德国哲学家对中国没有兴趣,这是我的尴尬。大部分的德国哲学家对中国思想一无所知,无论是古代的或当代的。如果要跟德国学者介绍陈来教授是做什么的,只能说是研究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德语里根本没有一个表达“国学”的词,在中文语境之外没法理解。翻译的时候一定要确定是指什么“国”的学问,所以变成“中国学”,因此离不开欧美学术界有关汉学和中国学的争论。汉语拼音的“Guoxue”也没法理解。在这个脉络下,跨文化研究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能帮我们扭转整个观点。在当今逐步全球化的世界中,民族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立足点基本上已经被瓦解了,或者被质疑。我认为目前在国际上最活跃的、发展最迅速的、最有广泛影响力的学科,不是站在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学科,而是强调不同的语言、文化之间的动态交流和混血关系的学科。所以我用“跨文化动态”来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流动状态中,特别强调中华文化的纯正血统或许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当今比较前卫的学术发展,不可建立在一个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做学问。但这不是说要彻底否定民族文化的存在,而像是你所讲的真谛和俗谛,要调节民族文化和跨文化动态的紧张关系。
李雪涛:你上述的观点我基本认同,如果从一个大的历史叙事来看更是这样。民族主义实际上仅仅是人类多种认同感中的一种,其他诸如对人类共同体、语言以及家庭等的认同,也都同时存在。我不希望将民族认同作为唯一的自我身份认同,社会要允许多层次认同感的存在。之前我们举的19世纪下半叶学科的划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很陌生了,这个流动的进程在一两百年间是非常大的,全球化无疑又加剧了这个进程。现在看一两百年前定下来的学科划分是很有问题的,有一点很重要,你也提到了,我们要面向未来,充分考虑将来会怎样。我认为,坚守现在国学和汉学的阵营,是没有出路和未来的。因此如果要在文化上有所进步和发展的话,需要一个面向未来的思考,并做出相应的方案。这一次我们仅仅提出了问题,从大的方面对讨论的范围进行了勾勒,没有办法更深入进行讨论,期待着以后更有针对性、进入更多细节的探讨。
何乏笔:是的。在思考当代处境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选择中国的经典作为出发点,但不能只是把它放在中华文化的脉络下来加以思考,同时也需要打开跨文化的视野。比如说,研究《庄子》的时候,也要关注为什么《庄子》在法语学术界特别受重视。为什么毕莱德(Jean Franɕois Billeter, 1939—)认为《庄子》的“主体性范式”充满当代性呢?因为它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最强调多元性的转化思维,而思考主体性和文化认同的多元化,正好也是当代全球化世界极为迫切的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对当代最有意义的中国思想,或许不是要巩固单一的自我认同、捍卫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而是要有助于发展多元的主体性,促进自我反省以及自我转化的思想。《庄子》就代表一种对民族文化、对单一主体、对固定立场的怀疑态度。
李雪涛:所以今天看来,庄子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最当代化、最具有当代思想意识的代表,而之前我们一直认为,近代以来一切跟文明相关的想法都来自西方。本学期我给博士生开了一门“全球视阈下的中国近代史观念”的研讨班课,在课上我们讨论每一个近代史的重要观念,在中国革命史上怎么看,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怎么看,日本学者是怎么看的,德国学者怎么看,很有启发。这样,一个学期下来,同学们觉得以前认为确定无疑的史实都不那么确定了。也开始慢慢了解历史描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张力以及历史描述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样,大家开始了解到,历史事实并非是被给定的,而是不同时代的史学家们根据历史的新问题、新方式和新对象建构起来的。任何唯一正确的描述和定义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我们需要确立解释系统的多样性。这样,学生们就不会再轻信任何一种所谓真实客观的历史描述了。当只有一个观点来源时,人会变得偏执。我觉得国学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它想建立一个新的正统。在今天,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何乏笔:当然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可以讲“《易经》管理学”,但不得不在国际贸易的脉络之下来讲;可以用《孙子兵法》打败西方资本家,但是这个目标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里面达到的,我从来没听人家说要使用《孙子兵法》来搞出一个新的经济体系。我觉得,与其批评汉学与国学,还不如提出一些新的思考角度,邀请两个领域的人来参加,在明确的问题脉络下进行反思。我现在对批评(欧洲)汉学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因为认为汉学属于过时的知识结构。在一个面向未来的思考里面,可以尝试着让这些领域的学者参与,以产生更深刻、更多元的历史反省。我想这是目前可以做得到的,也是有价值的方式。
李雪涛:你的建议很好,我想,这样一个预设既可作为此次对谈的结束,同时也可以作为下次对谈的开始。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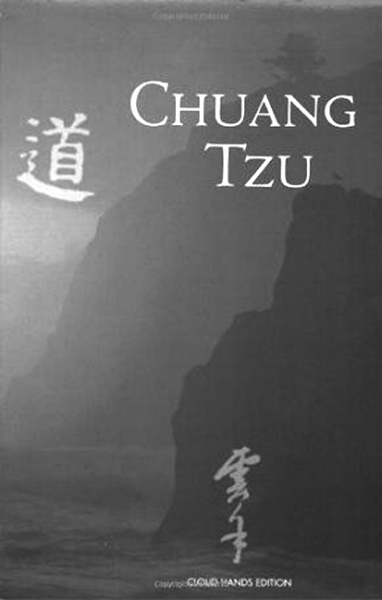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