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寻路中国》的书名,会以为这是一本背包客写的旅行读物。还好有个副标题——“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给了读者一点提示,这不是一本单纯的旅行读物;或者也可以说,根本不是一本旅行读物。至少,它没有旅行作品常有的游山玩水、借景抒怀的文字。它的作者是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何伟,当过美国《纽约客》杂志的驻华记者、《国家地理》的撰稿人。本书就是海斯勒2001年考取了中国的驾照后,在此后的七年间,驾车漫游于中国从西到东的乡村与城市,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结晶。《寻路中国》连同他的另两部中国题材的纪实作品《江城》、《甲骨文》,构成了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三本书横跨了海斯勒在中国的十年,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见证了中国在这十年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江城》甫一推出便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美国《时代周刊》年度最佳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也被《华尔街日报》誉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作家之一”。可见中国纪实三部曲在西方世界激起的反响,也说明《寻路中国》是断不能把它当作旅行作品来读的。
《寻路中国》由三条不同的线索平行构成。第一条线索是作者从北京出发,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第二条线索则聚焦因中国汽车业的飞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作者特写了长城脚下一个农民家庭在这一嬗变期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第三条线索则是作者驾车沿着中国的东部沿海,考察了浙江金(华)丽(水)温(州)地区的工厂和小镇,记录下了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老板和政府官员的点点滴滴,勾勒出了急剧变革的年代这些普通人命运的变化,由此探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和动力源泉。
在本书中,进入海斯勒视野的,都是他沿途遇到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河北、陕西交界的一村庄葬礼上遇见的名片上印有27个服务项目、号称实行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的风水先生张宝龙,专心于研究长城的前村支书老陈,在鄂尔多斯沙漠搭便车、到城里美容院打工的农村女孩王燕,向海斯勒提出开一段吉普车要求的退伍老兵,在江苏、甘肃之间跑服装生意的巨能王卡车司机李师傅,以毛泽东名言自勉、在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打工的云南苗族青年小龙,等等,海斯勒为这些开放年代的普通中国人留下了一幅幅简练而传神的速写,记录了他们的梦幻、迷惘、奋斗和追求。
海斯勒驾车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以一个记者的敏锐搜寻、思索着现实的中国,同时不乏学者的视野,考察、探究着历史的中国,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解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动因所在。他考证出现代中国大规模的公路建设始于1920年华北地区的大饥荒,为了把粮食送到忍饥挨饿的灾民手中,美国工程师奥利弗·托德受雇开始在山东境内修建公路。到1935年,中国状态较好的泥土公路已达到了八万公里。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还曾写信给亨利·福特,邀请他来中国投资办汽车厂。这些对现代中国初期道路交通现代化努力的记述,加深了本书的历史纵深感,可以说是书中叙述的本世纪初北京每天有近千人考取驾照,中国迎来汽车工业飞速发展这一辉煌年代的“前传”。海斯勒的目光穿越了历史,停留在长城脚下一个名叫三岔的山村里,他住在租来的农民的屋子里,参加村民们的劳动,与村民们交流,帮助村民的孩子看病,记录下了自己居住的几年间山村方方面面发生的变化。尤其是他笔下的村民魏子淇,外出打过工,干过保安,回到家乡后搞过养植,虽然失败了,但没有气馁,他抓住了城里人驾车来乡村旅游带来的商机,建起了农家乐家庭餐馆。魏子淇的脱贫致富由城里驶来的汽车而起,富裕之后的他又买了汽车,汽车改变了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可以说《行路中国》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海斯勒的观察是敏锐、宽阔而又细腻的。在描述三岔及魏子淇命运变化的过程中,他还涉及到了中国社会及农村改革的许多深层次问题,比如,由陪魏子淇儿子魏嘉去城里看病遭遇的困窘反映出的农民看病难问题,从魏嘉的死记硬背课文折射出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及应试教育弊端,由魏子淇妻子致富后的焦虑及信佛反映出的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信仰缺失问题,从三岔村对外旅游合作项目开发的暗箱操作凸现的基层权力缺乏监督,等等。海斯勒将他的这种多维度的观察、真实客观的记录贯穿始终。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描写东部沿海金丽温地区工厂、农村的见闻中,海斯勒全程跟踪了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的罗师傅,他有一手调试机器的过硬手艺,他不满足于打工者的角色,时刻寻找着机会,在本书的结尾,胸罩调节环制造厂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搬迁到了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外地,罗师傅则自立门户,建起了塑胶加工厂,圆了自己的老板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曾经穿普拉达、带贴身保镖、用高档洋酒招待海斯勒却又随口吐痰的暴发户季胜军,终因非法集资东窗事发而锒铛入狱。海斯勒勾画出的罗师傅与季胜军这命运的两极,可以说是改革大潮风起云涌的年代中众生相的缩影。
海斯勒的许多观察和思考,还可以促使我们反思中国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走向。比如,他比较了中美两国新兴城镇诞生时的差异,“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至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确实,中国改革的深入,已到了需要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公民意识的觉醒的阶段,这是我们的社会走向健康协调发展的保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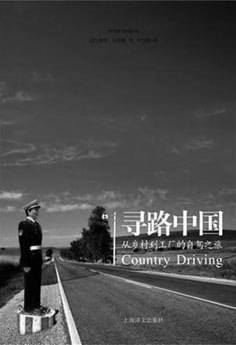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