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缪哲在《自序》里言及,真没意识到《祸枣集》是他的第一本书。他自己也说,“从1986年开始,我就煮字为生了”,写了这么久,读者肯定有印象,进而产生其已著作等身的错觉。这错觉并非只靠从文时间跨度之大、报刊露脸之频密而诱发,实在是他的文章见识宽泛,观点独到,词句讲究,让人读过难忘所致。
所谓“祸枣”,应是成语“祸枣灾梨”所喻,古人多用枣木或梨木刻版印书,浪费恁多枣树梨树去印无用的庸作便为祸不浅。缪哲的文章是否有用?那要看读者对“开卷有益”的理解会功利到什么程度。想从《祸枣集》中参透什么微言大义或是临时抱佛脚应付考试再或是从中汲取积极向上的励志力量,怕是会失望。想必这也是作者以此为书名的自谦之意,这份自谦透着对文字的尊重,此种写作态度弥漫在他诸多文章中。如他笔下这般既文采漾动又情绪克制,古意乍现且与时俱进,含蓄着犀利,幽默中带些温情的文字现今可算稀缺,这令书中篇章在流畅可读之外亦经得起咀嚼,品味得出作者成文过程中的打磨与斟酌。
据说此书最终得以问世要归功于出版商尚红科与《南方周末》编辑刘小磊的敦促,从缪哲多年“七杂八芜的小文”里拣选若干集结成册。正因如此,书中所收文章的体例真够散的,专栏、序跋、书评、文论都有,内容指向则事关亲情、友情、读书、治学、翻译及不可归类的其它。这些篇章能否呈现一个文字背后的缪哲未可知,唯恐漏下他某方面的行文魅力倒是真的。这书就像从他二十多年笔耕光阴的沙漏中流淌下来的沙砾,几经筛检,细碎绵密,队列松散但不会掩盖文字的光芒。
专攻艺术史的缪哲系北大中文系科班出身,文化、思想最为蓬勃活跃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他的求学阶段,彼时的大学仍有学术净土般向学、自由的氛围,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至今回味不尽的美好遂构成书中“忆往”的重要部分,也是全书最为感性,真情流露的部分。他在《开场白》中忆及那时老师上课前的几句话有如旧时相声演员的“定场诗”,比如教古音的唐作藩教授一登讲台就是大实话,“我这课你要会呢,就别来了。不会呢,也别来了”,足见这门学问的艰深,唐教授的形象用笔触白描出来,活灵活现。大学时代同窗也多理想主义洋溢个性特立独行的“神人”,且不说经历颇富传奇色彩的老Tra,那个志在成为诗人却“误入”北大法律系的骆驼被缪哲“揶揄”为“骆驼不来中文,固未必如他自信的那样,是文学的损失,但入读法律,却是法律系的赘疣”(《记骆驼》),他的故事同样有理想与现实间惨烈交战的唏嘘。
缪哲喜欢诗,既读也写,自然对为诗之道不乏心得。他从北岛的《时间的玫瑰》中读出作者的“自负”,盖因北岛对欧美诗作的不少汉译本不以为然,认为里尔克不够伟大,但“北岛也自称不通德文,说里尔克不伟大,一定是从译本得到的印象。而诗翻译了之后,剩的只有观念、意象而已”(《北岛的“世界诗学”》)。在这里,缪哲引用宇文所安对所谓“世界诗”的定义,“诗人意想的读者,不是与自己同文的人,是全球人”,他认为北岛即如此。这样的表述是相当典型的缪哲式的点到为止,他不是没有批判精神,只不过他的敏锐直指臧否本体,如古人比武,意在过招而非伤人。所以,他评价宇文所安的文字优雅而有杀气,用以形容他自己的文章也算恰当。
学术研究与写文章之外,偶尔为之的译作亦不失水准,须知《瓮葬》或《塞尔彭自然史》就内容而言都是翻译的硬骨头,缪哲的中译本口碑甚佳。而《钓客清话》仅此书译名已收到中西交融之效,若不是知情,谁会想到这是英国作家沃尔顿的散文经典?多像明清小品。说到翻译,如今一方面读者和出版方都抱怨好译者难找,另一方面翻译的社会地位乃至经济收入堪忧,于是《祸枣集》中最“情绪化”的文章《谁实为之?》适时而生。“如今的物价,去当时三十倍不止,但眼下译文之质量,差前贤不过十倍。这个成绩,我是喜而过望了。论事要平恕,喂耗子料,求千里足,岂有此理?”该为如今译界水准每况愈下负责的固然不只是劳酬不均衡,但这绝对是主因。“记得四年前,我结束了最后一本书的翻译,时间已是午夜。望望窗外稀落的灯火,心里很落寞”,这样忧伤的情绪会成为缪哲译作的终结吗?我想不会,只要有触动他的外文佳作,只要他还心存与同道分享之念,重操译笔也许指日可待。
当整本书随着一连串序跋文字戛然而止,思绪还惯性似地停留在缪哲的意趣中,有点意犹未尽,“二十年煮字,仅得这薄薄一册,深觉愧赧”。其实是无心插柳地吊起读者的胃口,应该愧赧的肯定不是他,坊间泛滥得满坑满谷的庸作劣作还不是充斥书市,只不过那些真正的沙尘不自觉罢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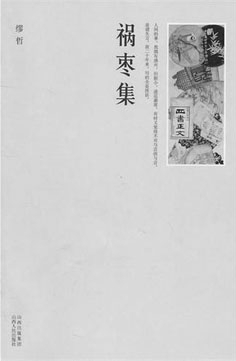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