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图2 图3
作为土生土长的陕北人,我对陕北文化一直怀有深厚感情,但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2007年,我的挚友老乡、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张东升先生,告诉我“中华书局”出版了当年北京赴延安插队知青王克明编著的《听见古代》,他认为是近年来最值得推荐的一本关于陕北方言的大著,也是最有可能传世的作品。为此,他自己掏钱买了二百册分送给关心热爱陕北的朋友们,并叮嘱我认真拜读。关于王克明,我和东升先生都未曾谋面,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看法:作为陕北人,作为深爱着这片土地、人民及其文化的陕北后代,我们应该向王克明先生鞠躬敬礼!,就能听见古代。王克明的《听见古代》以陕北方言为线索,运用独特的视角,把当今应运的陕北词汇追溯到古代,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陕北这片黄土地上下几千年的历史、被忽略了的文明和别样的民俗风情。用王克明先生自己的话说:“在寻找方言的历史时,所有的界限都可能消失,古代的历史,可以直接延续到今天的生活里面。方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观念形态,就在周围。”一个外来户,为融入陕北被迫学说地方土话,从简单的弄明白到感兴趣,从疑惑到寻根探源,竟先于我们这些坐地虎弄清了陕北方言之所以然,这对我是一种启发,也是一大惭愧。
好奇和自醒,促使我开始整理收集下准备好高骛远搞创作的陕北方言词汇。当我在文化视角下重新审视那些后鼻音齆齆作响、被认为土的掉渣的陕北方言时,我震撼了!对母语与生俱来的生命感悟告诉我,陕北人不经意间挂在口上的方言,其实正是生命状态下的古代词汇孑遗,这种完全靠民间口语、而非官方规范原汁原味传承下来的语言文化,反倒为中华文明保留了一抹亮丽色彩。陕北方言孤岛之沉积岩,不但处处折射出中华文明之发展轨迹,或许还能为我们找到破解中华文化基因之钥匙。徽钦,这个国史上最耻辱的靖康之难的二位亡国之君帝号,在陕北口语中表置于死地义,可谓入木三分;供给,这个古今通用的经济术语,引伸为供养义;鏖战,这个硝烟扑鼻的词,早已军转民用,表的只是打拼义;凌迟,这个血腥恐怖的刑罚词,已远离法律,表的不过是欺凌义;佛教女居士之称梵文音译“尤婆姨”,则以“婆姨”表示妇女、妻子义;争雌,这个专业的学术用语,表的则是一种强弱态势而非具体行为;谋略,也走出运筹之帷幄,成了平民的布置、实施行为……有趣的是这些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宗教,乃至有学术背景的词汇,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用的越多;越是文盲,表达的音义越是准确。如“供给”,凡读了几天书的,反倒易将其读作“供给”(gòng gèi),为什么?秀才识得半掐字!倒是被认为瞎字不识的村夫农妇,“子乎哉也许兮矣”等文言虚词整天不离口,就是简单的行与不行,也一定会用“使得”、“使不得”来表述。且不说大量似曾相识的古老词汇如何“沦落”到民间(或如何由口语被文言化),单就文言文语法、古汉语词汇几千年不变,在陕北被中规中距地成建制使用,这本身就是一大奇迹。要破解这一现象,还得从陕北本身来解读。
陕北,从行政区划讲,是指延安、榆林两个地级市辖地;从地理区域讲,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南以金锁关与关中相接;西以子午岭与甘肃、宁夏相邻,北以毛乌素沙漠与内蒙古相连;从方言覆盖范围讲,则包括延安市的宝塔区、子长、延长、延川、甘泉、安塞、志丹、吴起,榆林市的榆阳区、神木、府谷、靖边、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共19个县区和定边县原属安边县辖区为主的18个乡镇(安边、武峁子、石洞沟、学庄、砖井、黄湾、油房庄、杨井、新安边、白泥井、周台子、海子梁、堆子梁、郝滩、胡尖山、樊学、白马崾崄、张崾崄)。
放眼陕北,黄河、长城在这里交汇,大漠草滩、黄土高原在这里交界,中原文明、游牧文化在这里交融,从秦大一统置上郡起,这里就长期处于汉族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垒前沿。侵袭与征服相间的无尽战火、有组织移民与自发迁徙相伴的人口流动史实,从延安、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安塞、安边、定边、靖边……这些诉求绥靖边疆的县名便可一目了然。军事上的讨伐、拉锯,必然随之以文化上的碰撞、交融。黄帝陵延绵不绝的香火,延安红都炫烨的光环,赫连勃勃“美哉斯阜”的感叹,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悲歌,李继迁分疆裂土的征战,李自成改朝换代的闯旗……使陕北历史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块精神高地、资源宝地、文化福地!
人们常常要问:为什么陕北民歌能“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其代表作分别是《东方红》、《哀乐》、《春节序曲》)为什么卫星上天、汶川地震,中国人用陕北元素、而不是其它来表达自己民族的大喜大悲?如你走进陕北,陕北方言和陕北方言所诠释的陕北文化之典型性、代表性,就是基本的答案。
陕北方言虽属晋语系,但长期的封闭运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口气大、底蕴足、直白而风趣,为大众所乐见。称天为“大”、“老子”,活脱脱就是天子一个!将爱溺言为“幸”,骂女人为“贱妃”,用的都是皇帝专利,一派帝王作派。人的实力以封邑来衡量,称为“采”,好像尚处春秋战国,人人都是王侯公爵。而成语“碰头打纥结”,尽管其义已走向反面成不必斤斤计较、取个大约,但从词面直译就是结绳以志义,是否可以此断定其源于结绳记事年代,可以说遐想无限。光绪帝的老师王培棻巡视三边写的《七笔勾》,不屑乡民“开口不离毬”无拘无束的言谈举止,将此处描述为“圣人布道此地偏遗漏”之所,是“礼仪廉耻一笔勾”,实在偏激。其实,“毬”是生殖崇拜体现在陕北话中的、活着的语言图腾,与人类自然崇拜到宗教崇拜进化的轨迹一脉相承,应感谢这块土地为我们提供了语言进化的浓缩版。不管外人怎么看待,反正陕北人高兴感慨一个“毬”字,扫兴发泄也一个“毬”字。一个民间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旧时一外商来陕北贸易,认为买方出口“毬”字是对自己的污辱,与其发生争执并诉讼至衙门。被告当堂辩称,这是说话习惯,并无恶意。县令做官多时当然知道,但为了说服外商,即出题给被告,让简述案由,如自然而然出现十个以上“毬”字,就算是口语,不问过。被告随口而答:“走毬米脂,到毬绥德,买毬把胡麻,搅毬把圪渣,装毬起,倒毬下,为毬个官司叫告毬下,老爷叫我跪毬下,我一卜敛站起走毬吧!”众人一听会意大笑,外商也不由一乐了之。
人们早就注意到了陕北文化中的少数民族因子,而忽视了她所释放出的大中华主旋律。从蒙恬“将兵三十万,怯匈奴三百里”,到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四面八方来陕北戍边的历代将士,献了青春献子孙,不可能划水无痕。这就是为什么陕北方言中既有“忽了”、“圐圙”等原始的蒙古语单词,也有吴语“搲”(wǎ)、粤语“(见图1)”(lè)、西南方言“(见图2)”(luán)等词汇,即使常被作为陕北方言典型词汇的“而刻”,在南方一些地方多有使用,只不过发音有所不同。作为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工具,文明传承最直接的纽带,各地方言间的这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必然的,因为她们来自同一根系——古汉语,而汉语是由方言构成的。值得一提的是,陕北封闭的地理、开放的历史、传统的民风,使各地的文化元素能在这里落地、升华,并传统地保留下来,且发挥其反作用,进而影响全国。了解了陕北文化这种地方性、多元性,就不难理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走向陕北,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民族文化”之论断。
在千古一帝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币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语同音作为国策被强力推行已成趋势。行政上,方言不能进课堂、进讲堂、进大雅之堂;生活中,普通话成时尚、成时髦,方言阵地快速萎缩。如陕北称棒为“卜榔”,读的是“棒”的分音,但当翘起大姆指新潮地表扬人很棒时,再地道的陕北人也不会说“你很卜榔!”“卜榔”自觉不自觉地被“棒”无情置换。过去陕北人称父亲为“大”,可经过将一切古旧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文化大革命”洗礼,“大”被作为守旧的标志而惨遭淘汰,回望陕北,叫了一千多年的“大”,已进入绝迹的收官阶段。改革开放前还在煤炭交易中使用,兼具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汉字要素特征的标码数字炭码码——(见图3)(1—9),时至今日,别说认识,就是知道曾有此数码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我的一双80后儿女最早接触此书,却如看天书,十有六七不知所云。这真实地反映了陕北方言的生存现状。
方言的消失也许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我们不能无视方言词汇、方言成分消于无声、失之无形。在中国这个崇尚大一统的社会,春秋有雅言,隋有韵书,明有官话,民国有国语,今有普通话,不过我们就是缺乏西汉扬雄《輏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这样对待方言的态度。时下与忽视方言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对英语的“重视”和滥用,这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更有中国文化之安全!普通话与方言不是简单的孰优孰劣。客观讲,离开方言就无法了解现代汉语的源渊、承接、演变,甚至无法准确把握其词义;离开方言,就无法体味中华文化之多姿多彩。“乡音未改鬓毛衰”、一声乡音泪先流,方言的这种无以名状的情感和亲和力,正是中华文明生命力、感召力、凝聚力的具体写照。
陕北人从相貌特征上讲是鲜卑人、党项人、匈奴人等北方民族与汉人混杂的遗传结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典型特点如同听见古代的陕北方言一样正在淡化和消失。传统的陕北文化也正在离我们渐行渐远。对此,我们无能无力,唯有呐喊作为警惕。2010年春天在北京的郊区农村,我和东升及几个陕北朋友在田野信步,发出了把陕北方言留住,把根留住的呐喊,这是这本书书名的由来,也是动机和动力。从拿笔开始,就知道我在从事一件出力不讨好的事。榆林、延安两市在册户籍仅500多万人,别说对13亿汉语人群,对6300多万晋语人群也是区区小数。陕北方言书籍对外人来讲是吓蛮书一本,就是对方言区,从事语言工作的能有几人?吃饱撑的有条件对方言感兴趣的又能有几人?但我关注的不是这。我没能力对方言释疑解惑,但我要努力使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方水土,世代讲这么一种动听、明快、雅俗和谐的语言。也就是说,本书不是试图要陕北人怎样去说话,而是要告诉人:陕北人在怎样、或曾经怎样说话!
(《把根留住——陕北方言成语3000条》,王六著,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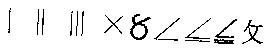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