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界和阅读圈的影响无需赘言,它开启了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对很多人影响至深。但也正因为它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模式,不仅至今仍有毁誉,而且当初出版的过程也经历了漫长的阵痛。
《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书名叫《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年,不重要的一年),早在1976年就完成书稿了,可之后的出版却屡屡碰壁,一直搁浅。在图书出版的商业和学术之间,美国出版界有严格区分的鸿沟,而《万历十五年》因为学术专著和历史通俗读物“两不像”,一直找不到归属。
直到1979年才由耶鲁大学出版社确定接收书稿,并且迟至1981年才正式出版,因为没有及时出版专著,根据美国publish or perish(不出版就灭亡)的学术圈生存游戏规则,再加上所开课程学生选课率低等原因,黄仁宇于1979年接到纽约州立纽普兹(NewPaltz)大学的辞退通知,于第二年夏天离开他供职十年的纽普兹大学。那段时间是黄仁宇的人生低谷期,也可见他当时迫切需要《万》一书的出版。
二
在这期间,黄仁宇也想该书能在中国面世,可巧1978年夏天,他的一个校友要到访中国,他便将部分书稿翻译成中文,托这个朋友带来内地,谋求出版。
这位朋友将书稿托付给亲戚黄苗子。黄苗子先问了金尧如和陈翰伯的意见,金尧如是老革命,当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78年底调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1989年移居美国。他对黄苗子说,稿子能用尽可能用,尽快出版,“这样做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陈翰伯也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当时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代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人之一,他的意见也跟金尧如一样。他们的意见让黄苗子心里有底了,当初的基本意向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书稿是分三次寄来的,稿件1979年到齐的时候,金尧如已经去香港工作了。
当时黄苗子住在南小街,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的灯市西口,相距不远,黄苗子和古代史编辑室的副主任傅璇琮交往频繁,便于1979年5月23日写信给他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将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并附上了金尧如和陈翰伯的意见,以及全部稿件,希望局里研究一下,尽快给个消息。
傅璇琮很快通读了稿件,并于6月16日写了份审稿意见,对书稿整体给予了肯定。但在刚刚拨乱反正的中国,出版《唐代诗人丛考》,前言里引用法国学者丹纳《艺术哲学》里的一段关于文艺理论的讨论,尚且一定要加一句批评,说他没有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而出版外国的新著,还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这是破天荒的,而且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更何况黄仁宇还有“国民党军人”的历史污点。
所以傅璇琮事后回忆:“说老实话,我还有一定的顾虑,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所以在基本肯定的同时,多少提了几点意见,一是“作者因为长期居住国外,受外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因此写作的布局与文字,和国内现在的写法很不一样”,第二点也差不多,说“作者先是用英文写成,后来作者自己又译成中文,但看来作者现代汉语的修养不行”,有些地方“辞不达意”。第三就是“序言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建设的,不好。”最后说“鉴于作者系美籍学者,出不出此稿,可能有政治影响,因此要慎重考虑”,因此建议别的编辑“再审阅一遍,共同商量一下”。
当时古代史编辑室没有主任,于是,书稿交给另一位副主任魏连科审读。9月22日,魏连科拟好审稿意见,和傅璇琮共同签名上报,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在一些提法和文字上做编辑加工。
当时书局还是有领导认为不宜出版外国新著,“何必出外国人的书”,建议“婉拒”。但书局的副总编辑赵守俨在两天后的9月24日即明确表示同意出版,而且提出文字上的润饰,仅“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写法和风格”。这个让其他领导“尽速阅示”的批示意见,最终决定了《万》书的出版。
中华书局版《万历十五年》后来的编辑徐卫东感慨说,上世纪70年代,“中国才从十年内乱里走出来,那时候的眼光没有现在这么开放,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而且此书的作者又是外籍华人,所以在当时出版这本书真是比较大胆的举动了。”
三
图书正式进入编辑状态,新的问题产生了。黄仁宇离国已逾三十年,汉语不仅生疏艰涩,而且不乏陈旧过时、不合语法的表达。在征求黄苗子的同意后,傅璇琮请古典文学专家沈玉成帮忙给稿子做文字加工。沈玉成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傅璇琮的大学同窗好友,1958年因为“右派”政治问题调到中华书局,又和傅璇琮成了难友,一起下过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当时他已经从《文物》编辑部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傅璇琮说,“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选。”
1980年1月,沈玉成将第一章修改完毕,傅璇琮复阅后,以编辑部的名义寄给黄仁宇,附信说明改稿的几条原则:“一,保持原作的论点和材料;二,尽可能保持您原有的文字风格,即文言白话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语言,同时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译文的意味。三、对某些语意不甚明了的,或并非必要的词句稍作删节。四,个别段落稍作调整。”信末提出“润色稿如您认为有不妥之处,请径加改正。”
黄仁宇回信,对第一章的改动表示满意。傅璇琮便于1980年3月22日回信说“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于是沈玉成每改定一章,便寄往美国,如此往复多次,而且每次傅璇琮去信,都先经赵守俨副总编阅改,可见当时的认真和谨慎。
虽然当时润色稿件的基本态度是“尽量地按照作者的行文规则进行润色,不进行较大删改”,但现在看起来,沈玉成的润色的成分其实是很多的,即以第一章一开篇为例,黄仁宇的原稿是:
1587年,为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国无大事可堪铺叙。
当年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疫气流行。山东亦有旱灾。南直隶则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地震。但是这种种小灾小患,因我国幅员之大,在所不免。只要小事不酿成大难,也就无关要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事既如此,我们是否可以即将这一年剔除于历史记载之外呢?
此又不可。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之前一年。当年中国之小波折,实为以前大事之症结,也即是以后各项波澜之序幕。其间关系因果,即为历史。有时表面不重要,而实际重要。并且若干历史家忽视之末端小节,恰为我国特征之所在。
因此我们无妨小事小纪,看他如何开展。首先先看当年阳历三月。
而沈玉成的润色稿、即出版的成稿是这样的: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两相对比,读者很容易看到文字表达上和阅读的流畅程度上的差异。《万历十五年》后来在中国的影响那么大,沈玉成的润色是功不可没的。黄仁宇就在该书序言中提到:“幸经……沈玉成先生……做了文字上的润色修改,又承……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1997年三联书店版《万历十五年》的责任编辑潘振平也说:“仔细比较黄仁宇先生的著作可以发现,《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很典雅,与黄仁宇先生其他著作的文字很不一样。沈玉成先生早年被誉为‘才子’,他后来跟我谈起过在本书文字上所下的工夫。中华书局确实在这本书的编辑上下了很大工夫。”
改稿期间,双方都很认真,比如信函往来详细讨论明代“杖刑”和“笞刑”的区别,书局在1980年6月提出“第七章有一段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认为以删去为宜”,黄仁宇即“遵命删去”,他甚至能发现参考书目中的英文Ricciane校样排错了的一个字母。
就这样反复的邮寄传递,一章一章地润色、修改、定稿,直到1981年6月才基本定稿、发排。当时中华书局考虑到印刷厂日期的限制,和海外邮件往来的时间过长,准备请沈玉成或黄苗子阅定校样,但黄仁宇主动要求看校样,这样,直到1982年3月,最后一部分校样才阅毕寄回,后来又来信修改几个数字。结果,这本18万字的“小书”,经两国作者编辑反复审阅打磨,历时两年半才定稿。其时傅璇琮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正式发稿由北大中文系新来古代史编辑室的王瑞来编辑担任。这样的慢工出细活,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四
1982年,《万历十五年》正式出版,黄仁宇原本是想请老朋友廖沫沙写序言,后来廖沫沙因为健康原因,只题写了封面书名。初版印数27500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于后来在中外学界的巨大影响,也都在作者和编者的意料之外。
新书出版之际,黄仁宇便提出“杀青之日,仍遵原议,著者不受金钱报酬。”只提出希望出版社寄些样书给他,“可以送给海外的学者和留学生朋友。”但样书数量也不必过多,怕“印数不敷分配”。于是编辑部将部分稿费折成230多本样书寄给他,还剩下的780多元稿费,黄仁宇坚持不要。他提出将稿费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但沈玉成执意不收。另一部分给黄苗子和廖沫沙,作为联系玉成此事的“车马费”,黄苗子也没有接受。当时,黄仁宇有个妹妹在广西桂林橡胶设计院工作,黄苗子便问是否能给她一部分稿费,黄仁宇说可以考虑,但在信中说:“如贵局愿付与少量报酬,笔者亦不阻挡,只是人民币三十元、五十元之间则已至矣尽矣,再多一分即与鄙意相违,亦陷笔者于不诚。”当年的君子之谊,竟让稿费领取成了难事。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因为当年中国出版界的版权意识淡薄,这本书在1982年出版时,并没有签署出版合同,纯粹是君子一言为定。直到十多年后的1995年,双方才补签了一份为期10年的出版协议,当时该书已有日、韩、德、法等多个译本,中华书局起草的出版合同草稿还说:中华书局享有该书的“全世界”版权。黄仁宇对此表示了异议,中华书局从善如流,很快重印了合同,事情圆满解决。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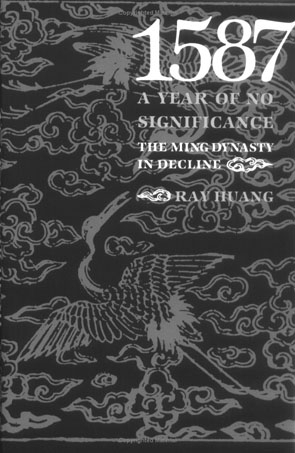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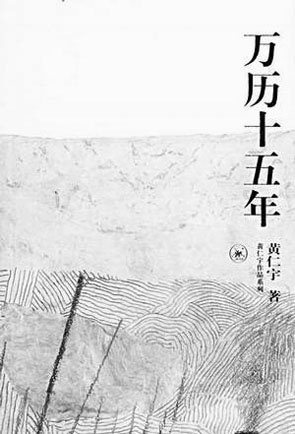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