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大学之前,雷颐曾当过知青、军人和工人。这样的人生经历,曾是那一代人共有的记忆。但与别人不同的是,雷颐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愿意正视和强调这一点。并且,早年的经历也成为他日后学术生涯中不断回溯的精神源头。“一个一直‘钻故纸堆的’为何‘不守本分’而经常如此这般地分析、评论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呢?实因在上大学以前,在本应在教室中读书的年代,‘这一代’却早早被抛向社会”。所以在钻故纸堆的同时,雷颐又总是走出书斋,面对社会现实。“当然,历史专业的训练,使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历史’的眼光来透视、分析现实”。
作为一位具有公共关怀的历史学者,雷颐自觉地将现实与历史连接起来,在对二者互动的理解中,更深切更准确地认清当下,而这,源于其“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考”的立场和思维起点。在新著《历史透镜看今天》和《历史:何以至此》中,雷颐延续其一贯的批判精神,对各种历史和社会现实问题掘幽发微,指陈利弊,所谓责之切,实缘于爱之深,在他平实的文字里,我们不难体会到一种心怀天下,关切民生的济世情怀。
读书报:生活在现代都市,交通拥堵给人们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前段时间,北京市有关部门为了治理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相关的治堵措施,如摇号买车、限制外地人买车等。您2003年即撰文指出交通拥堵与“公共空间”的分配问题,对比今日现状,您当年所谈竟成为现实。
雷颐:在北京居住,交通问题比大多数其他城市可能更早地反映出来,所以,我比较早就思考这个问题,在2003年写了文章。触动我写这篇文章的是一条消息,说北京第200万辆机动车拥有者产生,表明北京开始进入汽车时代,或者说是汽车社会。但是,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和地区,大城市汽车拥有量指标比当时的北京要高得多,但北京却比那些城市拥堵得多。我认为,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公共空间的分配和公民意识的强弱。由于公共空间分配整体倾向于有车者,导致用车成本不高,自然越来越多的人买车用车,因此也就越来越堵。我当时提出的具体问题都是“常识”,其实解决许多问题,只要正视常识即可。
读书报:您认为西方国家预防和治理交通问题的思路和做法是否对中国有借鉴价值?二者间的不同透视出哪些深层问题?
雷颐:发达国家的一些具体做法我在书中有关文章都提到了,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公共空间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比如,限制外地人买车,就像一些大城市为限制房价也限制外地人买房一样,其实是一种对户口本作用的强化,这种做法可能有一时的好处,但长久来看弊大于利。
读书报:“应试教育”的弊端历来为人所诟病。近来,围绕考试制度,又产生了很多争议。您长期关注教育问题,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对此,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雷颐:早在1998年,为了所谓“素质教育”,北京市提出“小升初”用电脑派位。我当时即写文章反对,认为结果将导致更大的不公平。这是有深刻历史教训的,只要不健忘,就应该想得到。再说,现在的“素质教育”就是钢琴提琴多少级、跳舞唱歌画画等等,这些“素质”与穷人家的孩子基本无缘。不以考试成绩而以钢琴等级证书入学,对穷人家的孩子格外不公。穷人家的孩子学费都困难,更别说学钢琴了。他们在困难条件下刻苦学习,还要帮爹妈干活,还能取得好分数,这难道不是素质?但在各种考级证书面前,这都不算“素质”。对素质的曲解,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读书报: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相关部门的“制度设计”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其症结是什么?
雷颐:我一直强调,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许多社会问题不解决而要“教改”单兵突进,必然会越改越坏。社会问题是复杂的,互相扭结,一定要有“路径依赖”的观念。“制度设计”一定要考虑到在社会现实中实行起来的后果。例如,强调素质和各种“加分”,主观愿望当然是好的,是要纠正考试的弊病,但实行起来就是走后门,是对穷人家孩子的不公平。
读书报:多年来,您除了埋头故纸堆做学术研究外,还对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保持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析,获得一大批读者的认同和赞赏。“把历史作为现实的参考”是否可看作是您一以贯之的出发点和立场?
雷颐: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是互动的。对历史理解越深刻,对现实也越看得透。反之,对现实的认识越深刻,对历史也越看得透。二者不是对立的,在许多方面具有同构性,如在某种情境下,“人性”的展现非常相似,对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也非常相似。所以,无论对历史或现实,我一直强调不要“唯文本是信”,不能从“文本”来理解历史,理解社会。“唯文本是信”的人在分析、解决社会问题时,特别容易“书生气十足”,以为按良好的理想制定出一个“方案”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可能问题因此越来越多。前面提到的几年前为纠正应试教育的改革,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历史与现实互动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甚至灾难的教训,现实社会总会有种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时不要找错了“参照系”。
读书报: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吗?历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几年前您的这一连串追问直接触及到了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本质所在。不知道您对此是怎样的回答?
雷颐:这涉及非常复杂的历史哲学问题,哲学家、历史学家争论了几百年上千年也没有定论,一篇访谈也无法展开。当然,我们所说的“历史”是记述下来的“历史”,历史的全部场景已经过去,不可完全再现。但“过去”的部分,总有可能被找到“真相”。如果完全否认这点,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例如,大多数案件都是“事后”破获的,可以说都是成为“历史”后才找到“真相”的,虽然也会存在假案错案,但如果因为这点就认为完全不存在真相,不必也根本无法“破案”,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了。比如,我今天说的话,做的事,到明天就成为“历史”了,就可以以“历史无真相”这种哲学观点否认我曾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如果所有人都是这样,彼此还有“交往”的可能吗?无法交往,就没有“社会”。
本报记者 陈菁霞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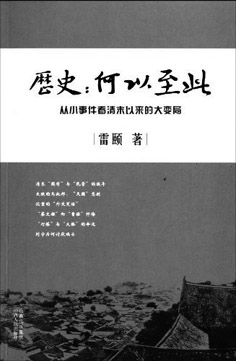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