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和比战难”到积极抗战,从不愿入仕到担任大使,胡适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利用自身影响进行广泛演说,动员欧美各国支持中国抗战,力促美国对日宣战,一位远涉重洋的博士大使,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一书,首次对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经历进行了系统研究与梳理,选取这一特定历史时段,专门介绍胡适不为人们熟知的“另一面”。胡适研究专家、著名杂文作者李传玺数载研读、披沙沥金,为您揭秘——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学者大使之人生传奇。
蒋介石派胡适出使美国,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虽然此时蒋介石没有彻底放弃“和”的希望与外交努力,但主调毕竟是抗战,同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低调俱乐部”的悲观失望以及所要进行的外交方式不同。周佛海在日记里写:8月23日,“十时,希圣谒汪回。据云:蒋先生不愿派宗武赴沪见川越,因其为正式外交官。闻之不胜失望,盖吾辈日来详商结果,均主宗武即赴沪作外交努力也”。8月31日,“希圣接汪先生电话,谓吾辈贡献外交进行方式,不被蒋先生采纳。大为失望”。另外蒋、汪一直是貌合神离。胡适的加入,既壮大了“低调俱乐部”的力量,也给其主张以理论支撑,并以自己的影响带动一个群体对其主张的关注甚至支持。派出胡适,无疑大大减弱了“低调俱乐部”的力量与影响。
对于胡适个人来说,他脱离了“低调俱乐部”,摆脱了其控制。胡适大战前再作一次和平外交努力的观点,同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截然不同。汪精卫等人是彻底的悲观,所谓“和”是放弃底线丧权辱国。比如汪精卫在“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时,曾给胡适这样一封信:“适之先生,我十分感谢先生的指示,我的意见,昨天已对先生说过了,我现在尽我的努力,我只有一句话对先生说,今日之事,最好是国民党以全党殉此最后关头,而将未了之事,留之后人。但有人反驳,国民党有预备好收拾后事的人没有?……这一句话使我十分难过。明日下午四时陶希圣先生约同先生来谈,我现在不写下去了。”汪精卫的悲观情绪可见一斑,刚一开战,就判断是国民党最后的关头,认为一定会失败,全体殉难。虽然胡适在他们的影响下,也曾提出不惜承认伪满,但胡适的思想中毕竟还有着血性与亮色,初上庐山时慷慨激昂,至于外交努力,其前提是必须能抵抗,即和平努力必须以此为基石:其目的是争取时间,即在实现自强的基础上使军事能够充分现代化;其底线是血战到底,即敌人绝不会让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绝不会给我们时间让我们从容地准备,在这种情况下,那就只有奋力一搏。
但这段时间,“低调俱乐部”将胡适抓得很紧,胡适也深受其影响,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将胡适当作了“令箭”。
7月31日,蒋介石约胡适等人吃午饭。胡适向蒋介石进言,请高宗武去进行对日外交。当天周佛海在日记中写:“托希圣等进言,盖渠等以宾客地位,易于说话,不如吾辈部属之受拘束也。”8月3日晚七点,程沧波在中央日报社宴请周佛海、胡适和蒋梦麟等人,几人一直谈到九点才散。几个人起草了一份包括承认伪满在内的“根本调整中日关系”的方案,5日与陶希圣一起见陈布雷,托其转交蒋介石。11日晚七点,曾任暨南大学教务长的杨公达宴请胡适,周佛海和陶希圣等人作陪。几个人又谈到九点多才散。14日晚,周佛海宴请胡适、高宗武等人,一直谈到十点多钟,16日上午十点,胡适、高宗武、程沧波等人来到周佛海家,密商对日外交进行办法,“为此次战争下场之准备。预计3个月后可开始外交,未知能否天随人愿也”。由于日机连续三次前来轰炸,几个人在他家地下室躲警报,胡适等人没走,在周佛海家吃了午饭,直到下午一点半才散。18日,胡适等人游了后湖,回到住处已是夜里,又被周佛海约去,一点多才散。所谈之事是请胡适和陶希圣再去见蒋争取一次,但周佛海日记中又记了一事,“请其在国防参议会约集同志,制订方案,促进外交”。没想到第二天蒋介石见胡适时,却要胡适赴美进行争取支持的外交活动。20日胡适搬到北平路69号中英文化协会住。21日,胡适中年到程沧波家吃饭,下午五点和周枚荪、傅斯年、杭立武等人商议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好大学教育,大致决定两件事:(一)将来各大学教员多余人,可送往边地大学服务;(二)将来宜在内地筹设一个科学工程研究所,以应付国家的需要。八点参加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不知当天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洁食物,半夜胡适开始拉肚子。第二天早晨仍没好转,程沧波、高宗武等人得知后,介绍医生来看,诊断为痢疾,只好到中央医院住院。胡适被派往美国,现在又住院,让“低调俱乐部”一帮人很失望。但他们仍对胡适寄予希望。23日,蒋介石否定了汪精卫等人想让高宗武去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进行谈判的想法。周佛海等人哀叹道:“无已,其待适之赴美经沪时进行与?惟恐时机已失耳。”(本书作者注:可能正是据此,现在很多回忆录认为胡适出使美国是从上海出发的。)胡适在医院住了6天,28日出院。当天下午,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来到程沧波家,胡适也被约来,几个人又就外交问题进行了商谈。30日,周佛海“偕希圣赴汪先生处,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开始外交之理由,并条陈步骤及负责人选;汪允向蒋先生力言。返家后,约适之、宗武商对日外交进行步骤及要点等具体方案,由宗武起草”。31日,蒋介石否定了他们的方案。9月3日,周佛海“与希圣谈,请其劝汪勿灰心,盖蒋先生于公开场所表示,自不能不强硬也。访胡适之,力劝其赴美不如留住国内较有作用,惟蒋先生意旨已决,姑设法进言,如能展缓固妙”。6日,胡适还有两天就将成行,周佛海仍然不死心,又于晚上给胡适写了封信,再作挽留的努力。可见,周佛海等人将胡适抓得很紧,多次约见、访见胡适,商讨对日和谈。他们对胡适寄予了很大希望,一是以名流学者身份向蒋介石进言对日和谈,二是以他的影响在参议会中拉拢一些人制造和谈的压力,三是用他替代高宗武以民间身份与日本进行直接和谈。正因此,当胡适准备赴美时,他们才力劝胡适留下。虽然胡适在“和”的问题上同这些人有本质的区别,但长期搅和在一起,胡适的理性精神再强,也难免近墨者黑。虽然历史没有假设,但我们仍然不能不替胡适叫声幸运,真要那样,最好的结局,也大约像“高陶事件”中的高宗武和陶希圣那样,虽然最终清醒逃出,但仍然染上了污迹。
蒋介石让胡适出使美国,对胡适来说,影响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命运走向。
胡适刚听到蒋介石让他出使的话后,一时想不出自己去了以后能起多大作用。他倒不是留恋“低调俱乐部”,而是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去有逃避之嫌。但胡适很快还是想通了。一是国家抗战大局意识。此前在写给张元济的信中,胡适说:“一家一校在此时都是小事,都跟着国家大局转移,国家若能安全渡过此大难关,则家事校事都不成问题。若青山不在,何处更有柴烧?”二是众人的劝说。8月底,蒋介石面对胡适的犹豫,给胡适以“敦促”;王世杰也敦劝胡适,他对胡适的抗战观尤其是外交观非常熟悉,力劝胡适担此重任;9月1日夜,在中英文化协会的宿舍,傅斯年向胡适进行了一番“哭谏”,力劝胡适下定决心。傅斯年的哭谏对胡适坚定信心起到了催化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胡适在 1942年移交大使事务时,给王世杰、傅斯年等人的信中回忆这段往事说:“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的一哭。”三是他头脑中“战”的思想再次浮出。胡适头脑中本就存在“和”、“战”两种思想。这段时间,他被“低调俱乐部”里的人拖着,自己也提出大战前再进行一次和平的努力,并且为此向蒋介石建言,但胡适的思想中,“战”毕竟是主轴,“和”毕竟是从属的一时利用的手段。当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抗战的氛围,听到越来越多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事迹,他不能不产生一种振奋。8月17日,胡适在汪精卫住所参加第一次国防参议会,得知在那三天中国打下了二三十架日机(8月14日,高志航率领的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对日空军首战即打下日机13架);21日参加第二次参议会,听了马君武、沈士衡等人对上海抗战情况的介绍,当天在日记里他记下了这样的感慨:“甚使人感动。”可能正是这种感动与振奋,胡适头脑中“战”的思想再次浮出且强化了主轴的地位,成了压倒一切的绝对观念。他一扫此前中国军队只能内战不能御外侮的印象;同时也觉得既然全面开战,想和,已经不可能,如果此时和谈,只能是我们求和,将签下更加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可能从此不仅在世界上抬不起头,而且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再无获得民族翻身解放的希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地打下去,直打到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的巨变,直打到敌人彻底的崩溃。胡适头脑中“和比战难”的思想开始明确形成,“苦撑待变”的思想也开始隐隐从付诸实践的角度聚集。
既然不能再“和”,那就让自己走出国门“走向美国”去争取国际形势朝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转变,使中国的抗战获得有力的国际支援。
这段时间胡适还想到了陈独秀,并为陈独秀的被释而奔忙。两人毕竟曾联手树起新文学运动的大旗,如果没有陈独秀,胡适能否写出《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还未可知。无论陈独秀后来走上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胡适在心中一直惦记着他。“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后,虽然胡适没有放弃通过外交手段争取和平的努力,但也知道战事不可能一下停止,万一打到南京来,陈独秀还被关在监狱里,到时该怎么办?于是他写信给汪精卫,请他设法释放陈独秀。18日,胡适收到汪精卫的信:“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胡适收到汪精卫的信后,立即拿着此信去探监。陈独秀此时被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虽然失去自由,又患有高血压,但由于有潘兰珍照料,他竟能安心研究古文字学,身体也不致太坏。胡适有点伤感,但看见陈独秀的精神状态,十分钦佩,甚至还有点欣赏他安心做学问的心境。胡适拿出汪精卫的信给陈独秀看。陈独秀心中充满了感激,由衷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了。”
由于战事紧迫,已容不得蒋介石再在陈独秀身上花什么工夫,司法院院长居正很快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递交了一份“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8月22日,《中央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九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有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有期徒刑三年(本书作者注:陈独秀1932年10月15日被捕,1934年6月30日被判刑)。”第二天陈独秀被释放。1938年10月21日,汪孟邹致信胡适,向他说明了陈独秀出狱后到达重庆的近况,并请求胡适给予关照。“仲甫于7月2日由汉到渝,每月至少两次与我通讯,现住离渝百二十里之江津县东门内郭家公馆,小轮船四五小时可达。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六十高龄,使弟十分悬虑,未能去怀。私意如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逾,因他体气素强,诸事乐观之故。到美之后,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如幸谓然,即请斟酌分别进行,感甚祷甚。”1939年春,汪孟邹再托人从香港带信给胡适,向他说明陈独秀的境况。前一信,胡适刚任大使不久,正忙于借款,没有回信;后一信不知是没有收到,还是那时胡适自己也在病中,又在为修改中立法事交涉,也没有回信。1941年2月25日,汪孟邹再次致信胡适,说到了陈独秀的近况:“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高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是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现住川东江津县黄荆街八83号。”胡适看到这些信后,很替老友着急,便帮忙在美国推荐联系,然后托人带信给陈独秀:“美国一家图书公司,慕独秀先生大名,邀请独秀先生去美国写自传。一切安排妥当,盼往。”没想到陈独秀断然拒绝,“鄙人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传奇的东西,不用去美国写自传。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同时,鄙人也厌烦见生人。”回绝归回绝,但只要一想到两人“五四”时期的合作,陈独秀心中仍然充满了自豪与温暖。蔡元培先生逝世后,陈独秀发表了题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的纪念文章,在给予蔡先生高度评价后,开展议论:“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道德是要躬行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愈落后,愈堕落。”对这段议论,陈独秀引胡适为同调:“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敢说蔡先生和适之先生在这两个问题上和我的意见大致是相同的;适之还活着,人们不相信可以去问他,凡是熟知蔡先生言行的人,也不至于认为我这话是死无对证信口开河。”此文的最后,陈独秀对三人为五四运动作出的贡献做了概括:“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也许陈独秀正是以这种方式对胡适的关心表示着回应。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病逝于江津,29日,陈布雷致电胡适,报告了这一消息。
9月7日,胡适去向蒋介石告别,两个人谈了半个小时。这一次两个人谈得很融洽,蒋介石说要给此时的驻美大使王正廷去电,让他做好对胡适等人的接待,并支持他们的工作。9月8日上午九点半胡适拜访了英国大使馆,会见了参赞布莱克·伯恩,就时局交换了看法,听取了参赞关于英美对此时中国抗战所能给予的支持与帮助的介绍,接着去向汪精卫告别。汪精卫正主持召开国防会议,十一点半才散会,简单交谈中,胡适一改前段时间的观点,开始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十二点又到高宗武家辞行,“只我们二人同饭,久谈”。胡适同样劝高宗武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我们8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胡适在这段话的“未免过虑”和“能”“肯”处都打上着重号。这都表明了胡适思想的切实转变,和对目前战绩的衷心首肯。
胡适对自己这段时间思想转变的轨迹作过概括:“我在8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9月8日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胡适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出发了。
(本文摘自《做了过河卒子——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李传玺著,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定价:36.00元)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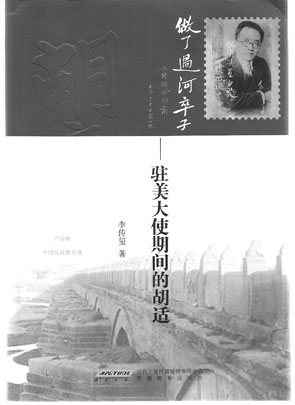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