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15日,在准备就“伊朗门”事件向参议院解释时,凯西突发中风。里根于1987年1月提名盖茨接替凯西。然而,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否决了这项提名。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随后被提名并得到通过,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由其执掌中情局。
韦伯斯特本人并没有受政治争议影响,也缺乏其前任“杀手”般的本能。盖茨仍是中情局的第二把交椅,同时也是苏联问题专家。他仍然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他坚称戈尔巴乔夫没有改变,苏联仍是美国利益的威胁。而戈尔巴乔夫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改革是为了恢复苏联力量,好更有力地对抗美国。
1987年12月,凯西去世的一年后,封闭的俱乐部——“意识形态情报”60位最突出的成员在国家战略信息中心的支持下碰了面。其中包括往届和当今政府的高级官员、情报官员、特工、分析师、学者、媒体、商人、国防部代表、总统外交情报咨询委员会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情报委员会的成员。
这次重大聚会是为了审视情报机构在“这一困难时期”的职责和功能。尽管聚会出于专业意图,但是结果却变得很政治。会议反对里根总统急切签署裁军协议,会议摘要最后写道:“虽然苏联面临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仍将在战略层面的若干领域变得更强。”会议还预测,在大多数与西方产生摩擦的领域,苏联将具备军事上的抗衡能力。苏联还将通过隐蔽行动和特殊手段增强外交和政治实力。
1987年年末,当美国情报机构精英在讨论苏联帝国的威胁能力时,多年来似乎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政府表面出现了裂痕。那一年1月,莫斯科大学校长把苏联形容为一个“滑向深渊”的大国,不过他也表示还有希望阻止颓势。这篇演讲发表于《真理报》,让苏联问题专家颇为惊讶。随后,莫斯科很快放松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87年2月2日,苏联政府开始释放数十名政治犯,允许他们回家,其中包括成为世界反苏异议分子代表的核科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
政治犯的释放潮引起党内守旧派和强硬派的憎恶,他们认为这种“松裤腰带”的行为会危及自身利益。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未退缩。在2月末一次集会上,他发表演讲,捍卫自己的政策:“民主并非与纪律背道而驰……民主并非与责任背道而驰……民主并非与秩序背道而驰。”他还严厉批评了党内官僚主义,认为这是造成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几天后,戈尔巴乔夫决定把话扩散出去,电视节目播放了他的演讲。
接着,苏联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公开分歧,克里姆林宫内文官和军官发生公开冲突。一位19岁的西德年轻人马赛厄斯·鲁斯特驾驶飞机从赫尔辛基飞往了莫斯科,轻而易举地躲过了苏联的防空系统。戈尔巴乔夫利用这次事件开除了他最强硬的反对者之一国防部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这一举动被解读为是苏联在对外昭示,文官地位在军官之上。这也是戈尔巴乔夫首次与军方掌权派发生冲突,且迅速得胜。
很快,戈尔巴乔夫开始限制克格勃权力,并准许对该机构进行公开指责。要求克格勃在法律框架下运作的声音也迅速出现。
在国家战略信息中心支持下会面的“美国情报俱乐部”成员却没有讨论苏联此次事件的影响,也未讨论美国情报机构没能感知苏联愈演愈烈的危机以及苏联红军的糟糕状态问题。他们关注的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弱点,可能“伤害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的意愿和能力”,据会议组织者之一罗伊·古德森教授说。敌人正在他们眼前崩塌这一事实并不在会议议程上。“大部分时候,”古德森说,“我们情报机构的政治和军事评估都太学术了,脱离了决策者的需要。”
正当国家战略信息中心举办会议时,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峰会也在华盛顿召开。会议结束前,两位领导人签署协议,要销毁欧洲所有短程和中程核导弹,两人还宣布愿意将协议范围扩大到洲际导弹。
峰会气氛其乐融融,这是14年来苏联领导人首访华盛顿。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私人纽带增强了。“我是罗(罗纳德的昵称),”里根说。“我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回答说。里根热情地招待了他的客人,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乘车穿过华盛顿街道。在访问期间,戈尔巴乔夫邀请美国公共舆论塑造者参加座谈,期间他谈到苏联以及与西方关系的新时代。“令人印象深刻,”参加会谈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道,尽管他一年之后才加入政府。“这次会议旨在给我们留下一种印象:我们没什么可怕的。戈尔巴乔夫知道怎样表现出西方作派以迎合观众。”
在苏联使馆庆祝戈尔巴乔夫来访的鸡尾酒会上,戈尔巴乔夫说,“美国和苏联必须重新思考他们的关系。”随后他直接转向坐在观众席的亨利·基辛格,问道:“对吗,基辛格博士?”
作为美苏缓和的“产婆”,基辛格知道这个“孩子”已经会走路了。但是现在却有一个切实的危险,即里根可能会选择过早地销毁导弹武器库。作为对戈尔巴乔夫的回应,基辛格有礼貌地笑了,顺势点了点头。
“您怎么看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一位记者在酒会后问基辛格。“很有意思,”他简练地回答。当记者要求这位外交魔术师再具体一点时,他回复道,戈尔巴乔夫的回答要比提给他的问题好多了。
早在1989年,盖茨征得老布什同意,在国安会框架下组建了一个绝密的紧急计划小组。康多莉扎·赖斯被任命为协调员。其他成员诸如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弗里茨·伊玛诗、中情局的罗伯特·布莱克韦尔、国务院的丹尼斯·罗斯、五角大楼的埃里克·艾德曼,国防部部长切尼的助手保罗·沃尔福威茨则偶尔出席。组织这批人马是为了研究苏联剧变对美国的影响。比如说,如果苏联政府被暴力推翻,那么那些核储备会怎么样?还有,如果华盛顿得知苏联有人计划政变该作何反应?那么这个小组基于什么进行评估呢?对于这个问题据说赖斯如此回答道:“我不需要中情局就能知道那里的情况有多糟糕。我看《纽约时报》就知道了。”
老布什看《纽约时报》,但很显然也会看情报材料。詹姆斯·贝克也是如此,他在苏联崩溃期间负责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他们却对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情报材料视而不见。遏制政策之父乔治·凯南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老布什总统对苏联的勇敢举动“反应不够”。
罗伯特·盖茨那时仍在国安会等待被任命为中情局局长,他在达拉斯演讲时回应了凯南的说法。盖茨声称美国“仍需与苏联进行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当有人问他,苏联陷入危机时,是否有必要伸以援手,盖茨回答得干脆利落:“没有。”
1989年五角大楼的报告间接支持了“苏联毫无变化”这一判断。这份报告对某种幻想提出了警告:
确信东西方关系出现剧变的想法必须经过审慎考量……苏联仍然通过外交和金融手段削弱西方以扩大自身影响力和实力,并且向与西方为敌的国家和活动提供军事援助……“新思维”没有制止戈尔巴乔夫把对尼加拉瓜的军事援助从1985年的2.8亿美元提升至1988年的5亿美元。军事援助继续成为苏联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借此保证硬通货流动性, 同时保证握有政治影响力的杠杆。
1991年6月12日,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首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政府都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美国将如何对待新形势,即如何对待俄罗斯联邦的独立和叶利钦本人。叶利钦在俄罗斯及其他想脱离苏联的共和国中人气很高,他似乎已冲上一条不回头的道路,基本上已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鑣,也就是与苏联中央政府毫无干系。1991年6月,中情局苏联事务处发布了另一份文件,负责协调苏联国内事务评估的格雷·霍内特认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力量已经团结在叶利钦身边。
叶利钦当选后不久于1991年6月访美。华盛顿还没想好如何在政治层面对待他。罗伯特·盖茨一直认为,戈尔巴乔夫内心仍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相信他的改革承诺。在国安会,盖茨建议总统给戈尔巴乔夫的对手叶利钦以国家元首待遇。老布什总统面临的僵局是,给叶利钦国家元首的礼遇等于打戈尔巴乔夫的脸,戈尔巴乔夫还在莫斯科苦苦维持着苏联统一。外交手段总能解决各种尴尬情况,但戈尔巴乔夫是能带来真正好处的人(裁减苏联军事和战略资产),而叶利钦在战略事务上的立场还不得而知。唯一明确的是,他钟爱酒精。
解决的方法是两边都不得罪,既对戈尔巴乔夫信守诺言也不疏远叶利钦,这一招在1989年叶利钦硬闯华盛顿时也用过。于是,叶利钦将与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举行官方会面,老布什总统会“意外地”造访斯考克罗夫特办公室,并参与这次会面。
华盛顿未及时发现苏联内部权力均势的变化,在1991年夏,美国的主要担忧是如何阻止苏联武力制止其加盟共和国脱离,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中情局一份分析局势的文章估计,戈尔巴乔夫在背后支持对波罗的海三国起义的镇压。一些情报显示,戈尔巴乔夫开始采取应急执法行动以阻止分裂势力。老布什的困境是,是要对这一趋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戈尔巴乔夫维护苏联统一,还是要暗暗鼓励分裂势力以增加苏联的不稳定,而这将加速戈尔巴乔夫的倒台。
乔治·柯尔特回忆说,当时描述戈尔巴乔夫内在虚弱、政策不得人心、政策蕴含风险的情报报告“被政府外交决策者完全忽视了”。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中情局局长韦伯斯特都觉得有必要公开维护其分析人员。
就在叶利钦6月当选俄罗斯总统后的五个月后,戈尔巴乔夫被迫离开克里姆林宫,这里将成为俄罗斯政府的总部。然而,直到他最后下台,老布什政府对待苏联领导人的方式好像都没有任何改变。
(摘自《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1980-1990: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月版,定价:9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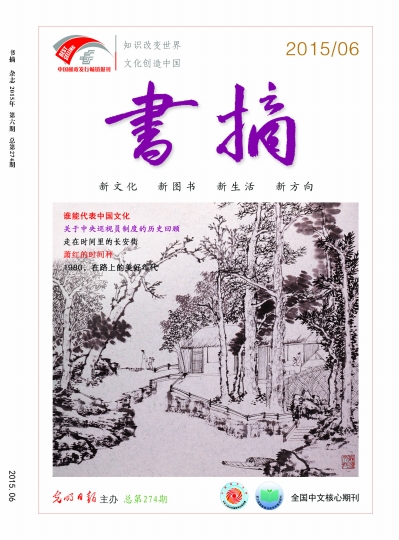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