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东方禅宗记载着这样一段广为流传的公案,徒弟问师父:“老师,我们如何能够战胜死亡?”师父回答:“学习好好活着。”徒弟又问:“那么,老师,我们怎么才能学习好好活着呢?”师父玄而又玄地回答道:“只要你能战胜死亡……”
这段有趣的对话很好地概括了自人类物种出现在地球上以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这个两难悖论的精髓:既然人生无一例外地终结于死亡,如何为其寻求意义?作为哲学和宗教这两大体系的核心推动力,这个明显透着存在主义色彩的问题占据了几千年来几乎所有伟大思想者的灵魂。柏拉图、圣奥古斯丁、但丁、笛卡尔、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这些人的思想之所以能够穿越诸世纪的重重迷雾影响着今天人们对于生命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于人类面对死亡状态的深刻思考,能够印证我们对于自身存在的脆弱性所感受到的疑惑。
我们总会自问:自己在世界上如匆匆过客般的一生是否有任何意义?有这样的疑问是很正常的,作为如人类这样的“理性动物”,总是会不断探究周遭世界中一切自然现象的意义。“生而为死”这件事儿,看上去是决然不可理解的,零和无用,且不合逻辑,在不得不承认其作为自然规律的绝对合理性的同时,困惑和焦虑的感觉依旧萦绕不去。经常会听到类似“死亡是人类唯一的共同点”的说法,那“手持镰刀,身材颀长的大收割者”无差别地袭击任何人,丝毫不问你是衣不蔽体还是富甲天下,天纵英才还是浑浑噩噩,国际巨星还是籍籍草民。从这个角度来讲,“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同样不容否认的现实,算是在自己临终或是失去生命时可以得到的一点微末的慰藉。
自从20万年前“智人”种族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已死亡的人数约以十亿计。单就数字来看,这似乎只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快而又老生常谈的现象,但是,其中每一次哪怕再无足轻重的死亡,都是一个悲剧,标志着一个独一无二的鲜活人生就此终结,在死者及其亲人的眼中,他的生命与你我的生命同样值得珍惜。死亡无疑是自然秩序的体现,但也是我们每个人最终要独自面对的终极试炼。请试想一出结局已经给出的戏剧,我们作为演员和作者,每天都要为之填进一个场景,还要费尽心力,按照合理的逻辑为它理顺一切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到最后一幕完结,大幕尚未完全拉下之前,我们都在尽自己所能试图理解那早已注定的结局,给这美丽故事的生硬结尾赋予意义。因此,为了赋予人生意义,有时我们不得不先为死亡找到某种意义。
尽管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布满了对于种族演进贡献突出的里程碑(如工具的发明、火的控制、语言的创造等),但说到现代意义上的人类(智人)诞生的最有力线索,公认的标志是原始葬仪的出现。从这些距今足足十万年的穴居人的墓葬里明显体现出的仪式中,我们除了可以见证死亡引发的焦虑之外,同时也发现了人类试图对于死亡的意义进行解读的最初迹象。从最早的遗迹开始,很多这样的墓葬中即包含了让死者重生的元素,如将尸体摆放成胎儿的体位,希望可以重现子宫的生育能力,或是将尸体涂成可能是代表着维持生命的血液的赭红色;以及在墓穴中发现的如陶器、武器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用来保证死者重获新生之后仍然可以成就彪炳。对于“如何战胜死亡”这个问题,人类的最初反应似乎是寄希望于生命不会在世界上短暂存在之后就告终结,这种愿望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并通过不断地创造愈发复杂的葬仪和宗教符号表达出来。尽管这些宗教仪式在岁月的长河中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异,但从根本上,对于如何面对死亡焦虑的探询中,无一例外地传达了同一个信息:人间的生命只是一个阶段,只是一个更加长远的过程中的一个可见的部分,那么在人死后获得重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了。
某位亲友逝世时,我们总会突然变得手足无措。像父母、祖父母、叔伯辈这些老年人,还包括所有在我们童年时期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其他长辈们,即使他们得以长寿善终,即使我们早已默默承认他们的逝去完全是顺应自然,他们的过世仍会是一次带来巨大悲恸的事件。像朋友、伴侣、同事、同学,这些仍然年富力强的人们的消逝,带给我们的则是更令人难以接受的震惊,以及对不公命运徒劳反抗的纠结情绪折磨。而最残酷的死亡,就是拥有无限美好未来的孩子的夭折,这是大悖自然之理、决然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的事情,在心里留下的深深创痕,即使是时间的流逝也终无法令其完整愈合。正因为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死亡是一个可怖又残酷的事件,永远在暗中窥视威胁着,它会永久剥夺我们与生命中珍贵的人相处的机会,所以正如拉罗什富科在17世纪时所说,“死亡如同阳光,都是无法逼视的”。
如果说为了身边人的亡故而落泪并珍重关于他们的回忆,是我们人性中最崇高部分的表达的话,那么由我们自己的死亡而引发的焦虑,可是种毒害生命的实实在在的负担。实际上,死亡所引发的恐惧中,最大的一部分都是来自于对我们自身的死亡的畏惧,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关于死后生命之延续,死亡仍然总是被视作交流的禁区,至少在提到的时候会特别小心措辞,尽量保留,这就有点儿像弗洛伊德曾说过的,我们在潜意识里抗拒关于自己死亡的念头。在我们看起来,造成这种不安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对死亡这个概念缺乏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死去?我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都会发生什么?令人迷惑的是,尽管世间每一种宗教、每一次哲学思潮,都无一例外地对死亡进行了心理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玄学层面的深度探析,但我们绝大多数人即使对于生命过程的机理都知之甚少,更遑论引致死亡的那些关键事件。我们很难真正地领会,人的生命是何等机巧乃至难以置信的一次经历,很难想象将拥有生命这一惊人事件的本原追溯到三十亿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一个原始细胞。另外,我们并不晓得死亡本身并不是一个错误的结局,更远非生命的不义不公,而是生命演化到我们这个种族出现在地球上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环节。这种认识的缺乏很令人遗憾,因为不管这听起来多么自相矛盾,但更好地理解死亡,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生命,更有助于我们充分地珍惜这永恒中脆弱而短暂的一瞬:在这一瞬之间,我们拥有无限的权力,去活着。
(摘自《活着有多久:关于死亡的科学与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1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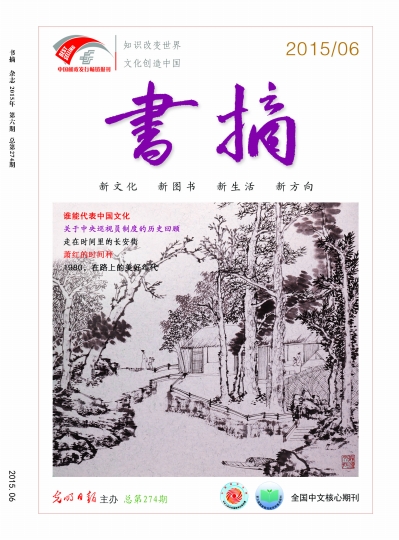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