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的资深编剧梁秉堃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刚刚走入直播间的时候,我还有些担心他的状态,但当那些往事流淌出来的时候,我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在话筒前他打开了六十年的记忆,说着那些人,那些事,让我重温了前辈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人艺有两个地标性建筑,一个是史家胡同56号家属院大楼,一个是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一个是演戏的地方,一个是休息生活的地方。
说起人艺,还有老人艺和新人艺之分。老人艺的成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没几个月,应该是1950年,那时候演了一部戏叫做《长征》,李伯钊写的,于是之演的,很轰动,从那以后老北京人艺就成立了。老人艺的节目包含歌舞、杂技、话剧几大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52年,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这时候有一位领导提出来,要建立一个专业的话剧院,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就演戏剧,而且是演女角,因为那时候男人演女角是很普遍的,女人根本不许上舞台。总理形象很好,他演了不止一个戏的女角。他还是南开新剧团的副部长,曹禺也在那里面演女角,所以总理老管曹禺叫老同学。
后来我们就问曹禺:“你跟总理是同学吗?”他说:“那是总理客气,他比我们大得多,但是我们是校友。”总理当时也写了关于新剧的文章,曹禺很赞成他的主张。举一个例子,新剧要担负社会责任,这是当时总理文章中写的,曹禹实践当中就是按这个做的。所以总理点名建议由曹禺来做话剧院的院长。
周恩来对人艺是非常的支持的。有一次看完表演,接待完外国友人之后,他主动提出要到56号院看一看。梁老先生记得很清楚。
他问我们平常上班走多长时间,我说走15分钟。他的车就停在楼下,那时候已经凌晨1点钟了,但他坚持要和我们走走。沿路就是聊天,比如问我们拿多少钱,还问剧院演戏卖票多少钱。我们说卖一块钱一张。他马上就想工人现在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大概是60块钱,他说你们这个票价还可以。他在考虑工人是否买得起,他考虑得很细致。后来谈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年轻人一定要经受风雨的考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指着我们厅里的一盆海棠花说,你们可不能学海棠花,你们要经风雨,以后的任务很重。他这次来,所谓的散步和谈心,是有目的的。
曹禺和老舍先生都是梁秉堃的老师。梁秉堃1954年来到剧院,那时候十八岁,在人艺做了很多事情,做过灯光管理员,还做过演出处的秘书,做计划、总结、组织工作,再往后就做了演员。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人家说我们剧院是“郭老曹剧院”,就是演郭沫若、老舍、曹禺的戏比较多。郭老曹那时候年事已高,于是剧院就开始找接班人,我就在其中了。
找接班人就是培养编剧。当时我就找老舍先生商量,我说您看这活我能干吗,他说你别一棵树吊死,多搞几样,你年轻,你完全可以改行。于是,院领导就把我正式调到文学组,改做编剧了。
说到这里,我还得说说我另外一位老师——曹禺。虽然曹禺是院长,但是他本身是剧作家,所以他分管剧目,特别是创作剧目。曹禺老师管得很细。每次我们出去采风回来,他都特别喜欢听我们说,一听就没够。因为他当时兼职太多,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出去采风,所以就希望我们年轻人出去多跑跑,回来说给他听。他还教我们一个搜集素材的方法,那时候我去工厂多,他就告诉我,到了一个工厂,先问厂子里谁最能聊,这个很重要,先找能聊的,通过这种“大嘴”了解工人们的生活。
曹禺老师教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打听厂子里最近出的新鲜事。后来我想,这实际上都是曹禺老师一辈子的经验。我觉得文学大概就是这些,就是写特殊的故事,你要是写很普通的故事,没有传奇性,就吸引不了大家。
曹禹老师说的这两条并不见得在哪儿写过,但是很实用。后来,于是之当我们院长以后,我们还继承这个传统,下去采风的时候让最能说的人放开说,我们选素材。我们给曹禺老师起了一个外号叫“神枪手”,他真是大师,他对戏剧的结构、组成、语言、故事、人物实在是熟悉。
梁秉堃是非常幸运的,能得到曹禺和老舍两位大师的亲自指点,获此待遇的全中国都没几个。
我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个相声,叫《查卫生》,就是老舍给我改的,而且是老舍给我推荐发表的,这使我终生难忘。在这方面他大有学问了,改到什么程度呢,他把我的语气助词都改了。比如说有的地方我用的是:‘啊’,他说你不如用‘喽’,他说‘喽’响亮,‘啊’往里收。按说,换成一般人,对这些事都忽略不计了,因为是助词。他却那么认真,对年轻人特别爱护,手把手教。我再说一个例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们都管他叫舒先生,不叫他老舍先生。有一次我问:“舒先生,您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好台词的条件是什么?”我就是想偷师。他告诉了我四句话。第一句话,说着上口。演员说你的台词的时候要上口。现在有一些句子太长,演员说起来很难,而且里面净用些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拗口的词,演员说起来就找不到感觉。第二句是听着入耳。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我到现在为止都觉得很难。第三句话很重要,是容易记住。你看经典台词都是容易记住的。第四句我觉得更精彩了,是不忍心把它忘掉。他的剧本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茶馆》里他写的抽大烟的那个唐铁嘴。‘英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够福气吧。’我当时就问他,先生您这个是怎么琢磨出来的。他就说:“‘英国香烟,日本白面’是生活里面有的,第三句‘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够福气吧’是我编的。”他解释了一句说: “这样无耻的人就得说这种无耻的话。”这种学习,恕我直言,比大学课堂里亲切得多。
我写台词的时候就想起这四句话,真是终生难忘。我再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茶馆》里有一个马五爷,一直在茶馆一个人坐着喝茶,一句话都没有。二德子和常四爷在里面冲突起来了,就是为了几句随便的话。这时候马五爷站起来了喊了一句:“二德子,你威风啊。”就这一句话,人物出来了,了不起。咱们写六车都不一定出一个人物。他之所以能做到,一是熟悉,二是技巧太高明了。这里有一个故事。当初我们演二德子的人,按现在的话说,也是腕儿,就是童弟。童弟演的时候嫌自己台词少,他就这么一句“二德子你威风”,他觉得少点,他说干脆我加一个字,改成“二德子你好威风”。他也没跟导演商量,因为导演没发现。他就这么一直演下来了,等到“文革”时,我们的戏被批为“大毒草”。后来四人帮垮台了,我们又演这个戏,童弟悟道,他多加这个字是错的。有这个“好”字是允许威风,要没这“好”字是根本不允许威风。十多年以后他自己悟出错了。
梁秉堃的讲述依然带着崇敬的口吻,他觉得剧作家的语言应该经得起推敲,而且简练。这跟剧作家大量体验生活、注意观察并且海量阅读有关系。梁秉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英若诚,也就是英达的爸爸,曾经在清华学习。他去清华图书馆找文艺方面的经典来读,后来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本经典都被两个人借过,一个是万家宝,也就是曹禺,另一个是钱锺书。
说到读书,不得不提一个演员,就是于是之,梁秉堃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半师半友。于是之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我读书受谁影响最多?就是于是之。在60年代初期,我们在一个组写剧本,他问我,你看什么书。我说很杂,没什么计划,碰上什么就看什么。他说我给你出一个招,你一个礼拜看一个经典剧本,不仅仅是外国的,也不仅仅是是中国的,古今中外的都要看。我很爽快地答应了,觉得应该很容易。一个礼拜七天,看一个剧本,一般的剧本都是五万字以内,两三万字的比较多。我觉得不成问题。可是等我看起来以后,我觉得这事可不简单,因为你不是欣赏,你是学习,你还要记笔记,这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是好的剧本看一遍是不行的。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他给我定了比较好的学习指标。如果我现在还有点底子的话,就是那几年打下的基础。你想一年五十二个剧本,而且还是经典的,三四年就是两三百个剧本了。我还真是坚持下来了。我常常在看了一个剧本之后跟他交流,他指导我那个本子好在哪儿,这个为什么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他给我做分析,因为这些书他基本上都看过。这也很重要。
人艺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爱读书。提到读书这件事,曹禺说:“人艺首先是文学院,成员不读书怎么能成文学院,你们的知识面必须广,知识底子薄的人不能写出好的剧本,也不可能演出好的角色来。”
记得海明威曾经说过,你写的作品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言外之意就是八分之七全都在下面,而读者能够通过露出的八分之一感受到藏匿部分的力量。七十多岁的梁老师还一直坚持读书,曹禺院长对人艺创作人员们的要求正是如此吧。
(摘自《听说》,译林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定价:36.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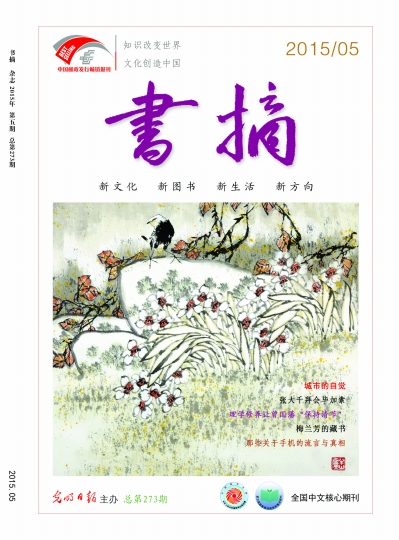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