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生喜爱养花,什么花都种。那时,我家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说是个四合院,实际上是一个大杂院。原本,那是个大户人家的庭院,弟兄三人,就前后贯通地建了三座小四合院。解放后,大户人家迁走了,四合院就膨胀起来。由于当时北京人口骤增,民用建筑又跟不上,于是,便都在四合院里搭建起一排排砖瓦小平房来。特别是唐山地震之后,这种临时搭建的筒易房就更多了,把来往的通道都挤得仅可容身了。好在,院子当间还留出一个小小天井,于是人们便各自在自家窗前栽种起花果草木来。母亲更是一马当先,一则是她喜欢养花,二则是我家占得地势,住的是向阳北房,阳光充足,窗前的空地也比较多些。
母亲什么花都种。不过那时条件差,也没有什么好品种,更不要说什么名贵的花草了。我看看摆在窗台上的,都是什么玉簪棒、绣球花、骨刺梅、指甲草、玻璃翠等平常的花,而最多的是死不了。这种花不娇嫩,插到土里就活,不择瘠土,不用上肥,怎么着都能活,而且是一年四季花开不败。
最喜人的是,母亲在窗前空地上栽种的那些爬蔓的花儿。这些花儿好莳弄,只要在小小的空地上挖个坑,撒下种子,然后在不占地方的空间里横竖给它搭上几个架条,它就不停歇地向上伸展着,在你不经意间,蓦然回首,就已经是绿叶满枝头了。再过几天,它就好心地为你搭起一座遮阴的棚架出来。
棚架能够遮阴的时候,也正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季节。每当歇晌之后,或者是傍晚时分,人们都爱坐在瓜棚豆架之下,一边手里做着家务活,一边闲唠家常。地上落着叶间碎影,架上爬满小果小花,坐在下面十分惬意。母亲是个大能人,虽然一天书没念,但却能够讲南朝道北国的,历史上那些演义长篇,她都能成本大套地给人讲述出来。院子里的老奶奶、大妈和孩子们,每晚都圈坐在棚架下,有滋有味地听母亲讲故事。人们一边听,一边称赞说:“这老太太,记性多好!什么都知道!”“若是搁到今天能够念书进大学,早就是一个老教授了!”听到人们这么说,母亲心里更加得意,故事讲得就更加有根有梢,有枝有蔓的了。
母亲种的爬蔓的花品种很多,有喇叭花、窝瓜,丝瓜、爬墙虎、梅豆角等,大多数是既可看花,又能吃果的。最有意思的是葫芦。它跟其他爬蔓的花一样,也是地面上不占地方而在空间长得密密实实的。藤上开着白色小花,镶嵌在圆圆的翠绿叶子中间,煞是好看。人们坐在葫芦架下,总比坐在其他什么棚架下面觉得更有些韵味。不然,元散曲中怎会有“闲来几句渔樵话,困来一枕葫芦架”的诗句呢?待到初秋,架上结满葫芦时,就更是喜气盈人了。一个个小葫芦排着队,仨一群、俩一伙地随风摇曳着,谁走到跟前都要踯躅止步,又看又喜,恨不得咬下一口咽到肚子里去。霜降以后.葫芦长成了,山鸭青色变成鹅黄色,用手指轻弹一下,里面便发出悦耳的响声。这时母亲就更忙了,摘下葫芦一个个地送人,大的送给大伯、大娘切开作水瓢,小的送给孩子们作玩物。大杂院里孩子多,二虎、三虎、老五、老六一大群,每个孩子手里捧着一个。小姑娘用它做贮钱罐,那帮小小子则用它捉蛐蛐,装蟋蟀。没事的时候,总是举起葫芦放在耳边,听里面小虫儿唧唧的叫声。
孩子们喜爱那葫芦,就跟捧着个宝葫芦似的。每当外院孩子馋羡地问他们是从哪里弄来时,他们总会骄傲地说:“是我们院里的邓奶奶给的,她家房前结好多好多的葫芦!”母亲听了,心里更是高兴。第二年种得更多了,外院的孩子也能分到一个两个。
母亲为什么能够招得那么多的邻居,特别是那么多邻居孩子们的喜欢呢?不单是因为母亲会讲故事,常在花阴下召开又风凉又有情趣的故事会;而更主要的是,母亲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她的心肠比谁都热,她的同情心比谁都宽。邻居们谁的家里有了事,她会跟那家人一样从早到晚地挂记在心里,跟着人家一起费力与操心;谁家的孩子生病了,她会跟那家人一样不时地走过去提醒他们按时给孩子吃药,或者是抱到医院里去打针;谁家要是有闺女出嫁或是小伙子娶媳妇,她更是比那家人还高兴还忙活,白天黑夜一遍遍地走过去帮忙。
母亲的性格,是很达观开朗、乐观向上的。感受最深的,莫过于过年过节的时候了。每当到了大年根底下时,她总是早于其他的人,张罗着筹办过年的事。人们一见到她一大早起就乐呵呵的那股忙活劲儿,无不受到传染,感受到日近一日、时近一时地扑面而来的过年气氛。人们虽然受苦受累一年了,甚至是忍饥挨饿地度过一年了,可是这个大年却总得要过好,总要过得有滋有味的。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这个大年,给我们的苦和累带来一点安慰和补偿。而更主要的是为着来年,为着能够给来年种下一片希望,一片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争取得到的美好希望。
母亲常这样对人们说,便也总是这样带头去做。一到腊月二十几,她便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褥子都叠好,把屋子归置得整整齐齐之后(不管怎么穷,她总是喜欢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便风风火火地张罗着怎样糊窗户,怎样糊墙。窗户纸是要崭新的,糊墙的纸要雪白的,这些东西她早就预备下来了,是她靠卖废品积攒下来的钱买的。由于她那么热心,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和做子女的子女的人们,便不管怎么忙也得赶上前去帮助她一起来干。因为她是小脚,那登高爬上爬下的事,便只能由别人着手。她便站在地当间作为总指挥,指点着人们这一张纸要往哪儿糊,那一张应当稍高或稍低一些。缝儿没对整齐的,有一边露角的地方,她一定要你揭下来重贴,质量关她从来都是把得严严的。邻人们过来看了看,都说:“看人家邓奶奶,窗户像窗户,墙像墙,弄得满屋子都亮堂堂的,这才像个过年的样子!”
母亲听了,心中自然更是高兴。于是,接下来就按照儿歌中所数落的那一套,什么“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糊香斗;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杀只鸡”等等,一样一样地来置办年货。虽然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所限,不能够都置办到,但她总也要想尽办法应个景儿。割年肉,还好办,尽量在二十六那天排着长队把早已积攒下来的肉票拿出来去割年肉。可是二十七杀只鸡,就不好办了,到哪儿去弄那只鸡呢?可是母亲偏能想出办法,用面捏出几只小鸡来,蒸馒头时放在锅里一起蒸。晚饭时,大家会惊喜地看到有几只小面鸡摆在自己的面前。
母亲的手很巧,不仅是针线活儿样样都拿得出手,而尤工于苇席编织。不论是屋子里铺的炕席,还是店铺里用的茓子,她都能编,而且编得又快又好。那些三、六尺长的小席子,一天能编两个;丈二尺长的大炕席,稍微贪点黑儿也能织出一领来。伪满期间,父亲为了躲避鬼子抓劳工,多年逃亡在外,一家人全靠母亲编席子度过那艰难岁月。好在母亲织的席子好,逢到有结婚办喜事的人家,她还会格外用心地给织出一些吉祥如意的花纹来。
要问,母亲肚子里的那些民间文学和为这民间文学所支撑起来的乐观向上精神,都是从哪里来的?说起来可能有人还不大相信,她肚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来自她天生的禀赋——好记性!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正是家境极为困难的时候。母亲白天织席子养家糊口,一天忙到晚已经累得够呛了,但是一到了晚上,她却偏有浓郁的兴趣让我给她读那刚刚从邻居家里借到的一本《薛丁山征西》。因为没钱生炉子,屋子里是很冷很冷的。坐着读不行,只能全家都躺在被窝里听我来念。念的时间长了,我伸在被窝外拿着书本的手冻僵了,抗不住劲了,便由母亲接过书来举着让我念。她举的时间长了也抗不住了,便由睡在我身旁另一边的二姐接过来捧着。冬日里天黑得早,我们这种被窝里捧着读书的接力棒,有时甚至一直传递两三个小时。
母亲给我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母亲是我真正的老师,给我的东西,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无尽无休的,都是永远也诉说不完的。我的母亲,我永远忘记不了的母亲,她应当是:
“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也是我永世的一个启蒙老师。”
(摘自《北京文学》20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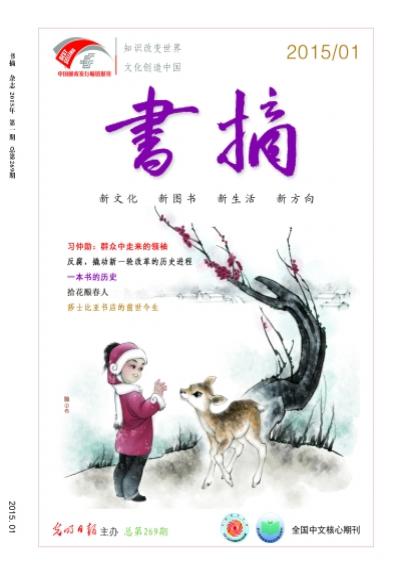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