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僚们在一旁大吃大喝
饥饿已经临门。大饥荒的阴影,原是早在地平线上出现了,到一九六〇年,不经意间,已经覆盖到北京的天空。
不久以前的反右倾运动里,已经把唠叨几句物资紧缺的人批了个三魂出窍,这时候谁也不敢说不够吃。粮食定量没减少,但没有油水,消化就快了。我在广播学院上辅导课,是十点到十二点,一般从十一点起,站在讲台上两腿就软了,发抖,一直抖到下课铃响。
但我像中国老百姓那样,习于自我安慰,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明天就出发,到良乡“十三号工地”去种菜!
“十三号”,这里已经不是工地,这里是一座广播发射塔。铁塔下面和周围,围墙圈起了大片的禁区。像北京各中央机关都在搞“生产基地”一样,这里也成为广播局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夏至将届,正是种菜的时令。为什么种菜,还用说吗?补机关食堂蔬菜之不足。这就表明,我们是为自己种菜(那时候远远不知道食堂管理科在每个集体户口人员身上,每天克扣一两粮食!)。大家还是振奋的。我在大家提议下写了《种菜突击队之歌》,中国音乐组的张定珠立即谱出曲来,然后每天就唱着这支歌下地。“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陶渊明只管莳弄庄稼就是,我们却还要面对……人事。
我不知道这个“十三号工地”的管理人员是哪一级干部,但想来应属技术管理性质,它在业务上应该主要服从于技术部门的领导。但因有了“生产基地”,常来常往的却不见局里技术部门的人,而是总务行政方面的人飞车来去。有时也有一二名列领导的人,来了可并不跟种菜种粮食的一般干部见面,直接去“办公”。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我家先祖召公在两千多年前总结的话(周厉王残暴,召公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王不听,三年后国人暴动,王死于彘)。我们来到这里,种菜之余,就听到一片对此地以至广播局“干部”层的不满。
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不能容忍任何的官僚以及官僚们营造的环境中种种不公和不义。我一时忘了我就是由于“以反官僚主义为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打入另册的。但也许因为我当时确实只是要反官僚主义,而没有把反官僚主义提升到反体制,对组织仍然采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权威”评价,并以此支持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革命者”的信心。
我想到,我应该向党组织反映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我想,过去反官僚主义,真也好,假也好,公开为文,嚷嚷出去了,构成罪状,那么,我按组织程序办事,写信给机关领导,请他们抓一抓吧。
8月11日这一天,我给广播局局长又是党组书记的梅益以及机关党委书记陈竞寰写了一封信。
为什么不给顶头上司、直接领导写信?因为涉及的不是我所属部门的事。还有一层,就是我对梅益品格的信任。大约一九五八年秋后,文秀从下放劳动的沧县回京,上班路上遇到梅益,梅益问:“小邵怎么样?”她答:“还好吧。”文秀面对老领导忍不住多说了一句:“我到现在也没想通,他怎么会是右派呢?!”梅益接着说了一句:“说不定哪天我也会成右派的。”这表明,梅益对党内生活的不正常,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是亲历深知的。有了这句话,还用担心他对我的进言会因歧视而不予置信吗?
不久,接到梅益的复信,全文如下。
彦祥同志:
8月11日的信今天才看到。前此我已收到了几封信,反映的情况同你说的一样,有些还要严重些。“13号”我到过那里,也受到同样的待遇。此风确不可长。当时我对他们说了,看来还要作进一步的规定。
你说提笔之前“不无顾虑”,我看大可不必。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说,就发表意见,即使有错,也不要紧。谁能说他的每一个意见都是正确的?
看了你这封信很高兴,后面那一点顾虑,虽然没有阻止你把情况和意见说出来,但如果今后能逐渐减少以至完全取消,就更好。希望能如此。祝你好!
梅 17/8
2005年时,我找到了这封旧信,曾写过几句话,说:“今天的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也许想象不出,这几句心平气和的话,解除顾虑的鼓励,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又是写给一个‘摘帽右派’,并且恰恰是肯定他向党组织提批评性的意见,揭露机关生活中老干部身上的‘阴暗面’……是多么不容易。——即使到了今天,类似的状况下,你以为容易吗?”我说,这里没说“官话”,“这是一种平常心,惟正直者有之。这也是一种天真,没沾染官场的世故。……不过,用今天世俗的说法,则是:邵某冒傻气,梅益也冒傻气。”
因此,梅益之被指责为“右倾”,指责为“招降纳叛”就不奇怪了。由于我们这里所谓左右之辨,有着中国特色,混淆不清,我平时不大愿意以所谓左右衡人。不过,在习称极左统治的年代,而被目为右,那是极左视角的右,倒说明其正是持中居正了吧。
农民替我们死于饥饿
机关里也在采取措施应对主食、副食都不足的现实处境。行政部门想出个主意,跟沧县(1958年选择那里作为广播局第一批下放干部劳动据点)和黄骅(广播局的右派分子们劳动改造地)两地建立了一份“供求关系”。黄骅靠海有海产,沧县不靠海,却有不少水洼子,连冬天都可以破冰捕鱼。一两年后,机关里面闹起一桩“沧黄账”公案,就跟此刻所谓困难时期实即大饥荒中的一些丑闻有关,我至今也没弄清楚。
编辑部在“救灾”中绝对不是主力。但我们也被叫出去参加打树叶的活动,据说是帮助食堂搞“叶绿素”。
文艺部一位编辑因为肚子饿“犯了错误”。他住在护国寺街麻花胡同宿舍,晚上回家路上,在护国寺街西口迤北一家副食品店,“拿”了一块点心,被抓住了。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记得他身量高高的,当时听说越是身高体壮的男子汉,由于平时食量大,越是容易感到饿,饿不可耐(浮肿也是从高个子壮年人开始的)!我担心,是不是又要开他的会,让大家表态,那可该怎么发言啊?后来好像没听说开什么会。这可能是文艺部党支部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文艺部支部书记,是秘书组的组长李新,一位中年的“部队家属”。她丈夫是总后车管部部长,但她身上没有所谓夫人气,每天乘公交车按时上班,勤勤恳恳,对人也平易和蔼,不板面孔,通情达理的。在今天看,则也近于“古典共产党人”了。我想,如果支委会决定不为那位当代的“冉·阿让”开批判会,李新该是起了主导作用。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明智选择,如按惯例开会,恐怕不仅两败俱伤,而且会数败俱伤的。
虽没开他的会,却把他下放安达了。
现在回忆1960年秋冬的事情,总觉得一片混沌。绝少晴和景明。也许是因为吃不饱的缘故?就在这种暗淡的感觉中过着早八晚五的日子。
文秀已经怀孕半年多,她跟我同吃食堂,我都感到吃不饱,她怎么能不饿?更别说营养了,偶尔吃到一两条炸带鱼,她把鱼骨架放到暖汽片上烤干,研碎,意在补补钙,聊胜于无。我们商量,是不是出去下一次馆子,稍稍补充些营养。当时下饭馆,有双重障碍:一是饭菜贵得吓人;二是不敢堂而皇之地去。如果遇到哪位积极分子,给揭发了,至少要开一两次会作检讨。好在冬天天黑得早,我们乘公交车西行,到终点站的公主坟,找一家小店,悄悄坐下,不言声地闷头吃。
回来以后,这一次“改善生活”的物质因素早已消化净尽,但它的精神因素还在拷问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背着党组织去吃了一次高价饭,而是因为我们背着父亲母亲,我父亲七十高龄了,还在辛苦上班挣那份工资养家,我母亲不时的胃疼、心绞痛,他们不是一样定量有限且油水不足么?!我们置他们于不顾,于心何忍?
我们觉得自己对不起父母老家儿,却忘了我们几亿衣食父母的农民正在大饥荒中忍受折磨。
我们当时竟以为,广大农村的境况会比我们城里人强得多,理由是他们不但有自留地,还可以利用宅旁园地莳弄些瓜菜,领导号召的瓜菜代,他们实行起来比我们得心应手啊!
错了,完全错了!错在哪里,今天已经不用多说。
我们优游在大饥荒的边缘,农民已经从饥饿线上被赶到死亡线上了。
近五十年后,2008年清明,我写了如下的两段话:
我从今天人们观念中对“这个人”,对“这一个人”的铭记和怀念,想到了近五十年前大饥荒中的三千多万死者。那是在和平时期,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统称“三面红旗”),持续到1961至1962年的三五年间,主要是“人祸”(而不是过去谎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所致。其间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约3755万人。大多是农村人口。在某些灾难严重的省份和县区,有一个生产队,一个大队以至一个公社(相当于一个乡镇)全部死绝的(河南信阳一个专区竟死了一百多万人!)。他们默默地以卑微如草芥的生命承受了违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承受了违反法律违反人情违反常识的灾难性后果!
而从那时起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册历史被尘封到阴山背后。我们,死难者的同代人和后人,由于种种原因,对几千万的死者采取了不可原谅的漠然的态度。例如包括我在内的,从那个年代活过来的城市中人,特别是大城市中人,当时是靠特别调拨的粮食得以维生,虽有小不足,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甚至浮肿,但不致命。我们的存活是以三千多万人饿死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三千多万饿死和非正常死亡者是替代我们死去的。然而我们在四五十个清明节,有多少人想到为这些饿死的冤魂烧一炷香呢,其中许多死者已是没有后人的绝户!我们不祭奠他们,谁去祭奠他们?
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觉悟,这是迟到了五十年的良知。
毛泽东的《矛盾论》综合了前人的学术成果和思考所得,也不排除当时陕北一些哲学工作者的参与,总归是值得一读的。我之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便得之于世界上矛盾的普遍性这一命题的启示。比如,我一方面走来走去的是一个“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在我的内心生活里始终未变的,则是以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是共产党意义上的革命者)自居,以此为精神支柱,以此为道义制高点,以此为自尊心的后盾。这样,我在从反右到“文革”前后的时空里,都能泰然甚至傲然面对一些趁乱投机的政治小丑、打手乃至身居高位但为我所不齿的人。而在服从革命利益的高调下,则不惜放弃、牺牲了个人的尊严,所谓“不向任何个人折腰,但无条件地俯首向党,‘俯首向工农’”云云。
(摘自《一个戴灰帽子的人》,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7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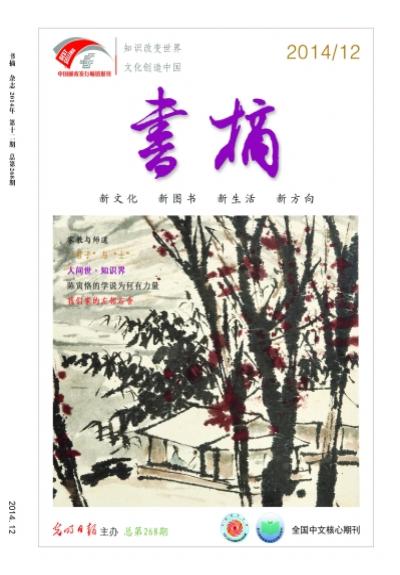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