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老五届,是指北大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学生。这个九千多人的群体,在1968或1970年间被集体发配到基层,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个人命运由此发生重大转折。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老五届学子的独特行迹,构成了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970年3月14日,我们北大三个外语系的部分同学离开北京,作为外交部代国家管理储备人员,来到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劳动。
一天,大雪横飞。农场一下雨雪,就到处泥沾脚。我们借来铁锹、柳筐,修理门前的鱼塘。我们自己砌炉子;拉胶皮车,出猪圈里的粪土。渤海湾比北京冷,水缸里的水早就冻成冰。新的连队什么也没有,连坐的凳子都没有,全靠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我们自己动手,用稻草编草凳。草凳在军垦可是必备物品。部队集合开会,或是看样板戏电影,战士每人手提草凳跑步入场,一声令下,齐刷刷放下草凳。又一声令下,齐刷刷坐下。编草凳之前,要学会搓草绳。这是我的拿手好戏,我是在巢湖农村长大,小时候在村子里就会搓草绳,自然得心应手。我一人就编了五只草凳,有些女生反倒编不好。后来,女生喊我去帮她们编草垫子,卷草垫子,闹得出了名。
军垦部队有炊事班,负责养猪。学生连也养猪,也杀猪。来新人,要杀猪欢迎,有人走,要杀猪欢送。春节过年,要杀猪欢庆。一天早上,连里杀猪。我们把猪捉住,捆住,杀了两刀才杀死。猪嗷嗷叫时,我不敢动手,操刀的是胆大的男生,他们用开水烫猪刮毛,用长长的铁钎,从猪脚捅入,插到猪肚,口咬猪脚,铆足了劲吹气,将煺毛的白猪吹鼓,像个庞大的皮球。坏了,皮球漏气了。急忙喊人来缝,应声来了几个女生,她们拿来针线。到了现场,傻眼了。原来漏气的地方,有皮球的敏感部位。但是,情势危急,是等不得的。她们也顾不得了,三下五除二,将漏气的地方,包括敏感部位,逐一缝好。忙了三四个小时,到12点才杀完。最后,我去洗猪大肠,这活特别脏。帮助杀猪,对我来说,可是生平第一次。
我们连有82亩地,是刚开荒的生地。早春天气寒冷,我们下大田,甩平地,抬筐平土,两人一副筐,一抬一甩就是一天,肩膀都抬疼了。没人喊饿喊累,回来时依然一路歌声。天暖之后,下水田,修田埂,育秧,放水,看水。早晚一片蛙声。晚上躺在炕上,没想到半夜搞紧急集合,我们排许多同学鞋子找不到,下地乱摸。棉袄穿成棉裤,绒裤只穿一条腿,还有的把裤子前后穿反,嘻嘻哈哈,乱成一团。
5月上旬,天阴水凉。拉木耙,平秧田,单裤卷到大腿根,嘴唇冻得发紫。我和朱立才一组,四人拉耙,全身湿透。泥水太深,齐大腿,停下的时候,我的腿尚未站稳,朱立才就拉耙朝回走,将我一带,往后跌了一跤,仰面倒在泥水里,全身泥水湿透。有条耕牛累坏了,摔倒在渠里。部队调来十几个解放军战士,跟学生一道,将耕牛抬出来。
在军垦,要求天天读,天天练。但都徒有其名,压根保证不了。晚上回到草屋,朝炕上一躺,仰面朝天就睡着,晚饭都不想吃。周总理指示,在军垦农场每天要平均学习外语三小时,没有得到落实。有件事跟外语有点关系,是到部队帮助战士练习所谓的俄语喊话,其实是用汉语注上俄语的发音,喊六句话:“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举起手来,出来,不要动,跟我走!”
8月,我看到《解放军画报》刊登巨幅彩照,绿油油的田野正是唐山军垦农场,大标题是《红了思想,绿了荒滩》。如今古稀之年,打开当年画报,展开巨照,暖融融的春风依然扑面而来。
我们学生连也种菜,养鸡,养鱼,养猪。天黑了,打着手电筒,去田野捉蛤蟆喂小鸡。晚上弄菜地,正是蚊子猖獗时,在头上和身边四周绕圈圈,多得碰手,叫得烦人。睡觉时不当心,胳膊碰到蚊帐,早上醒来,胳膊上一长串红包。我的日记本里,至今保留一只军垦蚊子的标本,像只小蜻蜓,大得惊人。9月中旬,暑气过去,学生连全连出动,到排水渠里去抓鱼,抓黄鳝,抓泥鳅。这还算善举,但是8月底,连部决定下田逮青蛙,聚餐改善伙食,现在可能会受到质疑。
晚上,学生连人人都出去,打着手电筒逮青蛙。去沟边路旁的同学逮得少,去稻田毛埂上则收获颇丰。毛埂很窄,一人走一条毛埂。军垦的青蛙很大,晚上都待在毛埂面上。手电一照,就傻乎乎地不动了,无需擒拿,只需伸手之劳。走一趟田埂,就能逮到几十只。后面的同学背着麻袋装,三人小组一小时逮到二百多只。夜间会师,多得不得了,数不胜数。第二天早上,发现打死的有一小半,剁碎了喂小鸡。我从小不敢杀生,有些男生胆子大,宰杀一大半活的青蛙。有的用刀切住青蛙头,另一只手将蛙皮扒下。切掉四只脚,除掉头,勒掉里面五脏,剩下一大块肉,还在跳动。有的先切头,斩掉四只爪,然后用刀划开蛙背,再扒下蛙皮。剩下的蛙肉足有二十多斤。女生都说残忍,声明不吃蛙肉。中午每桌摆一盘炒熟的蛙肉,蘸酱油,女生却吃得最凶最多。
有位小同学叫何畏,是学生连的女卫生员。大冬天12月份,给八班的女生打针。不小心,针头断了,半寸长的针头陷在女生的屁股里。她拔不出来,急得要哭。大家都十分着急,怕针头在屁股里面游走,钻进血管,祸就闯大了。这时,男卫生员陈应复赶来。大家七嘴八舌说,赶紧送部队医院。但从连队抬到医院,针头一经晃动,会在女生肉皮下乱窜。陈应复说,不行,得马上急救。何畏一听,就打麻醉剂。陈应复就在宿舍里,用刮胡子刀片,在女生屁股上动手术。第一刀下去,没找到针头,说是臀部难找。又下了第二刀,终于用镊子将针头取出。两人临危不惧,紧急处理后,把女生送到师部医院。挨刀的女生也很勇敢,说,不要紧,你们放心吧。
从北大,到军垦,如火岁月,似水流年,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真的好像换了一个人。1971年7月,全连94名学生,有69人评上五好,没有我。军垦许多营房墙上都有我写的大字,还有我画的巨幅宣传画。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合人意,不合时宜,改造的句号画得不圆。回望50年,此生还算坚强,于此得益甚多。1971年国庆,我们被召回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两年法语。谁也不知道,就在两周之前,1971年9月13日,林彪专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
(摘自《告别未名湖.2》,九州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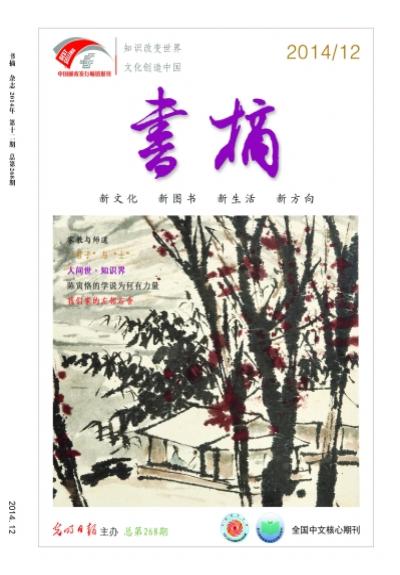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