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我最敬仰的现代学术大师。自从我差不多三十年前开始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直到现在,我读陈著没有停止过。陈先生的书是我的案边书,无日不翻。开始读的时候,没有想写文章。我在公共汽车上也读他的书。我读得非常仔细,像《柳如是别传》,我也是逐字逐句细读的。当我熟悉了他的著作、他的人格精神之后,陈先生就始终伴随着我,陈先生的精神和学问影响了我整个的身心,他再也不会离开我。
做人文学术研究的人,无论文学、史学还是哲学,我们常常有一种无力感——这些学问有用吗?人文学术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们常常感到人文学术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人文学术工作者、从业人员充满了无奈。但念了陈寅恪先生的书之后,对他的学问和学说有一定了解之后,会发现史学、诗学、哲思等人文学术是可以有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著作所以有力量,一个是由于他是大学问家,能成其大,见得大体。就像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样,王国维称他们的学问是能成其大者。还有,陈寅恪先生是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独辟创发的系统思想。简单以史学家目之,未免把他的学问看小了。他更不是一个单一的材料考据家。当然,他一生治学对中国的文、史二学做了大量考证,所涉材料的广博,鲜有人能及,但他在甄别考证这些材料的过程中常常放出思想的光辉。
大家知道他研究隋唐史的两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书并不厚,你注意到他的材料的使用,一遍一遍的引证新、旧两《唐书》。如果不懂学问的人或者不耐烦的人,很容易略开他的大面积的引证。可是,只要略开他的这些引证,你就不能懂得陈先生的学问。他的每一条引证都不是无谓而引,材料举证本身就是思想的发现。然后再看他引证之后或三言两语、或千数百字的疏通引论,所引证材料的生命力便粲然释放出来。因此可以讲,他的关于隋唐史的两部著作,既是史学的著作,也是文化史的著作,同时也是思想史的著作。姑且先不说其他的著述,单是这两部书,就可以认定它们是了不起的思想文化史的大著述。包括《元白诗笺证稿》,虽然是对以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文为中心的文史考证,以元、白两诗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里面的内容,实际上是研究唐代的思想文化史和社会风俗史,研究中晚唐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知识人士和文化人士的心理、个性、面貌所呈现的变化。
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与学说所以有力量,与他是一位思想家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由于他的学问里面有一种顶天立地、独立不倚的精神。他的学行经历,体现了一般知识人士所不具备的节操和气节。这就是他晚年在给蒋秉南先生赠序中所讲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以及绝不“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盖亦指此义。还有他在给杨树达先生的著述所写的序言里讲的,“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於立言不朽之域”。为学从来不“藉时会毫末之助”,“贬斥势利,尊祟气节”,这是陈学最富光彩的精神层面。他的学问充满了恒定的精神信仰力量。
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也还由于他的著作里面蕴含有深沉的家国之情。我很喜欢他1965年写的《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那首诗,其中有两句写的是:“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两句诗是陈先生整个诗歌创作的主题曲,也是打开他著作宝库的一把钥匙。因为他的精神力量跟他的家国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很多诗里都有类似的情结的流露。“频年家国损朱颜,镜里愁心锁叠山”、“衰泪已因家国尽,人亡学废更如何”。他的眼泪都哭干了。所以哭干,是由于深沉的家国之情,这是他一生精神脉络之所从出。
而他的学问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优美的家风门风使然。“优美之门风”这句话,是陈先生在他的著作里面,讲到汉以后的学术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刚才提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著作,其实此两部著作非常强调地域和家世信仰的熏习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有一个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的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版,第20页)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因此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以后,如果没有家学传统,就没有学术思想的建立。
当然很遗憾,晚清到民国这一百年以来,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不必讲,最大的问题就是家庭与家族的解体。家庭与家族的解体,便谈不上学术的传承了。所以我们特别珍惜义宁之学的传承没有断绝。文化传承有三个渠道,一个是家族,一个是学校,还有一个是宗教系统。宗教系统在中国不是那么发达,这是另外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讲。学校系统,现代的学校制度基本上是知识教育,遗漏了“传道”的内容,致使问题重重。所以中国文化的传承,家族的传承特别重要。但在今天讲此一渠道的文化传承,无异于缘木求鱼。相反文化衰落的迹象不时出现,这跟家族的解体、士族文化之不传直接相关。但是我们庆幸,义宁之学有陈先生这样的当代了不起的思想家和学者,陈氏家族的精神传统和文脉完全承继下来并有所光大。义宁之学不是陈寅恪先生一代之学,从陈伟琳先生读阳明书而发为感叹开始,到陈宝箴再到陈三立在晚清以至民国的思想人格建树,最后到陈三立后面的大家常讲的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陈师曾、陈隆恪以及庐山植物园的创建者陈封怀先生,都是如此。
我最近出版一本书,叫《陈宝箴和湖南新政》,探讨从1895年到1898年,陈宝箴在陈三立的襄助之下如何推动湖南的变革维新。三年之功,改革走在全国最前列。但是到1898年戊戌之年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维新变法的浪潮被打下去了,“六君子”被杀,康、梁被通缉,陈宝箴和陈三立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当时跟随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参与改革的诸多人物,梁启超、谭嗣同不必说,包括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都受到了处分。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陈氏家族的悲剧。陈寅恪先生一生,他的内心常常充满苦痛,他的苦痛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家国兴亡的苦痛。按照心理学的分析,任何苦痛都跟他的记忆有关,而陈寅恪先生内心的苦痛,据我的研究,跟他的家族在戊戌之年的悲剧有深切的关联。所以他的诗里经常把湘江、湖南跟他的苦痛连在一起。所谓“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等等,就是指此。
寅老何以有此种深层情绪的不可遏止的流露?仅仅是由于祖父和父亲受到了处分吗?不是的。他这个苦痛,是因为对家国有更大的关切。因为在陈先生看来,陈宝箴和陈三立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变革主张,属于“渐变”,是稳健的改革派。如果按他们的主张行事,最后推荐张之洞到朝廷主持变法,由于慈禧太后喜欢张之洞,就不致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完全对立冲突的地步。如果1898年的变法得以善终的话,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变乱。这就是陈先生的苦痛之所从出。1898年底,受处分的陈氏父子由湖南回到江西,住在南昌的磨子巷,后来陈宝箴筑庐西山,陈氏父子回忆湖南变革的不幸遭遇,孤灯对坐,仰天长嘘,这种情境下的心理情绪绝对不是个人的处境问题,而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忧思。陈宝箴、陈三立以及陈寅恪先生的深情,其实就是家国之情。
陈先生学问的了不起,他的学说的力量,还有一点,陈先生对古人——我们可以引申为对己身之外的他人的学说——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一思想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他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讲的,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内心世界的恕道。“恕”是孔子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生轻薄古人,陈先生不持这种态度。这个非常之难啊!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陈先生总是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所以你看三卷本的《柳如是别传》,很多人奇怪,包括一些老辈,很纳闷陈先生为什么写《柳如是别传》。我认为这是陈先生一生当中最大的著述,绝对不是简单地为一位古代的特殊女子立传,而是“借传修史”,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写的一部明清文化痛史。
很多朋友遗憾陈先生没有写出一部通史来,其实《柳如是别传》这部书的学术价值,远远超过一部所谓通史的价值。这部书对明清时期众多历史人物那种恰当的评价,那种深切的“了解之同情”,令我们读后非常感动。女主人公后来婚配给晚明的文坛领袖、有“当代李杜”之称的钱谦益,一个很有资格做宰相的人,由于天时人际的关系,宰相没有当成,告老还乡。他是江苏常熟人,后来他一个关键表现是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垮台,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是为南明。钱谦益在南明小朝廷入阁了,成为礼部尚书。柳如是跟钱谦益一道从常熟来到南京。但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下,扬州守不住了,史可法自尽而死,结果南明朝廷垮台。而率先投降的是两位文化名人,一位是诗文名气特别大的钱谦益,另一位是大书法家王铎。但是,柳如是并没有投降,钱谦益“循例北迁”,去了北京,柳如是没有跟去,独自留在南京,后来又回到常熟。陈先生讲她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民族英雄,这样讲看来不为过。钱谦益在北京也没有恋栈,很快告病南归,回到常熟。在他晚年的整个生活当中,跟柳如是直到死都是在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虽然他投降了清朝,但是他后期的反清复明举动对他的投降行为在精神上有所弥补。陈先生对钱谦益这种前后两重人格的表现,作了很多具体分析,指出其降清固然是一生污点,但后来的悔过,其情可悯,应给予“了解之同情”。而且即使对于王铎,也承认他的书法很好,堪称“绝艺”。陈先生对于古人、对于古人的学说,持有“了解之同情”的态度,陈先生的这一学说,可以说千古不磨,反映出义宁之学的渊雅博大。
(摘自《陈寅恪的学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版,定价:4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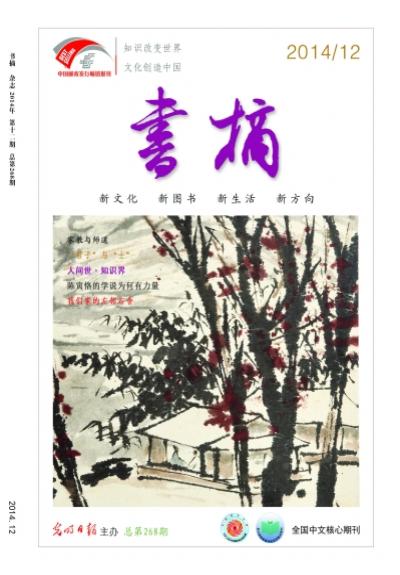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