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常被看做一件挺俗的事儿。其实,“吃”这件事原本不俗,讲究饮食恰恰是一个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是对大自然所赐的敬畏和珍视。况且日久天长,润物无声,吃也融进了我们的习俗和文化里。
饮食习俗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它最顽强,也最牢固。它化在人们的骨子里,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精气神,表现了一个地方的生活之美,之乐,之独树一帜。人们常说饮食文化,而文化无非是先人约定俗成的千百年的规矩。假若有一天,我们吃饭的方式都被彻底改变了,祖先所创立的灿烂文明远离了人间烟火,或作为文化遗产束之高阁,或为小众所把玩,那到底是可喜呢,还是可悲呢?
因此,我试图用文字记录那些最乡土也最普通的吃食,那才是我们文明的根本。
香椿鱼儿
北方的早春青黄不接,时令鲜蔬难得一见。然而,香椿树上滋出的嫩芽却是唯有这个时节才能享用到的俏菜。
在北京,吃香椿的传统由来已久。金代的《中都杂记》里说:“春日燕地以椿为蔬,喜之叶鲜味佳,实为上品。”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也记载着“燕齐人采椿芽食之以当蔬”的习俗。香椿是种很长寿的树。《庄子》上讲:“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八千岁未免有些夸张,不过爷爷小时候种的树孙子长大了还在吃确是常有的事。北京城里有许多高大的香椿树,每年郁郁苍苍,给古老的都城带来了一春又一春。
“雨前香椿嫩如丝”。谷雨前后是香椿芽最嫩最鲜的时节。肥润的春雨让院子里的香椿树上变戏法儿似地滋出一簇簇紫红肥嫩、光亮油润的小芽,馨香顺着窗缝飘进屋里。等到小芽长到两寸来长,芽叶中央略微变绿的时候,主人就会举着长竿打落下来,品味这至浓的春意。在北京话里,吃香椿被说成“吃春”,这可不是单单为省个字,而是在人们心目中实实在在吃到嘴里的四时节令。
香椿吃法很多。有香椿炒鸡蛋、香椿拌豆腐,也可以焯熟了切成小粒和焖得稀烂的黄豆拌在一起,点上几滴香油做香椿豆。不过最经典的吃法还得说是外酥里嫩的炸香椿鱼儿了。
调好的面糊加上苏打后略微饧饧,再和进少许素油。刚摘下来的香椿挑嫩芽洗净后用热水稍稍一烫,立刻变得翠绿。掸上千面粉蘸匀面糊,放进温油里炸。等到一颗颗裹着面糊的香椿在油锅里浮起,变成条条金黄灿烂的小鱼儿,赶紧用笊篱捞出来控净了油装在盘子里,撒上些椒盐,金裹翠玉般的香椿鱼儿就算做成了。拿筷子夹上一条,别急,小心烫,先用嘴轻轻吹吹,慢慢一咬,顿时满口异香从齿缝中窜入肺腑,每个肺泡里都充盈了春的气息。
香椿鱼儿格外鲜美的道理在于,吃香椿图的就是那股子鲜浓独特的香气。裹上面糊一炸,香气被油温迅速逼出,包裹在鼓起来的面皮气囊里,吃起来自然是鲜沁肺腑,春香独具。若是用香椿烙饼,半天不熟,香气都蒸发完了,尽管放的香椿多,吃起来反倒不那么香,实在有些暴殄天物。
吃香椿的习俗不仅北京有,华北、西北地区也很普遍。陕西关中地区由于盛产香椿甚至用其来做馅包饺子、包子。
俗话说:“门前一树椿,春菜不担心。”其实香椿不只是春菜,打下来的香椿如果多得吃不了,可以用盐揉搓了储藏在坛子里做成咸香爽口的腌香椿,那可是四季皆宜的佐餐小菜。一坛腌香椿能够供一家人吃上一整年。坛子空了,香椿树上就又滋出了鲜嫩的芽叶。
香椿对北京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蔬菜,更是生活的一部分。从前,它是素席上的佳品。尽管这些年香椿树越来越少,但它们却早已扎根在这座古城的深处——它在北京大街小巷的名称里:长椿街、椿树街、椿树巷,还有香椿胡同、椿树院、椿树馆……它也在老奶奶哄小孙子玩耍时哼唱的童谣里:
小椿树,棒芽黄,掐了棒芽香又香。炒鸡蛋,拌豆腐,又鲜又香你尝尝。
头 脑
很多人是从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里知道明末清初傅青主的。那位三绺长须、面色红润、儒冠儒服的无极派大宗师,令无数武侠迷为之癫狂。不过历史上的他却并不是靠武功扬名立万,而是靠才学、医术、孝顺和民族气节。更有意思的是,他把这四者融而为一发明了一种特色名吃——头脑。他家乡太原的父老们,每到秋冬时节大清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必是去“赶头脑”。
“头脑”是种早点,类似于面糊汤。名字听来也许有些恐怖,不过里面并没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只不过是用大块的羊肉、羊骨髓、藕根、山药、酒糟和上炒过的面粉慢慢熬成的浓汤。要说特殊,就是里面必须有黄芪和良姜这两味调养脾虚胃寒的中药,加起来一共八种。相传,这种吃食原是傅青主为自己体弱多病的老母亲调配的滋补汤,本名“八珍益母汤”,简称“八珍汤”。
明亡,傅青主悲痛万分,出家当了道士,隐居在故里太原。他总是身披朱红色的长衫以示不忘“朱”明王朝,于是大家叫他“朱衣道人”。因为他医术高明,很多乡亲常来找他看病。
傅青主把八珍汤的烹制手法传给了一家小店铺,并且为其题名“清和元”,又特意在边上写了“头脑杂割”四个小字。凡遇体弱者他总会交代:“从明天起,赶天未明之时打着灯笼去‘清和元’吃‘头脑杂割’,吃过了冬天就好了。”病人按他的吩咐每天大清早从家跑到清和元锻炼上这么一遭,再吃上一大碗热乎乎的滋补汤,直吃得从头顶暖到脚心,浑身上下微微冒汗,五脏六腑都通泰。这么吃上俩仨月,自然是活血健胃,精神饱满,步履轻快。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半个太原城的人不等天亮都打着灯笼争先恐后地赶着去吃头脑了。于是,“赶头脑”也就成了太原一景。多数“赶头脑”的人们并未意识到,傅青主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故国的怀念,抒发对亡国的愤恨——寓意要割了“元”和“清”的脑袋,恢复大明的江山。据说傅青主至死依然穿着那件红袍。
转眼三百年过去,他所痛恨的王朝早已不在,但赶头脑的习俗却被传承下来。从深秋到翌年初春,老太原人仍然会天不亮就去“赶头脑”,而那些经营头脑的店铺门前仍然要挂一盏纸灯笼作为标志。
乳白浓润的头脑,盛在大碗里,不稠不稀。尝上一口,绵滑中透着微甜,清淡里带着醇浓,还有股若隐若现的酒香。就上一碟搭配的腌韭菜,咸鲜味出,咀嚼那大块的羊肉、山药和藕块也异常鲜美。
吃头脑要成龙配套,讲究配上一壶温热的黄酒、二两稍梅,外加个帽盒。黄酒要选杏花黄酒或北芪黄酒,浓得像蜜一样才好;稍梅就是烧卖,当然要吃热腾腾的羊肉韭菜馅的;帽盒是一种太原特有的空心烧饼,形似帽盒,味道咸香,掰碎了泡在汤里是越嚼越有味道。一套热乎乎的头脑大餐下肚,肠胃里涌动着热流,暖暖的,带着微醉。
话又说回来,头脑作为吃食的名称,并不是傅青主的创造。《水浒》第五十一回有段话:“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这里的头脑应该是头脑酒,原写为“酘醪”。“酘”是再酿的酒,“醪”是没去酒糟的甜酒,后来谐音演变成了“头脑”。傅青主发明“头脑”时或许是受了头脑酒的启发也未可知。
面 茶
“熬粗茶叶汁,炒面兑之,加芝麻酱亦可,加牛乳亦可,微加一撮盐。无乳则加奶酥、奶皮亦可。”这是堪称中国饮食圣经的《随园食单》里对面茶的记载。遗憾的是,这种吃法早已经失传了。
如果说《随园食单》里的面茶和“七碗生风,一杯忘世”的茶叶还确实有些瓜葛,那么北京的面茶和茶叶就八竿子打不着了。那是一种用糜子面熬成的小吃,类似于浓稠的小米面粥。至于为什么叫茶,恐怕谁也说不清。
糜子也叫“黍”或“稷”,江山社稷的“稷”指的就是糜子。古人把它当做谷之精华奉献给上天,称做“祭社稷”,进而社稷也用来指代国家,而糜子又称做“禾祭”。
糜子看着和小米类似,但颗粒略小,产量也低。就是这些小渣渣似的种子最能滋养人,每颗小粒都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凝聚着旺盛的活力。虽说加工起来非常麻烦,但磨成了面,味道要比小米更醇香,口感更细腻,颜色也更鲜艳。把极细的糜子面徐徐下进烧到八成开的热水里,加上少许碱和盐,一边慢慢搅拌一边熬呀熬,直到熬透了,就可以做面茶了。可惜现在糜子面非常少见,就连一些知名小吃店里的面茶也用小米面代替。
熬好的糜子糊看上去黄灿灿的,稍微稠些也无所谓,喝起来并不觉得粘嘴,但这样的面糊还不能被称做“面茶”。面糊盛在碗里,在上面转着圈淋上薄薄一层加了香油的巧克力色芝麻酱,再撒上少量芝麻盐,才称得上是面茶。芝麻盐不能多,多了喝起来齁嗓子,那可就不是味儿了。
老北京喝面茶讲究在冬天,而且最好是刚睡好午觉。伸伸懒腰,端过一碗滚烫的面茶,闻起来浓香扑鼻,品一品口感醇厚,热热地喝着,一股暖流穿过肺腑直落丹田,自是肚饱心暖,胳膊腿立刻有了活泛气儿,人也精神了。简单的享受给寒冬增添了无尽的温暖。有两句诗专门说面茶:“午梦初醒热面茶,干姜麻酱总须加。”也许是为了御寒,早年间面茶上还有撒上千姜粉的,不过现在已经不见这么喝的了。
面茶不同于粥,喝法有特别的说道。要先用筷子顺一个方向稍微搅和一下,然后端起碗来托在手里,直接把嘴凑在碗边上“吸溜吸溜”抿着喝,一边喝还要一边转悠着碗。这么个喝法的妙处在于,即便表面一层凉了,喝到最后碗里的面茶仍然是烫的,让人始终感受到全身经络无一处不暖;也唯有这么个喝法,舌头才能清晰地分辨出上面芝麻酱的浓香和底下糜子的醇香,充分领略面茶的层次感。而且这么喝完了,碗里是干干净净的,透着利落。如果用勺一搅和,就变成糊里糊涂的一大碗温吞糨糊。温吞和糊涂的吃食在北京人看来是不地道的口味,还不如不喝。
面茶是很普通的北京小吃,原本是走街串巷推车卖的,现在要想喝到地道的面茶,只能去那几家著名的小吃老字号,比如护国寺、白魁、南来顺等等。
冰天雪地的时节,热热地喝下碗面茶,浑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暖和透了。尽管未必想得起江山社稷,但却能感受到老北京的味儿。
(摘自《吃货辞典》,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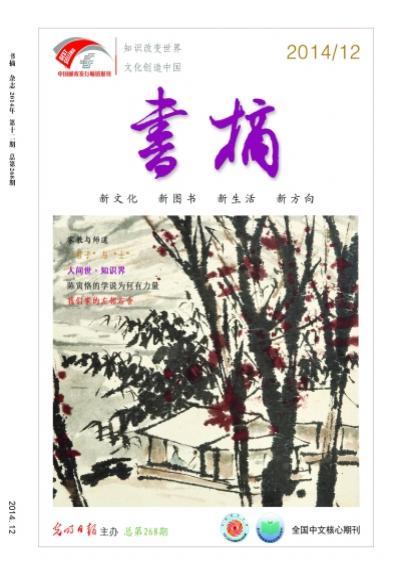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