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沈培,原名沈培金。
1934年正月初三生于杭州。
国统时期。
上小学,读初中,直至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共产党领导。
入艺专(国立杭州艺专)五年,1954年毕业。分配到上海新少年报。做美编,一干26年。会烧砖、犁田。
1980年,移居香港。
先后进香港商报、香港加华日报,混十个年头。
1989年1月辞工。
1997年7月香港回归,我成一国两制的香港居民。
老同事说:“你想跑?跑不了!”
哈哈!
债
1961年冬结婚。六二年初,妻下放东北白城子劳动,把工资存折交我。她月工资四十挂零,我有72元,还有些稿费。除月寄父母20元外,统统用光,多用在请朋友吃馆子。
来朋友,必上馆子,必我请客。没有钱,就借。
六二年底,妻归。我负债300元。
妻哭:“把我的工资用光,就算了。欠人300元,怎么还……呜呜呜……”
不要哭。连夜开工,画画画。
还了债。
给妻买自行车。
妻笑。
售票员
1958,“大跃进”年代。
树标兵,争先进,选模范,热火朝天。
从东直门开往南菜园,10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市级模范。
我坐过他的车,多次。
他售票,搀扶上下客,为客找座……他打竹板,声嘶力竭说快板,不停地说。他拿一把破蒲扇,给你打扇,哗啦哗啦哗啦啦。你连声谢他,求他别扇了。放下蒲扇,他端水给你喝。你不喝吧,他自己喝一口。就这杯子,他端水给那位喝。那位说:“我回民。”他立马拿出另一杯:“有回民杯!您呐!”
你受得了吗?!
茅台酒瓶
1963年,赴山东沂水采访。
住在县委招待所,松柏间一排小屋,静谧之至。赫见单独一间大屋,窗台上摆满茅台酒瓶。我说,此地住过大人物。
一言中的。住过大作家某某某。他引来许多仰慕者,高中的女生、年轻的护士……
作家热情招呼,分赠名著精装签名本,或以上海牌手表作饵,择其姣好者,一一放翻,犹如作家作品中主人公英勇杀敌般。
大作家愈益放肆,白日作战,门不上锁。上得山多终遇虎,招待员萧老头送饭,推门撞破。大作家以30元作掩口费,萧老头婉拒。大作家某某某被调回单位整肃。
这位年纪不大的萧老头,亦给我送饭,叼个烟袋,讷讷寡言。他的工资才21元。
敲锣的
温泉源,中学美术老师,儿童画大家。东北人,黝黑,兔牙,30岁,仍独身。温母焦急,时时催促其成亲。
一日,温告母:“妈,有人给我介绍人艺乐团一个打鼓的,好吗?”
温母曰:“啊呀,小祖宗,甭说打鼓的,敲锣的也行啊!”
喜欢谁
儿子未迟,1964年6月15日出世。有幸,他两岁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他上报社办的幼儿园,周六周日才回家。
1967年初,一个星期日,他妈在包饺子。未迟坐在小椅子上。我问他:“未迟,你喜欢爸还是喜欢妈?”他眨巴着眼,傻望着我。
“说呀!喜欢谁?”
“毛主席。”他嗫嚅答。
“对对对!”我赶紧道。
片刻,我又问:“你喜欢爸还是妈?”
“明彪同志。”他才三岁,口齿不清,把“林”字念成“明”了。我又赶紧“对对对”。
又片刻,我再问他爸妈中喜欢谁?
他答:“中总理。”
我不再问。
拼音字
1967年,革文化命第二年。
牛棚,关着“现反”张谦、“历反”胡哲安、叛徒阎仲禹。
张谦将硬纸板撕成小块,写上J(车)、M(马)、P(炮)……在练习簿上画格格,免写汉河楚界。与胡哲安对垒,进M吃P,厮杀一番。
造反派查棚。
张谦念念有词:M——M——P——P……
“学拼音字哪!”造反派离去。
连心事重重的阎仲禹也乐了。
枪毙六次
H,南大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少年报。她矮得像个小学生,圆脸小眼。大革文化命运动开始,她当上领导之一。她冲着我喊道:“沈培,你老实点,你的罪行,枪毙六次都不够!”
我惶惑,等待着六次枪毙。
折腾又折腾。直至抓“五一六分子”阶段,对我发起总攻。大字报、大标语、名字倒转打上×,来势汹汹。揭晓我弥天大罪:美院时期,大雪天,在孤山上,用小便在雪地上浇出反动口号:打倒毛泽东。
我说:“哪位能用小便浇出这五个字来,我服罪,枪毙十二次也行。”
有人忍不住,轻笑声。
瞎出空。
马家斌
“文革”中某日,紧急集合于饭堂。全场鸦雀无声,屏息以待。主持人喊:“把现行反革命马家斌揪上来!”
马家斌,天津人,大个子,木模工。他咋啦?
两边各一人,将马扭手摁头。马弓背,在小碎步中被拽上台。
主持人:“马家斌,你是不是反革命?”
“是——”声尖而长,唱大戏般。
“滚下去!”嘡嘡嘡嘡,押了下去。
马的罪行太反动,会上不便重复。会下悄传,他给三个孩子起名字:爱国、爱民、爱党。正好:爱国民党。
呜呼,此罪如何翻身!
臭分子
郑于鹤,泥塑家,成绩卓著。
“文革”中批斗他:“郑于鹤这个臭知识分子……”他即起立申言:“我无啥知识,叫我‘臭分子’好了。”
妙人妙语。
地瓜烧
1970年,河南黄湖农场劳改。烧窑班。
累极回家,喝酒解乏。地瓜烧,三分钱一两,亦醉人。
正喝着,令到:“专案组叫你去!”
小头目胥某,湖南人。老套训斥一大溜。
我,一腔酒气难开口,紧闭嘴,任骂。
训累收场,结语:“今天态度老实,没有驳嘴。滚!”
出得门,长舒酒气一口。
回家,酒兴过,泼剩酒,倒头睡。
田头小歇
军代表宣布:全体人员安家黄湖,不再回京。
绝望,厌倦。
军代表想着法折腾“臭老九”。五千亩小麦,不用收割机,下令人用手割,练人练思想!
割麦真累。排长下令:休息半小时。众人掷下镰刀,纷纷躺下闭目养神,管他娘!
唯有刘宾雁,拿出些小纸片,安坐田边学起英文来。
在这个人间地狱,我大概在八九十层,刘是钦犯,毛老爷子御定,他至少得在十九层。
他何来勇气、毅力、信心、远见?
我远远望着他,感慨,不解。
刘大洪
刘宾雁的儿子,我的小友。
在黄湖农场,整我的专案组某,对大洪说:“沈培给你放什么毒,你要好好揭发!”大洪答:“用不着沈培给我放毒,我爸给我放的毒就够了。”
我起码有三十多年没有见到大洪了,该五十多岁了,真想念他。
罗山猪
休息日,丁午、罗菁兰、钱玉良、我,赶集罗山。集上买条大鲤鱼,到饭馆,请掌柜的烹煮。
小钱内急,老丁说:“后院猪圈拉去,猪吃屎。”
一会儿,小钱一脸松快回来,入座,等吃鱼。
后院嘈吵,只听掌柜大声骂道:“哪只癞皮狗,朝猪圈里屙屎!”
往回走路上,老丁纳闷道:“黄湖的猪吃屎,罗山的猪不吃屎!真怪了!”
大 梨
1973年,京新巷,永玉先生家。有人敲门。“爷爷来了,坐、坐。”黄先生说。
是沈从文先生,黄先生介绍我认识。第一次见面。他个子不高,瘪嘴,眯眯笑,慈祥如老太太。他解开手帕包,一个大梨,大极的大梨,给黑蛮的。
晚饭罢,由我陪送从文先生去公交车站。
“文革”后,沈先生作品重新印行。当我读到《湘行散记》时,浮现出他笑眯眯拿出一个大梨来……
恁好文章,是他写的么?
暂存
应该是1977年,夜访黄永玉先生。还是京新巷那间小屋子。他抽着烟斗,看着挂在墙上的画,招呼我自己倒茶。
是一张唐德懿太子墓的仕女石刻碑拓,神品!
我走近看裱在拓片上方的题跋,赞评此拓片如何如何了不得。后题:黄永玉暂存。
问:“是人家借你看,要还的?”
“不,送我的。”
“那为何写暂存?”
“我不是要死的吗?”
包公放屁
据说是文艺界文艺晚会的节目或灯谜。
谜底:王朝闻。
绝倒。
免流失,一记。
瞎 捧
初识,想说句赞语恭维对方。道岔又未扳对,撞车!尴尬难下台。
任溶溶来港颁发儿童文学奖,见面闲谈。我称赞他在《小朋友》杂志上一篇文章,牛啃小孩耳朵里长出来的一棵苗……
任溶溶笑说:“那不是我写的。”
真要命!
在弥敦道遇文楼,他是港地雕塑界闻人。我与他仅点头交,说啥?我赞他新世界广场上的两株不锈钢树做得好,风一吹,钢片树叶叮当作响。
文楼说:“那……那不是我做的!……”
又撞车!
这就切题了:“瞎捧!”
一通电话
廿多年前,某日,电话铃响,我接听。对方说:“我找沈培金,我叫某某,是沈培金的同学,现在是美院院长……”
我答:“沈培金去广州了。”
挂断。
老 贾
贾化民,山东人,中青报摄影记者。四九年前开照相馆云。拍摄西沙群岛第一人。他受派赴东德,为团系统报刊购大宗摄影器材。“五反”中打成“大老虎”,关起来。审核账目分毫不差。“文革”中斗他崇洋,称赞蔡司相机好。他顶回道:“係(是)好!係好!不好还进口?!”批者无言以继。
在黄湖农场劳改,叫他运送井水。戴顶巴拿马草帽,叼支烟,背手,慢悠悠走在驴车旁,活像丘吉尔。他小屋门口,用井水浸着三两黄海瓜,清凉馋人。
晚年,三里屯偶遇,头脑灵清如昔。他临终前,婉拒抢救,说:“我满意自己一生,未讲过假话。”
我与老贾,交浅敬深。
(摘自《孤山一片云:沈培琐记》,天地出版社2014年3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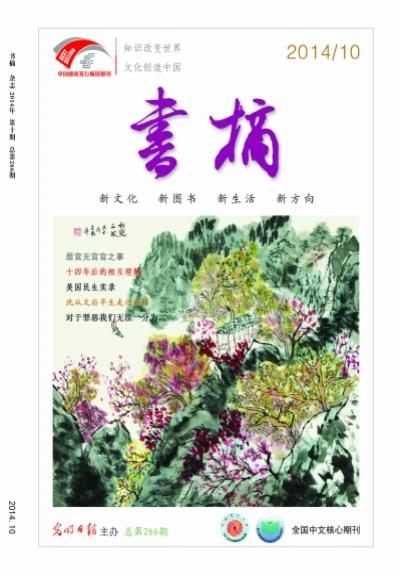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