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没有亲见,王瑶先生中年的时候还是西装革履,并且叼着烟斗的。这是真的。大概是1988年吧,有一天晚上我们去拜访先生。临告别,先生让蕴如师母拿出一套五张照片送给赵园和我,上面已经题好词。其中1961年的全身像,就是笔挺的西服,乌黑的头发,而且特浓密。那张头像的轮廓,长长的脸,稍尖的下巴,乍一看,像50年代我们熟悉的一位苏联诗人。不过王先生的眼神是严厉深邃的,但并不看着你,也不像在沉思,挺怪的。对了,先生那照片上的眼神,就是冷冷的清醒的专注的眼神,却又向内吸收自己的所见所思的样子。这些,自然是现在对着照片的遐想。那天晚上双手接过照片,略一翻检,心情是别样的沉静,而且奇怪:为什么现在送这一套照片呢,题好了词的?
我认识王先生的时候,他已经“华发满颠,齿转黄黑”了。那是1976年,“最高指示”创建“鲁迅研究室”的时期。李何林先生从天津南开大学调到北京,出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又指定从全国几个省市借调十几二十个研究人员,而王先生内定为研究室副主任。
于是每星期有那么几天,上午八九点钟左右,王先生从接他上班的轿车里出来,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上得二楼,走进他的办公室。下午五点钟,王先生又一手拿着或挟着深褐色的大皮包,叼着或拿着烟斗,一摇一摇快步走进送他的小轿车,绿色上海牌的小轿车,回到北大去。这五点钟,是准时的。这是李何林先生的脾气。要不是北大路远,接王先生的车开出得迟,早上也会八点上班的。王先生有个晚上读书、看报、写作到深夜而次日晚起的习惯,临到该上班的时候,可以想象他的辛苦。
王先生一进办公室就很少出来。不串门,不谈笑,也很少开会。要不开会的时候轮到他不上班,要不开的会只谈室里的行政事务,与他无关,他不来。只有中午吃饭的时候,能够见到王先生,拿着一副碗筷,和我们一道排队买饭。很快地吃完,涮涮碗,走了。
王先生的办公室是室里最简单的。因为我们的大都兼作寝室,内容丰富,也颇有气氛。王先生的却名副其实,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对简易沙发和配套的简易茶几,一个书柜里面空空荡荡。王先生就在这样的办公室坐了两年,指导我们研究,回答提出的疑难问题,审阅集体编著的《鲁迅年谱》。
我常常回味和王先生在一起的往事。可在鲁研室的两年只记得两件事。一次我去王先生办公室请教一个鲁迅所引古籍中的问题。敲过门,应命进去。王先生坐在满室烟雾中看东西。他抬起头听我问完,摘下秀琅架的老花眼镜,直白地告诉我不知道。我一下愣了,不知如何是好,鞠个躬退出来,比在室内闻着烟味还难受,也颇生气。一次吃中饭的时候,王先生在排队,我走过去告诉他大家正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瞿秋白到底是不是叛徒?并问王先生的意见。王先生脱口就说:这是中组部的事情。我的心一震,真像醍醐灌顶似的,许多暧昧难解,三番四覆的疙瘩全解开了。
不记得什么时候,也不记得为了什么,怎样走进王先生的家,到北大镜春园76号去拜访王先生的。但他给我碰的那个大钉子,每每想起都心颤,当时是气得决心不再踏进那个门的。
王先生住在一个独立的四合院里。门口有一对比我还高的石狮子,这种权势的象征颇不一般。后来才知道这里曾是黎元洪的别墅。进门一个大院子,有高大的柏树,有青翠的竹子,有蓬勃的杂草,因为没有人再来修葺了。东西房住了好几家,北房王先生也只住西边的小一半。后来落实政策又加了连接客厅东边的一小条,两米多一点宽的,横放一张床就差不多齐了。王先生用作书房,取了个名字叫“竟日居”,是把“镜春”两个字拆散来的。有人作过演义,头头是道。但王先生心里怎么想的呢?我没有听他说过。他自己很得意这个名字是感觉得到的,因为他平常几乎不写毛笔字,这回却用毛笔写下了这个名字,而且挂在案前;他又想用“竟日居文存”的书名编辑他的文章,——这是他得力而且得意的高足又是助手的理群兄告诉我的,可见很不一般。
王先生的客厅很大,很高,夏天阴凉,冬天很冷,——直到1987年才接上暖气;不知是“殊遇”,还是落实政策。那部电话确是落实政策才给装的,而且是王先生强烈要求的硕果。在装暖气的前一两年,北大要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决定给教授装电话,但必须是一级教授。王先生虽说在“文化大革命”时就被北大中文系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聘为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但教授还不是“一级”。可王先生50年代就装了电话的,这电话是“文革”革掉的。“落实政策”名副其实。王先生通知我装上了电话,分机号很好记:“三五九旅(3590)。”我立即跑去看他。他开怀大笑,告诉我这样的经过。
王先生的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红木家具:大书案,八仙桌椅,书柜。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箱装四部丛刊。西墙上挂着三帧条幅:靖节先生画像和《归去来辞》全文;鲁迅《自嘲》诗手迹的水印木刻;沈尹默先生书赠的墨宝。客厅中央按凹字形放着一组沙发,沙发前是茶几,茶几前是一架彩电。
王先生接待我们时,家里是非常非常安静的。王先生叫人斟满一壶茶,茶来人即退下,王先生再往杯子里斟。偶尔有家人从外面进来,都是轻轻地侧身走过去。唯一的例外是先生的孙女王宜,两三岁吧,她敢于闯进来,敢于爬到王先生身上去,敢于打断王先生和客人的谈话。王先生也任她嬉戏,设法哄她。
我的钉子于是乎也就来了。
我喜欢小孩,无论师长的,朋友的,同事的。我喜欢教他们直喊我的姓名,常见的喜欢带一块巧克力什么的去送他,王振华先生就曾戏呼我为“巧克力伯伯”,冲着他的孙子。我既然知道了王宜,也就兴之所至,忘乎所以。那次当我告辞的时候,拿出一块巧克力来给王宜。先生立刻变脸,阴沉着,推开我的手,厉声说:“别来这一套。”好难受呵。
后来师母告诉我,王先生连儿女亲家都不走动的。虽然,先生多次同我谈到过,他怎样操心女儿的婚事,怎样为她奔走。
后来王先生去昆明,去东北,去香港,总带给我一盒茶叶,一条领带什么的。1984年赴日本讲学回来,特地请师母拿出一只带回的皮包给我,并说,还有一只给钱理群。
1987年我去日本。行前问王先生需要带什么不,先生说清理烟斗的玩意儿折了,遇上带一只回来吧。在东京,我告诉王先生的日本研究生尾崎文昭君,他陪我着意找了一家专卖店,我俩挑了又挑,挑了两种两件。先生见了,很高兴。
现在,清理烟斗的物件没用完,先生却已走了。那时怕一件不够用,先买两件,还想再要再买的。先生送我的皮包已经修补了两次。赵园说了几次该换,该换,换什么呢?不过,总有一天得换的吧。
王先生的心情愈来愈开朗,思想愈来愈活跃,社会活动愈来愈多,兴致也愈来愈高了。
新加坡一华文日报请先生题词,王先生用毛笔写了一首七律:“叹老嗟卑非我事,桑榆映照亦成霞。十年浩劫晷虚掷,四化宏图景可夸。佳音频传前途好,险阻宁畏道路赊。所期黾勉竭庸驽,不作空头文学家。”先生拿给我看,说从来不作诗,也不写毛笔,诗既不好,字也难看,怎么办。我说,您不是诗人,也不是书法家。人家求您,是想听见您的声音,看见您的手迹,这样就好。先生从我捧读着的手稿上抬头看我,凝视了一眼,不说话。我说,这一张给我吧。先生正了正身子,稳稳地坐在沙发里,拿起了烟斗。
《中国新文学史稿》要重版了。一次我一进门,先生招呼了一句,立即转身匆匆从卧室拿出一叠稿纸,说我写好了《重版后记》,你看看,我一下紧张起来,像面临一场考试,站在书桌前读起来。先生就立在旁边吧嗒着他的烟斗。
我读了一遍,又快速复了一遍,对先生说,很好,结尾很动人。我建议先生考虑:是不是把被批判被迫作检查的事点一句?吐一口恶气!先生拿过稿子,走进卧室。很快,快得惊人,就出来了。指着加的一句问:怎么样?我看原来写着:“本书出版较早,自难免‘始作俑者’之嫌,于是由此而来之‘自我批判’以及‘检查’‘交代’之类,也层出不穷。”于是先生用力吸着烟斗,快活地谈别的话题。
清华大学的校庆,王先生是非去不可的。有几次他推掉别的活动,有几次他事先提醒我。有时谈起他的导师们,不仅带着深情的怀恋,也有对清华教授优裕生活给人影响的清醒分析。偶尔涉及身居高位的同学,三言两语,谈锋明快,没有丝毫过眼云烟的感怀。《清华1934-1938-1988纪念刊》出版了,先生拿出来给我看,笑着告诉我,每个人非写一段《自我介绍》不可,二百字,你看。我埋头读了很久。我感觉到王先生稳稳地靠在沙发上,咬着烟斗看我。他一定猜得到,我心里多么赞赏,惊叹。终于我念出“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一段给先生听,并说“似犹未失故态”,写绝了,妙不可言。先生不说话,也不笑,端起茶杯,很响地咕噜咕噜喝干了。任我给他又续上一杯,只客气地伸过手来挡一挡。
在王先生家和王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是一大乐趣,和听王先生讲演不一样。王先生有山西口音,讲演是愈讲愈快,愈讲愈陕,几分钟后就憋住了,讲不出来,于是喀喀喀几声,自顾自啊哈哈哈哈放声大笑,听讲的多半没听懂,也就不跟着发笑。这并不影响王先生的情绪。他照样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直到讲完为止。可王先生聊天,从容不迫,话并不难懂,说到痛快处,他笑,我们也笑,完全是“同声相应”。我曾琢磨过,王先生讲演为什么会那样?我想,王先生是善于思考,又富机智,日积月累,脑子里充满了见解。待到讲演,脑子运转快,口里吐字慢,他不但不自我调整,反而迫不及待,一发而不可收。像打机关枪,先是点发,接着连发,一连发就卡壳了。
王先生聊天,无所不谈,无所顾忌。他鄙夷的人、文,也毫不淡化自己的鄙夷。他每天看报到深夜,又看得特仔细,似乎对期刊的出版广告,尤其着意。因为他经常谈谁谁谁发表了什么文章,却又说明他没看,是广告上的目录。
大凡文学界争论的问题,王先生都很注意,也几乎都谈。他支持“重写文学史”,他支持重新研究过去被冷落的作家,他坚持文学史的分期是有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质的标志的……许多见解,脱口而出,“出语多谐”。这时他自己先笑,我们也笑,他就笑得更响。我几次劝超冰多主动来听王先生聊天,记一记那些很难复述的语言。可惜我懒,她也懒,大家都“得意忘言”了。
(摘自《阅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定价: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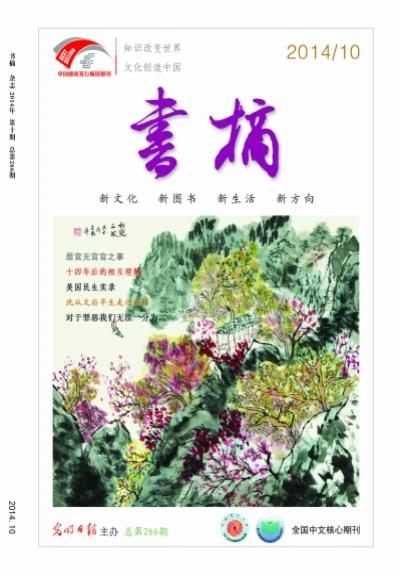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